書名:「盼望是安樂死的更好選擇 – 從中國與西方傳統文化角度來看盼望」
作者:趙洪鍠醫師、基督徒(院牧、教牧關懷輔導員、CPE 臨床教牧培訓督導候選人)
資歷:醫學博士(婦產科)、神學與心理學博士。第一位積極將西方的臨床教牧培訓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簡稱CPE) 帶進中國的院牧;為時十多年(2004-2015)。參面書Facebook 和 Youtube 的 Philip H Chiu.
摘要:
請問什麼可促使活在痛苦中的末期病患者繼續活著,而不選擇安樂死(醫師協助的自殺)?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給他們一個更好的選擇、藉著盼望來鼓勵他們積極活下去。在中國,許多農民和“都市貧民”在患上絕症時都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們負擔不起頻頻看醫師來止痛的費用;而另一方面,他們雖然很想醫師來協助他們了此殘生,但在現時的中國,安樂死還是不合法的。從作者多方面的臨床經驗和跨文化的學科綜合研究,表明了盼望似乎特別適合幫助這些處在水深火熱的末期病者、支持他們如何處理生老病死這些問題。
書本的第一章概述了中國衛生保健近年來所面臨的挑戰。第二章是通過作者的個人訪談,描述了在今日中國的絕症病患者是如何過活,並且他們是如何憑著文化信仰、個人强項和價值觀尋找到生活意義和盼望。第三章是從西方傳統哲學的角度來探討一些受訪者所提出的問題,例如:我的人生意義是什麼?第四章是描述盼望在跨學科的論壇上,表明了不同的維度,並且展示出盼望是人生中最先發展的美德(其次才是意志),所以盼望具有獨特的能力來成全絕症病患者的需要。第五章是探討一下,關顧者致力於 “培育臨終病者的盼望” 是否在情在理説得通、行得通。最後第六章概述了關顧者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來培育盼望,並且如何適當的尊重病患者的個人尊嚴與獨特文化背景。總而言之,當臨終病者仍然有盼望之時,他們會繼續從事生活,不至於考慮到安樂死這個問題。結論是:有盼望就有生命;比起安樂死,盼望是更明智的選擇。作者應當在此聲明,因爲作者本人是基督徒,又是西醫和院牧,所以這論文對文獻的傳譯可能帶有某程度的偏見和傾向,請讀者明鑒。
序言:
作者曾在中國一家規模頗大的城市醫院做了15個月的心靈輔(導)關(懷)員(西方稱之為院牧)。在醫院的腫瘤科所接觸的病者有不少都是身患絕症。他們忍受著頑固的疼痛和苦難,實在令作者感到非常難過。他們很想醫師協助他們了此殘生,因為他們實在負擔不起昂貴的緩解疼痛醫療費用。他們可謂進退兩難。一些人已用盡積蓄在醫療上,甚至陷入沉重的債務中;這造成了相當大的家庭經濟負擔。如果再堅持下去,不止意味著個人尊嚴受損、身體在疾病的蹂躪下日漸敗壞,而對家庭來説,也會帶來更多的債務和負擔。他們想死,但不確定如何才能有尊嚴地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知道作者既是醫師,又是心靈輔關員,不時都問作者有關“安樂死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PAS”的事(這概念在中國已流行很久),希望能為他們提供建議,甚至幫助他們達到這個“好死”的境況。這使作者也進退兩難。第一、安樂死在中國仍然是不合法的。第二、作者的基督教信仰和醫師身份(曾對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es oath作過承諾)不允許做這樣的事,盡管作者非常同情他們的處境。要知道,不論任何形式的自殺都會引致嚴重問題:如倫理、社會文化、政治、法律、心靈和關係的多種問題。在這書中,作者建議另一個可能是更好的選擇:就是在適當的環境下,培育病患者盼望,作為一種介入性的應對策略,鼓舞起病者的求生慾。作者認爲:有盼望就有生命。
與這核心問題有關的背景
中國是一個正在多方面轉型的國家。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當下,驚人的經濟增長帶來不少繁榮,但成本也實在不輕,形成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中國從國營企業過渡到自由企業的過程裏,使不少國民得不到足夠的醫療保健,因爲這些在過去都是由國家幫助提供的。當患有絕症之時,貧窮的人往往負不起醫院昂貴的治療和緩和醫療費用。他們也沒有任何善終關懷服務hospice program來減輕他們的痛苦; 家裡又很多時沒有提供他們足夠支持的人。難怪越來越多病患者對安樂死表示興趣。在西方一些國家(如荷蘭、比利時等)安樂死已成合法,但中國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作為一位已退休的美籍華人醫師和一位基督教牧者,作者對這些病患者深感同情,並常常想著,我怎樣幫助他們呢?我覺得無奈、覺得自己無用。我問自己,我是否真正理解他們呢?他們對苦難和“好死”又怎樣看?在中國,這些絕症病患者是怎樣過活的呢?他們的家人又是怎樣照顧這些親人呢?是什麼支撐著他們?他們活著的理由又是什麼?牧者與其他關顧者怎樣才能更好的支持他們呢?
論題與論點
當我看到這些絕症病患者在身體上、情感上和財務上遭受到難以想像的痛苦時,我多次問自己同樣的一個問題:是什麼促使這些百端受盡折磨的人選擇繼續活下去(而不是自殺)?當維克托·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被囚在納粹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時,他也問同一問題。他發覺答案是要“有堅强的意志來尋找生命意義。”這意念和意義幫助他和其他囚犯繼續活下去。基於這概念,我認為培育盼望可以幫助絕症病患者對生活保持積極的態度,讓他們繼續參與日常生活,即使在最黑暗之時。盼望允許人投射到未來積極的意義。作者個人認為,當末期病者認真考慮安樂死之時,盼望或者可能阻止他們這樣做。神學家詹姆斯·科恩James Cone 有云,“沒有盼望,人就形同死了。”
抱著盼望是一個過程:不僅是一個體驗過程,也是一個互動(愛和支持)過程、屬靈(信仰和信任)過程、和理性(思維和行動來達成目標)過程。 這四維度的盼望似乎特別適合處理絕症病患者普遍存在的四項存活關切:即生活無意義meaninglessness、孤立isolation、無依據groundlessness和死亡death。盼望也是人類生命周期中發展最早的一項美德(或强項)。如果真是力上加力,這便意味著盼望是所有其他美德(或强項)的基礎。
作為看法或觀點,盼望也可以戴上不同顏色的眼鏡來觀望未來。因此,不同的傳統文化和境況會帶出不同的看法。中西兩方對於盼望和意義的觀點可能會不同,但雖然假設和預設有不同,但卻可以相互補充和學習。作者熱切的希望這交流會幫助絕症病患者有多些選擇,應對他們的痛苦和苦難,實現他們自己定下的優質生活因素。
綜上所述,本文論証了以下幾點:(1)基於弗蘭克爾的積極尋找生存意義,以及盼望的獨特四維(包括其有關生活體驗、人際關係、精神寄托、與理性思維四種特質),作者認為盼望可以幫助絕症病患者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即使在最黑暗之時,也不必考慮自盡這一回事﹔(2)盼望具有獨特能力來處理臨終病者的存活關切,把盼望寄托在有意義的體驗、親朋的信任和愛、信仰和屬靈上的支持、和理性的處理(包括思維和行動)﹔(3)盼望並不是隨意加諸於對方的一類東西,而是一種有滲入性的積極態度或美德,是可以從關顧者實踐而作爲模範來培育出來的,好得病患者加强對未來的盼望﹔(4)關顧者需要堅定不移的一心一意將盼望注入信任和關愛的環境中,並且遵守對病患者的承諾﹔(5)培育盼望需要考慮到被關顧者的文化背景和社團因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文獻綜述和批評性分析,並且進行臨床訪談來補充文獻分析。研究問題有二:(一)在當今中國,絕症病患者若負擔不起醫療費用,無法獲得足夠的疼痛緩解時,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關顧者之生活是怎樣過?(2)家庭和專業關顧者還可以發揮什麼作用?他們又有什麽需要?關於這兩個問題,我特別對盼望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興趣。作者在中國的臨床經驗包括實地訪談,深切的了解絕症病患者的經驗,再憑著文獻回顧和文化背景的考慮,確定最適宜和最有效的關顧輔導方法,幫助病患者尋找個人的生命意義、存活原由,以及培育盼望。
作者在華南,因爲個人和專業關係,有機會接觸到不少病患者、醫師、心靈關顧者和咨詢師。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期間,作者採訪了總共23人。其中15人患有絕症,5人為其親屬,3人為關懷輔導員(1名道士、1名佛教醫師和1名伊斯蘭教教長Imam)。在這些採訪中,問題主要是開放式的問題(即是避免對方可以用是或不是來回答),鼓勵被訪者傾述他們的心事和故事。採訪者對盼望的任何暗示都是含蓄的。一般來說,訪談牽涉三個問題:(1)你可否描述一下你對苦難的理解嗎?它對你意味著什麼?(2)你的經歷會影響你(或你的家人)嗎?(3)在處理這病時,你(或你的家人)如何看生死?在聆聽回答之時,採訪者特別注意什麽是影響對方痛苦的因由、干預因素、和情境等各方面,並且對方是如何應對和後果又是如何。每次訪談結束後,作者都會在一小時內寫下簡短的筆記來記錄,並且在24小時內在電腦上記錄每次訪談的總結,盡量忠實地引用被訪者的陳述(見附錄)。所聽到的都會適當地加插在文章中來說明綜述文獻所提及有關生命意義和盼望的觀點,祈望匯集中西資源來幫助這些病患者渡過難關。
作者也應該同時指出,這些臨床經驗訪談並沒有按照正式的經驗標準來進行。要知道,盼望是否對絕症病患者有利還未經實証檢核。這有待將來更多的研究來確立其有效性。由於中國政府對宗教研究有所保留,所以作者沒有採用嚴格的實証標準,除非得到政府的承認和批准。今天國家所認可的三個外來宗教是中國愛國天主教會、三自愛國基督教會、和中國愛國伊斯蘭會。佛教和道教是國家正式承認的兩種傳統信仰,而儒學在中國是被視為一種哲學而非宗教。
這書可應用之處有幾方面:除了直接與絕症病患者及其家屬對話之外,此書還可作爲教牧關懷和輔導的培訓教材。牧者(如教會牧師、醫院院牧等)、傳道人、教會同工、甚至醫師、護士、社工等人(尤其是致力於善終關懷服務的人員)都會閲後得益。作者真的盼望這項研究受到中國衛生局保健政策制定者的關注,使他們持續的與醫療人員、屬靈領袖和關顧者保持對話,好使我們可以為所有相關的病患者提供最好的善終關懷,而不需要考慮到選擇安樂死。
Table of Contents 本書目錄
Introduction 序言
Chapter 1 第一章:Health Care in China中國的衛生保健
Overview概觀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經濟和社會變化
Demographic Change人口變化
Medical Need among the Elderly老年群體的衛生保健需求
China’s Strategy in Managing Transition國家如何經營轉型的策略
Evolution of Health Care in China近代中國衛生保健的演變
The Period Between 1949 and l965; 1949年至l965年文革前夕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1965-1978年文化大革命時期
Problems of the Traditional Health Care System傳統衛生保健的問題
Health Care Reform (from 1980s) 衛生保健改革(從20世紀的80年代開始)
Emergence of Basic Health Insurance (urban) 城市基本醫保的出現
Reform in Cooperative Health Care (rural) 農村合作社的醫療改革
Current Management of Health Care衛生保健設施管理的改變
Fiscal Decentralization財政分權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System財務責任制
Government’s Price Reform政府的價格改革
Evaluation of Health Care Reform since 1978 自1978年以來衛生保健改革的評價
Overall functioning of China’s health care delivery system中國衛生保健 系統的整體功能
Disparities between China’s Rural and Urban Areas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間的差
Equity in Accessing China’s Health Care公平使用衛生保健服務
Summary概要
Chapter 2第二章: Living Through Terminal Illness in China絕症病患者在中國如何生活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Suffering中國人對苦難的看法
Chinese Cultural Beliefs中國的文化信仰
Uncontrollability世事難以控制
Ubiquity of Change世事變幻無常
Fatalism宿命論
Dualism自然界的二元性(陰與陽)
Collectivism集體主義
Utility of Efforts有毅力就有成果
Strengths and Virtues in Coping應對生活滄桑所帶來的强項和美德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Life and Meaning of Life中國崇尚的人生觀與生命意義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Good Death” 中國人對 “安樂死” 的看法
Chapter 3 第三章:Wester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aning of Life西方哲學思想如何看生命的意義
True-World Philosophy哲學上的所謂真實世界
Continental Philosophy歐陸哲學
Quality of Life生活質素
Search for Existential Meaning探索生存意義
Critique and Discussion批評與討論
Implications for the Terminally Ill對臨終病人的影響
Chapter 4第四章Hope 盼望
What is Hope? 什麼是盼望?
The Earliest Virtue盼望是人生中最早有的美德
Development盼望的發展過程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Hope中國人對盼望的看法
Western Perspectives on Hope西方人對盼望的看法
Dimensions of Hope盼望的四维
Christian Theology of Hope基督教神學看盼望
Grounding in Scripture基於聖經的盼望論
Contemporary Theology of Hope基於現代神學的盼望論
Critique評論
Pastoral Theology of Hope教牧神學看盼望
Summary and Discussion總結和討論
Chapter 5 第五章:Is Fostering Hope Justified in the Terminally Ill? 與臨終病者培育盼望合理嗎?
Ethical Consideration倫理方面的考慮
Existential Consideration存活方面的考慮
Meaninglessness and Hopefulness生命毫無意義與盼望的關連
Isolation and Hopefulness孤立與盼望的關連
Groundlessness and Hopefulness無所依據與盼望的關連
Death and Hopefulness死亡與盼望的關連
Research Consideration關乎盼望的臨床研究
Biology of Hope生物學與盼望的關連
Chapter 6 第六章:Fostering Hope in the Terminally Ill在身患絕症的病者中培育盼望
General Considerations總則
Cultural Considerations文化的考慮
Role of Physicians醫師的角色
Role of Hospice Programs善終關懷服務的角色
Role of Pastoral Caregivers教牧輔關者的角色
Where there is Hope, there is Life有盼望就有生命
Appendix: Interview Data附錄:訪談資料
Bibliography參考書目錄
Acknowledgments 鳴謝
作者非常感谢 Professor Kathleen Greider, Professor Ellen Marshall 和 Professor Samuel K. Lee三位教授在南加州克萊蒙特神學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的督導,更多謝神學院的Professor William Clements 和橙縣華人浸信會之奬、助學金的幫助方能完成這博士學位。在這多年的學習中,内子趙陳煖儀一直在我身旁幫助我,令我一無所需、專心向學。爲此我要向這些導師和親友衷心致敬。


第一章
中國的衛生保健
概觀
中國現正處於轉型期: 經濟從中央管制轉向市場體制; 從農村社會轉向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 從閉關自守轉向歡迎整個世界來北京參與2008年的夏季奧運會。國內通信與全球通信也發展奇速。隨著其它的轉變,年齡結構和國民的衛生保健需求也正在轉型。雖然中國現在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但這快速的經濟增長並不均衡,導致貧富懸殊。這差異可以在今天的衛生保健業界得以體現。
據官方統計,中國仍然主要是一個農村社會。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年來,都市的人口比例大幅增長。
表一:都市人口的增長趨勢(1980 – 2000年)
年份 | 全國人口 (百萬) | 都市人口 (百萬) | 比例 (百份率 %) |
1980 | 987 | 191 | 19.4 |
| 1985 | 1,059 | 251 | 23.7 |
| 1990 | 1,143 | 302 | 26.4 |
| 1995 | 1,211 | 352 | 29.0 |
| 2000 | 1,266 | 458 | 36.2 |
在2000年,有4.58億人登記為市區的永久居民,佔全國人口的百份之36.2(見表一)。
在1980年,中國有223個城市,其中有15個超過一百萬人口。在2000年(二十年後),中國有663個城市,而其中超過一百萬人口的卻有41個(見表二)。[1]
表二:以城市人口分類的中國城市數目
| 城市人口 | 1980年 | 1991年 | 2000年 |
| 超越二百萬 | 7 | 9 | 14 |
| 一至二百萬 | 8 | 22 | 27 |
| 0.5-1.0 百萬 | 30 | 30 | 53 |
| 0.2-0.5 百萬 | 72 | 121 | 218 |
| 少過 0.2 百萬 | 106 | 297 | 352 |
| 總共 | 223 | 479 | 663 |
這些變化部份是來自農村人口移居城市的結果,也部份是來自農村和城市地區的重新劃分。
戶口註冊對一個家庭成員來説意義重大,因爲戶口會對居民權利,例如就業和獲取社會福利,影響極大。農村人口遷移到城市,需要得到官方認可和重新註冊,從農村戶口轉到非農村戶口。如果沒有這登記,移民將很難在城市中有就業保障和醫療福利。在城市居民之中,這些沒有登記的移民,雖然還未知其確實數目,但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比率。
經濟和社會變化
中國過往二十多年來的持續經濟增長導致了人均每年可支配的收入急速上升,從1978年的RMB(人民幣)343元上升到2000年的RMB 6,280 元(約一千美元),[2] 引進了消費模式的變化。這劇變可以在家庭彩電數量的增加看到:從1985年至2000年,憑每城市一百戶來計算,彩電數量從17.2部增至116.6部。在城市居民中,即使是在最貧困的百份之十家庭,100戶中也有99部電視。在2000年中國總人口中百份之93.7都擁有電視,這就足以證明通信也隨著經濟增長而劇增。許多商品和服務廣告,包括與健康有關的,都在電視、無綫電廣播和文字媒體上出現。這普遍影響到大衆的期望。
然而,經濟增長並沒有均勻地分佈。中國東部地區的開發速度遠遠超過西部。在2000年,國内的人均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可以從貴州(中國西南部)的RMB 2,662偏差到首都北京的RMB 22,460不等。[3] 此外,不同地區還有實質上的經濟福利差別。在2000年,城市中最貧困的百份之十家庭衹有每年RMB 2,678的人均收入,與最富裕的百份之十家庭 [4](每年人均收入RMB 13,390)還有一大距離。這失衡產生不少影響,包括富裕群體的消費模式間接影響著大衆預期的生活方式。
近年來,一批一批城市貧民已經出現,其中包括失業者、部份就業者、殘疾者,退休者,和那些被解僱而下崗者。這不斷增長的經濟失衡在某程度上與就業類型日益多樣化有關。在 1980年,大多數城市的雇主都是國營或集體企業。在2000年,這兩類企業已經走下坡,受僱於私人企業的人數卻增加至一千二百七十萬(相比1995年的四百九十萬),而個體戶更超過二千萬人(見表三)。[5]
表三:城市就業人數(按僱主類型而分)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百萬人)(百萬人) (百萬人) (百萬人) (百萬人)
| 國有企業 | 80.2 | 89.9 | 103.5 | 112.6 | 81.0 |
| 集體企業 Collectively-owned enterprises | 24.3 | 33.2 | 35.5 | 31.5 | 15.0 |
| 私人擁有的公司 | — | — | 0.6 | 4.9 | 12.7 |
| 個體戶 | 0.8 | 4.5 | 6.1 | 15.6 | 21.4 |
在八十年代中期,政府引進勞動合同,取代了國有企業保證“工作直到退休”的政策,使到這些國有企業在蝕本時可以裁員下崗。因此,雖然國家統計自1997年以來,一直引述城市失業率爲百份之3.1,[6] 但如果把下崗的人數包括在內的話,1999年的失業率實則是百份之6.99。[7] 雖然女性下崗的總數沒有在比例上高超男性,但因為她們還構不成一半勞動力,所以她們的失業率實在比男性高。這些下崗者,連同其他失業者和殘疾者,構成了“城市貧民和弱勢群體”,處於社會等級的最底層。[8]
不錯,中國政府定下了城市地區最低的生活保障標準,好讓那些入息低於這標準的市民有權領受社會的經濟支持。據負責監督“城市貧民和弱勢群體”的民政部2000年調查結果,約有一千四百萬市民的入息是在當地的貧困線以下,而其中每年個人平均收入可以從 RMB 1,680元偏差到RMB 3,828元不等。貧困線是反映生活費用,也反映著市政府能否補充低收入與生活費的差異。此外,貧困線在城市範圍内的鄉郊實際上是比平均貧困線還要低得多,並且越來越多人的收入僅僅在貧困線之上。這展示出有相當數量的國民是貧民或即將陷入貧困的危險。這對國内的衛生保健具有重大意義。
人口變化
在同時,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也在迅速變化。隨著積極的計劃生育政策、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相關因素、再加上不斷上升的平均壽命,導致年輕人口(十五歲以下)比例的下降、和年長人(65歲以上)的比例上升。1964年的年長人比例是百份之3.6,到2000年已增加到百份之7.0(見表四);而超過75歲以上的比例,也從1964年的百份之0.8增加到2000年的百份之2.2,即兩倍有多。這人口老化現象預計將會持續。這將會對中國未來的衛生保健有顯著的影響。
表四:中國的年齡結構(1964至2000年)[9]
| 年齡 | 1964年 (%) | 1982 年 (%) | 1990年 (%) | 2000 年 (%) |
| 0-14 歲 | 40.7 | 33. | 27.7 | 22.9 |
| 15-65歲 | 55.7 | 61.5 | 66.7 | 70.1 |
| 65+ 歲 | 3.6 | 4.9 | 5.6 | 7.0 |
| 75+ | 0.8 | 1.4 | 1.7 | 2.2 |
老年群體的衛生保健需求
衛生保健需求的定義包括健康欠佳的存在,但也包括有效治療方法的存在。[10] 衛生保健需求的程度是視乎個人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情況、視乎病患者對自身健康的期望、視乎能否找到有效的治療措施、和視乎社會能否安排適當的角色來提供病者醫療服務和家庭護理。根據這個定義,衛生保健需求是基於疾病的負擔和社會的共識來決定有關各種支持病者的需要。這兩個元素在中國看來似乎正在改變中。
在中國各城市,老年人的醫療費佔了頗大的比率。先進的市場經濟數據提示,隨著年齡的增長,平均醫療費用也迅速的增加。[11] 超過七十五歲的病者尤其是需要昂貴的醫療保健。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老年人疾病的性質,例如流行在年長人的心血管病、癌症、以及慢性疾病。[12] 另一個原因是家庭結構的改變,令到家庭成員不能或不願照顧家裡生病的親屬。[13] 老人家昂貴的醫療費用,給予家庭關顧者(大多數是留在家裏不出外工作的婦女)沉重的負擔。
國家如何經營轉型的策略
國家經營經濟轉型的策略是採取高度財政分權。[14] 在收入方面,各級政府都可以收稅。保留了大部份的稅收後,便根據複雜多變的規則來轉付上級。此外,市或縣政府除了稅收外,也可以有大量別的資源。許多地方政府都擁有自身的企業來支付利潤或管理費。有些還擁有土地和收取地租。有了這個收入,地方政府的自主權可以很大,可以自由決定如何使用這“預算外的收入”。在這種財政分權下,地方政府可以自1980年代初開始,自由決定分配多少錢或多大的補助來支持當地的醫療機構。國家的衛生部已授權這權力給地方政府;同時,每一級政府衹需要監督比它低一級的政府。
這種財政分權有兩個重要的影響。一方面,它導致了地方政府中越來越大的資源差距:一些地方政府擁有非常豐厚的收入,而其他卻衹能勉強支付工資。另一方面,這財政分權給予地方政府很大的資源控制權,也限制了上級政府同樣的權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垂直的行政級別,從中央延伸到地方行政。地方各級政府都是或多或少地複製中央層面的結構; 例如各區或縣(甚至更高的各級地方政府)都有衛生處,不但要向當地政府交代,亦要向比它高一級的衛生處交代。在每一個行政級別,都有醫院、預防性服務、醫療機構、和健康培訓學校,而其中大部分培訓學校是直接由相應的衛生處來監督。這平行垂直通道的組織有優點、也有缺點。它建立了緊密的問責制,並且從基層建立了非常有效的預防性保健方案。此外,緊密的問責制使地方政府的衛生處很難偏袒自身的醫護人員。然而,這個系統最終產生了無數與健康相關的委會、部門和機構來托管規劃、服務、監管、問責與融資。
在如下的表五,可以看出這種高度官僚作風是很難規劃出連貫性的衛生保健發展策略。再者,這系統更是一個協調的噩夢,剩下國家民政部與各省(或省下級)的民政部門作爲“城市貧民和弱勢群體” 的安全網。
表五:對“城市貧民和弱勢群體”的醫療保健有影響力的政府機構 [15]
規劃方面 – 歸國家開發計劃委員會來負責監督制定醫療保健政策。它還負責落實五年期的區域衛生規劃。
服務、財政、監管和問責幾方面 – 歸國家衛生部負責。
雖然國務院是負責衛生改革,但因它也負起經濟和社會改革的責任,所以在國務院授權下,衛生部全面領導地方政府的衛生部門達到預期的服務績效:即每年預算有足夠財源來補助政府的衛生設施(包括公共衛生)、落實政府僱員的醫(療)保(險)、並管理和監督所有政府或私營衛生機構和醫療服務人員。
其他的監管與問責 – 歸有關的委會或部門: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前身是國家開發計劃委員會)有物價委會來制定醫療服務和健康商品的價格,故此在省、縣和市級都有類似的物價局。
•國家人事部是負責管理公務員和有公職的技工。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是管理帶有公職的半熟練和非熟練工人。該部門成立於1997年,開發了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城鎮職工的基本醫保。
•國家藥品管理局的成立,是發展與藥品有關的條例、批准新藥的使用、並監督中國的所有藥品有效和安全的使用。最初成立是歸于國家衛生部,但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政府機構,在省和以下都有相關部門來執行同一的職責。
財政方面 – 除了由國家衛生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負責以外,還有國家民政部和以下各級的民政部門提供安全網給“城市貧民和弱勢群體”。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是如何通過一個高度分權化的財務政策和高度官僚制的政府來管理人民的衛生保健。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兩者各有優點、也有缺點。在應對國民的衛生保健需求方面,成功的程度究竟有多高?就讓我們現在來看看近代中國的衛生保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的演變吧。
近代中國衛生保健的演變
近代中國衛生保健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從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到1965年文革前夕; (2)從1966年至1977年文化大革命時期; (3)從1978年經濟改革開始到現在。
1949年至l965年文革前夕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由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中國繼承了有待發展的衛生制度。[16]
提供衛生保健的人物主要是使用草藥、針灸和中國傳統醫療方法來治理病人的中國傳統醫師(中
醫)。西醫數量相對較少,主要是在市區的醫院工作。
在1951年新政府國務院舉辦了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宣佈了以下的衛生政策:[17]
•醫療服務必須是為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和士兵)而設
•預防必須勝於治療
•醫療服務必須結合中國傳統和西方醫術
•醫療服務必須配合人口的移動
從20世紀50年代初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現有的醫療設施進行了翻新;每個城市和市區都有新的“人民醫院”和預防性的衛生設施。一些工業,例如採礦、鐵路和電信與軍事組織都設立了自己的醫院;到了1965年,位於市區和附近的醫院數目已達1500左右,[18] 都是為這些行業的在職員工和家屬服務。此外,幾乎每一個政府機構、企業和學校都有健康診所來提供很基本的預防和治療服務,也有培訓護理人員在社區診所服務,作為第一線的衛生服務員。因此,市區的衛生服務網絡有大大的擴展。
同時,培訓能力也有迅速的擴展。醫學院和藥劑學院的畢業生數目從1949年的1314增長到1965年的22,027。因此,到了1965年,中國的西醫數目增加了五倍,而藥劑師的數目也從近乎零上升到8000。[19] 即使政府不斷努力部署更多的專業衛生人士在農村服務,但大部份的醫生和藥劑師都是在市區的醫院或衛生設施受僱。
應該指出的是,在20世紀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中國的市區衛生保健發展主要是跟隨蘇聯採用的模型,直至中國和蘇聯之間的友誼結束。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大部份被僱的市區居民都是受益於50年代的傳統衛生保健系統,直至90年代中期的衛生保健改革。具體來說,這傳統衛生保健系統的管理是通過兩種不同的保險體系:(1)政府資助的衛生保險體系(government-funded insurance scheme GIS),保障受僱於政府部門或機構的在職人員和家屬,並且包括傷殘軍人; (2)國有企業的職工衛生保險體系(labor insurance scheme LIS)。國有企業是以超過100員工受僱於工廠或企業(例如鐵路、採礦、交通運輸和郵政等)為準。參保職工享受幾乎免費的衛生保健,治療不論與工作有否關係的疾病、損傷和殘疾。他們只需支付較昂貴的藥物費用,而直系親屬的手術費和一般藥物費用將由國有企業支付一半。在這中央管制的經濟體制下,就業的職工受益良多,令到絕大多數住在市區的居民在衛生保健方面有顯著的改善。
相反地,農村地區的衛生保健體制是由當地農民合作社在1950年代中期推出,隨後得到中央政府的肯定。[20] 這體制設立了衛生保健基金,由當地公社或生產隊的成員資助,再加上公社或生產隊的直接津貼來補助。村民所接受的治療或處方藥物都是免費或價格低廉的。然而,在農村地區服務的醫療人士數目有限,都是處於鄉鎮和縣級的小診所。
這衛生保險體系的分岐造成了城市與鄉村區域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在城市受僱的員工可以享受到城市所提供的傳統衛生保健,但農村人口大多數都仍然不能充份地享受到基本醫保。
1965-1978年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5年毛主席發表了著名演說,批評衛生保健服務偏袒著城市地區人口,呼籲根本改變這優先次序。大約在同一時間,毛澤東和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政治盟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接下來的十年帶給中國大幅的政治和經濟動盪。
新成立的衛生局開始進行優先發展農村衛生保健的政策,導致了大量培訓 “赤腳醫生”— 即又是農民、又是農村醫生– 在提供農村衛生保健、建設農村衛生設施、和重組農村合作社來資助農村衛生服務這幾方面都起了關鍵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在醫療衛生工作者人數上減少城與鄉之間的不平等。這導致了許多城市培訓和研究中心的關閉、和高層次醫學教育的重組。培訓醫生(包括公共衛生醫生)的期間由五年減為三年。許多城市醫院的醫生都被派到農村去提升農民的衛生保健、並監督缺乏訓練的農村衛生保健工作者。即如在1969年,中國西部的甘肅省就派出一半城市醫生到農村衛生設施來。[21] 同時,新畢業的醫生和公共衛生專業畢業生都被自動分派到農村設施。因此,在農村地區的合格醫生人數幾乎在十年內增了一倍,而護士人數也增了137%。再者,在建設衛生保健設施方面,農村的數目也超越了城市。到了1975年,超過85%的農村居民在他們的村莊都有一個衛生站。到了1976年,約90%的農村居民都加入了合作社的衛生保健體制。[22]
綜合評估文革後的衛生保健體制,可以說是有壞也有好。在某方面,許多城市的衛生保健發生了整體的質量惡化,原因是涉及轉介到城市診所和醫院的制度崩潰。並且,有許多醫療機構,包括醫學院或藥劑學院,都無法有效地發揮其作用,以致影響到教育和研究的質素。但在另一方面,中國農村人口的健康狀況實在有顯著的改善,這可以歸功於調派更多的合格醫生下鄉、培訓更多的“赤腳醫生”、和進一步發展農村合作社的衛生保健體制。
傳統衛生保健的問題 [23] 在傳統的衛生保健體制下,凡是工人,如果是享有政府或國有企業所資助的醫保(GIS / LIS),都可以得到不錯的醫療服務,包括免費的診斷和治療(手術與一般藥物)。不錯,在中央管制的經濟系統下,廣大城市居民可以有基本醫保的保證,促進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但是,隨著農村合作社經濟體制的瓦解、分權決策的開始、管理方面問責制的引進、以及私營企業的出現,傳統的衛生保健體制便在20世紀70年代末出了問題 。
第一,因爲醫療服務的供應和使用失控,導致醫療費用高、效率低、和浪費大。[24] 在醫學方面嚴格來説,估計約有20%至30%的全國醫療費用被認為是不必要的。衛生保健在需求方面,消費者過度使用醫療服務,而在供應方面,由於當地政府越來越少資金來支持醫院,所以醫院不得不倚靠採用高端醫療器材和出售藥物來增加利潤,以支付營運費用。[25] 不少醫院僱用的醫生都點上不必要的診斷測試或過度開藥方來增加醫院收入。這進一步增加了整體醫療費用。第二,基於免費或低廉的廣泛工人醫療福利,政府和企業的庫房都快要被倒空了。[26] 第三,由於衛生保健與就業掛鈎,所以不同的企業僱員會有不同水平的醫療服務。這間接減低了勞動力的流動、妨礙了勞動市場的發展。第四,企業沒有試圖合拼它們的風險和資金來支付工人的醫療費用。[27] 所以當企業遇到資金周轉困難時,它們只能減少衛生保健的供應,或遲遲不付醫療費用的欠款。因此,許多工人沒有得到他們應得的基本衛生保健。第五,儘管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發展迅速,受僱企業的職工仍無法享受基本衛生保健。[28] 綜上所述,有利於城市居民的傳統衛生保健體制(GIS和LIS)帶來昂貴的醫療費用、帶給國庫和企業沉重的財政負擔、妨礙了勞動力的流動、減低了抗風險的能力、和引致受益者不平等的待遇。
在農村方面,隨著合作社經濟模式的分化和人民公社的解體,合作社的衛生保健體制也崩潰了,令到農村人民處於困境。隨著鄧小平1978年的經濟改革,醫療改革也隨之而來。
衛生保健改革(從20世紀的80年代開始)
從80年代開始,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和企業開始採取改革衛生保健體系的措施:[29](1)要求工人與他們的僱主一同負責工人們的醫療費用;工人的自付費通常約為10%到20%的醫療費用,並設定上限額;(2)引入按人頭計的固定支付系統 – 每年企業按照員工的數目給予醫療服務人員固定的金額來照顧員工;[30](3)在1989年,一些城市開始統籌基金來建立醫保,作爲支付退休人員或有嚴重疾病的員工之醫療費用;[31](4)在1993年,再加添個人醫療帳戶到這醫保來幫助員工支付未來的醫療需求。[32] 然而,這一切的改革措施還是在傳統的保健制度框架內進行,所以對廣大民眾利益不多。[33]
城市基本醫保的出現。多年來,中國都是採取漸進方式來實現各方面的改革,例如經濟改革和勞工改革。衛生保健改革也不例外。 在1996年,國務院主辦了全國會議來討論基本醫保;結果有超過五十個城市成為這推行改革的首批城市,[34] 結合了上述的改革措施到這測試策劃中。其結果令人鼓舞。因此,國務院於1998年12月頒佈了一項可説是里程碑的法令,名爲“關於設立城市職工基本醫保的決定。”其次在1999年融合了政府保險計劃(GIS)和國有企業保險計劃(LIS),建成“城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簡稱基本醫保)。口號是“低水平、廣範圍“ 。[35] 該衛生保險改革的基本目的是以相對低廉的成本,提供更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來達成滿足城市職工的基本醫療需求。
總括來説,這醫保的資源是來自社會統籌基金和個人醫療賬戶,而管理方面,是交由當地政府的社會保障行政部門管理,而不是由僱主自行管理。所匯集的資金來自僱主和受僱者所繳納的保險費。至於個人醫療賬戶,其目的是鼓勵職工為他們未來的醫療需求作好準備。這樣一來可控制過度使用醫療服務的浪費,二來確保僱主和受僱者一同支付衛生保健的費用。
在這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下,職工可前往指定的衛生保健站進行診斷和治療,跟著可慿處方在醫院的門診藥房或指定的藥品零售商買藥。這些定點都是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所認可,必須要先與當地政府的社會保障部門簽訂了論人計酬的合同,才可提供衛生保健服務。
這基本醫保本意是覆蓋全國所有在企業、機構、和政府機關工作的城市職工。為了確保公正和發揮職工的自發性,凡顯著對社會有貢獻的都可從政府或國有企業所附設的補足保險得到額外好處。凡染有嚴重疾病的也可享受這補足保險。此外,如果僱主能夠負擔得起,商業保險也可提供另一層的幫助。不幸的是,那些失業的、殘疾的和那些因疾病已用盡了一切保險渠道的,衹有求助於政府為貧困線下的人民所設立的醫療救助了。
除了基本醫保外,這個衛生保健改革還有兩個主要部分:改革醫療機構和改革藥物的生產與流通體制。鑒於本論文的目的,筆者不會進入其中細節,只説及以下幾點革新便足夠了:
•降低醫務人員的總數,但提升他們的質量和效率
•設定醫療服務費用標準
•積極發展社區的衛生保健服務,改善大衆享受醫療服務的途徑,並將這些服務納入基本醫保的利益中。
•分開藥物管理和醫療服務管理
•阻止醫生過度開藥方:限定醫療機構從處方藥物進賬的收入不能超過一定比例的醫院總收入。
•用集中招標的方法來鼓勵藥品批發商投標
•鼓勵非處方藥物特許在專賣店櫃檯或超市作零售。預計醫院藥房將最終轉為獨立的零售藥店。
•藥物價格將用國家所定的標準來劃一制定,並且政府會指定基本醫保所認可的處方藥物,好使病患者得以報销。
•規定藥物要在其包裝上打上零售價的印,以防價格欺詐,並且必須在銷售的每一個階段中在發票上標明實際的銷售價。
這個醫療改革有一些顯著的變化。首先,衛生保健現已被視爲一種行業。衛生局和醫院之間的上下級行政關係已被廢止。衛生局的現任職務是監督,而醫院所擔當的角色是提供醫療技術和服務。以前衛生部管理醫院,但從這時起,衛生部只負責監督醫療機構的行業水平。其次,醫療機構現已被列為牟利和非牟利經營:非牟利機構可以接受稅收優惠待遇;而牟利機構則可以自行設定費用表,但必須依法納稅。政府也有經營一些非牟利醫療機構,並且會提供津貼。再者,此時已成立了一個由社區衛生中心、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所組成的廣泛服務系統,務求促進醫療機構的轉型、配搭、合併和分組,從而確保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
隨著改革帶來的競爭,醫院領導的管理水平、醫師對醫藥費的意識、和醫院服務的質量都得到提升。[36] 此外,醫院需要簡化其操作或與其他醫院合併才能保持競爭力。
農村合作社的醫療改革。隨著城市醫療改革和農村集體經濟的解體,農村合作社和生產隊所支持的舊式衛生保健制度需要修改。迫切問題是:中國有9億農村人口,其中7億多留在農村,生活條件很差。[37] 在2003年,衛生部、財政部和農業部聯合頒佈了“關於建立新型農村合作式衛生保健制度的通告”。[38] 根據這份通告,新型的合作式衛生保健制度是由政府規劃、引導和支持; 資金是來自不同渠道(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農村的各類合作社)。個人加入與否是出於自願。
在此統籌方案中,每個農民衹要每年交付至少10元(USD1.25)到他/她的個人醫療帳戶作保險費,政府(中央和地方)和農村的各類合作社則會另行注入40元(5美元)到該帳戶。此後政府每年將為他/她支付上最多65%的醫藥費。若是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保險費可能會高一些。至於受僱於鄉鎮企業的職工,將由縣政府決定他們是否應該參加城市基本醫保或農村新型合作式醫療保險(從此簡稱為新合作式醫保)。
這個新合作式醫保的基金主要是用於巨額醫療費用和住院費用。若受保者一年内沒有動用 這基金,這合作式醫保准許受保者定期體檢,費用由該醫保負責。當地的縣政府會設定這體檢的費用表,和那一些檢查項目是適合這個體檢,而藥物費用表則由省政府或同階層的政府來確定。
從2003年起,隸屬中央政府的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必須至少選擇兩個至三個縣(或市)來作改革測試地點。獲得必要的經驗後,才逐步擴大這個農村新合作式醫保到其他的縣。若不能滿足這要求,縣方仍可協調鄉鎮裏實施新制的初級階段。最終的目標是讓農村新合作式醫保在2010年在全國施行。
因此,總括來說,中國的醫保是多元化的和多層面的。多元化是因為衛生保健資金是來自政府、企業、工人本身和捐贈。多層面是因為醫藥費的支付是來自個人儲蓄(個人醫療賬戶和個人資金);家庭援助(作補充);企業保險(作補充);商業保險(作補充);社會統籌或合作社匯集(例如保險費)和經營(通過企業、機構和合作社相互配搭)的基金;和政府援助那些在貧困線下生活的醫療津貼。
中國有這樣一個多元化、多層面的醫保主要原因有二。首先,由於社會統籌的基金僅覆蓋基本衛生服務,所以需要有空間來容納其他不同類型的保險,來適應收入水平和醫療需求的差異。其次,爲了保證新舊系統的交替和穩定醫療改革的實施,各地區、行業和企業實應繼續提供高於基本衛生服務的多層醫療保險。。
截至2002年底,約有6926萬職工和2474萬退休人士加入了城市基本醫保。[39] 受保人數的增加證明了基本醫保已獲得充份的動力。至於農村新合作式醫保的評價仍為時尚早:由於其微薄資源,這新合作式醫保僅覆蓋住院費用(並且有非常高的自付金額),令到農民沒有足夠的基本衛生服務和藥物覆蓋。
衛生保健設施管理的改變
財政分權
在1980-2000年,大多數的中國地方政府都一直沒有把衛生保健的發展視爲一個優先事項。發展地方經濟始終優勝於衛生保健和其他社會服務的發展。自從20世紀的80年代開始,經濟改革帶來財政分權,導致政府補助與醫院總收入的對比顯著下降。在2000年,這比例平均來說只8.7%醫院總收入(見如下表5,清楚的顯示出中國醫院的收入來源在1980-2000年内如何的改變)。
表5: 1980-2000年中國醫院的收入來源 [40]
| 項目(年份) | 1980 | 1985 | 1990 | 1995 | 2000 |
| 醫療服務收入 % | 18.9 | 22.2 | 28.6 | 34.7 | 40.2 |
| 藥物收入 % | 37.7 | 39.1 | 43.1 | 49.8 | 47.1 |
| 政府補助 % | 21.4 | 20.2 | 11.6 | 7.5 | 8.7 |
| 其他收入來源 % | 22.1 | 18.6 | 16.7 | 7.9 | 4.0 |
| 總收入(CNY億元) | 292.6 | 428.6 | 702.2 | 1,003.4 | 2,296.5 |
表6:中央政府在國民衛生保健所支出的款項,與國民衛生保健的總支出之對比百份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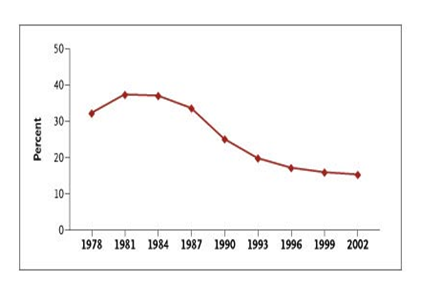
明顯地,從1978年到1999年,中央政府在國民衛生保健的總支出中所佔的比例從32%下降到15%(看表6)。[41]
財務責任制
正是因為財政分權化(導致政府的補助日減),醫院和其他衛生機構需要向病患者收取更高的醫療服務費來增加收入,以便應付日益增加的營運成本。在2000年,隨著政府補助的大幅下降,醫療服務收入大幅上升至醫院總收入的40.2%(見表5)。
基於財政分權和財務責任制的發展,衛生機構也在管理上,無論是關乎財務、人事或醫療服務,獲得更多的自主權。
在財務上,若果衛生機構的生利活動有盈餘,管理人有權決定多少來支付獎金、多少來投資作進一步的發展。在職工的支持下,管理人可以有系統的來將獎金支付給不同級別或類型的職工。
在人事上,衛生機構的管理人在徵聘和解僱兩方面將會有更大的發言權。越來越多的醫科專業人士是靠合同來執業,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得到“鐡飯碗”(即永久性工作)。整體來說,在短短的二十年内,許多衛生機構的人力資源管理層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要達到高質的服務效能,實在還有一段距離。
在醫療服務上,衛生機構的管理層經常有策略性的開發新的衛生服務(例如購買新的高科技影像設備),以便增加醫療設施的收入和利潤。在某範程度上,中國許多的衛生機構服務是由利潤所驅動,而不是符合當地人民的需要。中國大多數的地區性和三級醫院都購買了CT掃描儀來增加利潤。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因爲需求不斷的上升,CT(計算機斷層)掃描儀的售價曾經遠超其成本。
在提高生產率的同時,由於衛生服務的成本高升和使用率下降,大部份的醫院管理層都紛紛頒佈獎勵機制,來激勵部門、單位和個體的職工來達到收入預算的目標。大多數醫院最初都是鼓勵醫師和其他衛生服務專業人士增加醫療服務的使用率,並向病患者推銷藥物來增加收入。這意味著醫師從這兩方面所產生的收入越多,他們每月所得的獎金就會越多。這樣的激勵確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然而,過度開藥與過度使用高科技診斷測試和治療都大大提高了衛生保健的成本,使病患者對主治醫師的信任降低。[42] 近年來,這些問題已被確認;因此,一些提高成本效益的措施,包括病患者的滿意度,已被採用來扭轉局面。
政府的價格改革
在經濟改革之前,政府衛生保健服務和藥物的價格都很低,使絕大多數人民都能負擔得起。從八十年代初,中國政府開始提高衛生保健服務的價格,這都是因爲政府的經濟支持實在有限。要使衛生保健機構避過赤字,唯有提高價格來反映實際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衛生保健服務和藥物的價格都有新的制定。在中央物價局帶領下,省和市政府的有關部門都要根據當地情況來制定和頒發更高的醫療費用表,令所有公共衛生保健機構來實施,並要求縣級以上的公立醫院自行監測這定價方案。
自1978年以來衛生保健改革的評價
這一連串的事件 – 政府財政分權、衛生保健機構財務責任的增加、與企業和農業經濟的私有化- 最好從以下三方面來理解:[43](1)中國衛生保健系統的整體功能; (2)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間的差距; (3)使用衛生保健服務上的公平問題。
中國衛生保健系統的整體功能
2001年的調查顯示出:在三個被挑選出來的代表性中國省份中,有一半的居民說在過去12個月裏他們已經放棄了衛生保健,原因是因為他們付不起昂貴的費用。[44] 在2002年,只有29%居民(包括城市和農村居民)有健康保險,並且自費的支出佔了全國衛生保健的開支58%,與1978年的20%相比分別很大。[45] 從1978年到2002年,隨著醫療費用的迅速增長,個人用在衛生保健的每年平均支出增加了40倍,就是從11元人民幣增加到442元。總體而言,在衛生保健的各類型裏(包括公共衛生),國家支出從3.0%GDP(生產總值)上升到近5.5%。因爲銷售藥物和提供高科技服務的盈利高,所以這些項目都被廣泛濫用。相對起來,中國的衛生保健支出有一半(50%)是用在藥物,而在美國卻是10%。[46] 在西方資本的支持下,一個新的營利性醫療行業已經出現,在舒適豪華的新設備裏,為中國的城市暴發戶提供西式的醫療服務。在此同時,中國的衛生保健效率急劇下降。隨著私營醫療機構的增長,中國的醫療衛生設備和員工數量從1980年起都有顯著增加,但由於使用上仍有障礙,令到衛生保健服務的生產率下降。[47] 這情況不止發生在中國;在美國而言,也面對同樣的現像 – 成本急劇的增加、個別地區的醫療服務質素和使用失去平衡、效率普遍下降、普羅大衆付不起昂貴的醫藥費 – 這些聽起來都令人沮喪。[48]
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間的差距
在中國的市場化醫療體系,消費者的財富是他們是否獲得高質量服務的關鍵預測指標。既然城市居民的收入比農村居民高達三倍,城市居民所享受的醫療服務肯定遠遠超過農村居民。 在1999年,中國城市居民中有49%享有衛生保健保險,而農村居民整體上衹有7%,甚至在中國西部省份最貧困的農村更是衹有3%左右。[49] 此外,正因爲在農村地區的衛生保健設施在質與量和人員方面都有不足,不如城市社區,所以農村居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一待遇。説來也不令人驚奇,這個問題是世界性的。在中國,一貫在農村工作的赤腳醫生,其實並沒有什麼特殊醫療訓練。他們作爲農村居民的醫療護理者,維持生計的方法往往是靠賣藥物或提供靜脈注射。這靜脈注射在中國是一項非常流行的治療方法,不論什麽奇難雜症都用得上。[50] 據估計,在農村地區所賣的藥物有三份之一是假的,[51] 給藥物供應者帶來豐厚的利潤。
農村居民既然意識到他們的衛生保健在質量方面都比不上城市,所以有重病時,都會經常繞過當地的醫療人員和設施,在城市醫院的門診部尋求醫治,不止浪費了當地的醫療設施和服務,還過度使用城市的醫院或門診、付上高昂的醫藥費、增加了自己的經濟負擔。 高昂的衛生保健支出可説是農村地區貧窮的主要原因。不少農村居民都想遷移到城市,尋求更好的的工資和衛生保健。[52] 地區的貧富差異也深刻影響到地方的公共衛生開支,例如上海的開支就比最貧窮的農村地區高出七倍。[53]
衛生統計顯示城市和農村間的經濟實在有顯著的分歧,而兩者的衛生保健設施使用率也有顯著的分歧。這都反映在兩者的公共衛生開支上。1999年在農村地區的婴兒死亡率為生育成活率的千份之三十七,而城市地區則只是十一。2002年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在農村地區是千份之三十九,而在城市地區則是十四。同年,母親死亡率在城市和農村分別為十萬份之72和54。也許最令人震驚的,是一些貧困農村地區的嬰兒死亡率最近有增無減,反而在城市地區這死亡率仍繼續下跌。再者,過去已受控制的一些感染性疾病,例如血吸蟲病,又死灰復燃了。[54]
這樣的中國衛生保健差距可能就是引起部份農村居民對政府、對共產黨、和對新貴富豪越來越感到憤怒的一個重要原因,也造成日益頻繁的農村地方暴動和騷亂。[55] 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權易手(例如共產主義革命本身)就是出於貧窮農民的不滿。城市和鄉村之間的衛生保健差距所造成的後果,實在值得當前中國政治領導者深切的注意。
公平使用衛生保健服務
人民能否享受到公平、劃一的衛生保健服務,這一直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要獲得衛生保健,一直都是基於就業 – 就如就業狀況、表現、僱主的參與 – 和所居住的地方;即是根據戶籍列爲農村或城市居民。傳統的衛生保健制度(即政府保險制(GIS)和勞工保險制(LIS)的結合),是專為城市職工而設,而在1998年所推出的基本醫保,也只是延續這基本特徵而已。
儘管如此,中國城市的衛生保健制仍然是排斥了(或保護不了)那些沒有保險和保險不足的居民。顓慧琳的文獻找出五個弱勢群體:在2002年,山西省估計共有200萬員工或不同狀況的前員工是屬這弱勢群體,另外還包括58萬已受政府援助的貧窮人,其中大部份都是老人或慢性病患者。雖然政府保證給他們某程度的生活津貼,但在新推行的基本醫保下,他們還是得不到衛生保健的利益。[56] 這五組人分別為:(1)任職於虧損企業的員工; (2)失業工人; (3)養老金低微的退休人士; (4)殘疾人士; 和(5)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居民。這五組人看來都很有可能是因為經濟開放後因爲就業狀況欠佳的受害者。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在那個時候已經是比其他省份有更多的城市貧民,[57] 但這衛生保健收益問題並不單是關乎山西省,而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即使在中國的首都北京,也曾經報導了類似的情形。在2001年,負責扶貧與協助貧困和弱勢群體得到社會福利的民政局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有四份之三的受訪者選擇了即使有病也不就醫;四份之三自付醫療費用; 而只有12.2% 的受訪者有參與基本醫保。[58]
這些調查結果並不希奇,這是因為衛生保健改革還是基於人民的就業狀況,所以改變不了中國的醫療系統。更糟的是,經濟改革也帶來了龐大的入息差異。雖然中國在200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1000美元 (按現行匯率記算)的門檻,跨上一個重要臺階,但許多弱勢群體仍然沒有醫保或是保險不足。[59] 這並不是說衛生保健改革並沒有分毫緩解到不平等的醫療服務受益; 有證據表明,當病重時需要醫療,一些經濟較低微的社會群體仍然在受益方面處於不利地位。[60] 儘管他們的利益在横平層面上已得進展,但在公平獲得基本衛生保健利益的豎直層面上還需改善。
概要
衛生保健服務需要適應需求不同模式的變化。出生率下降導致孕產婦和兒童保健服務的需求也下降,而人口老化所產生的多種服務需求也未能達成。此外,越來越多的城市貧民和社會福利顧不及的民眾與大量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人口也創造了很多新的需求。因此衛生保健機構和設施需要加強本身的監測能力和應對這新的需求。
基本醫保是政府在資助城市衛生保健服務上戰略性的核心。其最終目的是幫助所有城市建立基本醫保。較富裕的城市可以補充這醫保。國家所面臨的挑戰是說服年輕工人,令他們覺得自己將會最終從中受益,否則他們會認為這醫保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稅收。基本醫保當下並不包括員工的家庭成員,而留在家裡不外出工作的中年和老年婦女,更有可能不能受益。此外,這基本醫保只是局部覆蓋慢性病的門診治療費,令到這些家庭經濟負擔沉重。實際上,從長遠來看,病好不了要入院接受昂貴的治療可能會花費更多。
除非更改提供衛生保健服務的體制,任何醫療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目前依賴急性護理醫院的住院治療和治療慢性疾病的費用都是非常昂貴的,實在需要更多和更優良的社區初級保健護理和設施與改進醫院管理層的成本效益,包括合理使用高科技的診斷測試和昂貴的藥物。
此外,中國需要有多元化的健康保險計劃,好使有需要的居民可以適當地選擇他們自我的消費能力。政府衛生局或部門也需要加強監督醫療設施和調節它們的的性能。市政府最好能積極策劃發展自己城市的衛生保健服務,也需要讓市民知道他們可以選擇的保健項目。
人口老化在衛生保健來説是一個特殊的挑戰。比起那些目前享受到全保的人,在大多數城市裏老年人都很難獲得那種以醫院為主的衛生保健服務。如要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城市最好是通過初級保健和社區支持,讓他們在家中或養老院得到照顧。若單靠年輕一輩的工人和僱主完全承擔醫保費,任何健康保險計劃都會承擔不了。在該種情況下,政府應該承擔部份費用,否則整個健康保險計劃都可能會落空。
可以肯定的是,要想每個人都有醫保, 還需要一些時間,但政府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保護那些未能享受到醫保的人民,例如政府可以充份資助社區的初級保健和疾病預防措施、鼓勵門診設備的發展和有效運作、監測和管理醫院的業績、減低藥物和醫療服務的濫用、和教導民眾他們可以選擇的各種保健措施。在民政局的領導下,政府已開始為窮民(尤其是有慢性病患者)的衛生保健設立一個安全網,好使他們能夠充份獲得基本衛生保健的機會。
城市周邊的許多地方現正越來越城市化,而城市衛生部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為這些逐步融入城市範圍的人口提供服務,包括如何創建衛生保健設施、組織城市服務網、發掘財源、和繼續改革衛生保險。正如前所述,農村人口遷徙到城市的數目實在難料,但肯定是不少。市政府應負起為這些人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原因有二:首先,這些遷移之民也是和納稅人一樣應享有社會福利;其次,在公共衛生方面,政府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傳染病的繁殖。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已在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期間有很分明的展示。市政府應鼓勵僱主為這些從農村來的工友提供基本醫保。問題是:當這些工人囘農村之時,他們能否轉移其醫療福利?
在過去的20年裏,正因為相當迅速和成功的市場經濟轉型過程, 政府總是相當被動的來應對城市的衛生保健問題,其中包括醫療費用的急劇上升。許多市民開始擔心他們如何支付重病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此外,當有迫切醫療需要時,衛生保健的受益又是否足夠和公平?這仍然是一個問題。政府已承諾對這些問題優先考慮,有待將如何達成。
第一章參考目錄
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1).
[2]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 Tables 10.3 and 10.9.
[3]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Table 3.9.
[4]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Table 10.5.
[5]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Table 5.4.
[6]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Table 5.1.
[7] Edward Gu, “Labor Market Insecurities in China”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Publ., 2003),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es/download/docs/labour_china.pdf (accessed May 14, 2008).
[8] Sarah Cook and Susie Jolly, “Unemployment, Poverty, and Gender in Urban China: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Laid-off Workers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IDS Research Report, No. 50 (Brighton, England: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Chun-ling Li,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a’s Urban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3, no. 1 (2002): 91-99.
[9]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1.
[10] Alan Williams, “‘Need’ – an Economic Exegesis,” in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ed. Anthony J. Culyer,vol. 1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Pub., 1991), 259.
[11] Morris Barer et al., “Aging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New Evidence on Old Fallaci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4, no. 10 (1987): 851-62.
[12] Ai-hua Ou and Yan Zhu, “Analysis of Condition of Elderly People and Their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in Guiyang City,” Chinese Primary Health Care 14, no. 3 (2000): 47-8; Li-ping Zhou and Rui-zi Wang, “Analysis of Health Need and Utiliza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Hangzhou City” [in Chinese], Journal of Zhe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27, no. 2 (1998): 84-87.
[13]Yue-gen Xiong, “Social Policy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Ageing in China: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fare for the Aged, 1 (1999): 107-22.
[14] World Bank, China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b-National Finance: A Review of Provincial Expenditures, Report No. 22951-CH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2).
[15] Gerald Bloom and Sheng-lan Tang, eds., Health Care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14.
[16] Joshua S. Horn, Away With All Pests: An English Surgeon in People’s China: 1954-1969, chap. 8(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70.
[17] De-quan Li, “The Right Direction in Providing Health Care for the People” [in Chinese],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First 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 Beijing, Aug. 7-19, 1950, reported in People’s Daily Oct. 23, 1950, Editorial,http://read.woshao.com/400327 (accessed May 25, 2009).
[18] Bloom and Tang, 18.
[19] Bloom and Tang, 18.
[20] Dong-jin Wang, e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ese] (Beijing: Falu Press, 2001), 278-79
[2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System in Gansu Province” [in Chinese], Gansu, 2000.
[22]Wa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278-79.
[23] Chack-kie Wong et al., China’s Urban Health Care Refor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6), 14.
[24] Dong-jin Wang,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Sufficiently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of th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for Urban Staff and Workers” [in Chinese], China Labor 158 (Jan. 1999): 4-7.
[25] Xiao-wu Song and Hao Liu, “The Reform of th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and Accompanying Measures,” in Report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ese], ed. Xiao-wu Song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1), 83-106.
[26] Pei-yun Peng, Reform on Health Care System for Staff and Workers [in Chinese], report prepared for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Gaige, 1996), 3-21.
[27] Ibid., 4.
[28] Ibid., 3.
[29] Jia-gui Chen and Yan-zhong Wang, “The Report on China’s Urban Health Care System,” in Chin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 1997-2001 [in Chinese], ed. Jia-gui Che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Press, 2001), 81-82.
[30] Song and Liu, “Reform of th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89.
[31] Ibid., 90.
[32] Ibid., 91.
[33] Chen and Wang, “Report on China’s Urban Health Care System,” 82.
[34] Chen and Wang, “Report on China’s Urban Health Care System,” 83.
[35] Lan-qing Li, “The Reforms of the Basic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Health and Medicine System for Urban Staff and Workers” [in Chinese],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
3124/node3125/node3127/userobject6ai269.html (accessed May 24, 2009).
[36]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Investigative and Analytical Report on the Reform of th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Zhenjiang, Changshu, and Shanghai” [in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Nov. 11, 2001, 11.
[37]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Rural Medical Care System to Insure Farmers’ Health,” information pamphlet publ., March 30, 2006, http://www.china-embassy. org/eng/ xw/ t243199.htm (accessed May 14, 2008).
[3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ircular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Style Rural Cooperative Health Care System” [in Chinese] promulgated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Health,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Jan. 10, 2003.
[39] Chack-kie Wong et al., China’s Urban Health Care Reform, 123.
[4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Health, Annual Report, Beijing, 2001.
[41] Yuan-li Liu, “China’s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 Facing the Challeng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 ation 82 (2004): 532-38.
[42] Therese Hesketh, and Wei-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The Healthcare Market,”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 (2004): 1616-18.
[43] David Blumenthal, and William Hsiao,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The Evolving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3, no. 11 (2005): 1165-70.
[44] Meng-kin Lim, Hui Yang, Tuo-hong Zhang, Wen Feng, and Zi-jun Zhou, “Public Perceptions of Private Health Care in Socialist China,” Health Affairs 23 (2004): 222-34.
[45] Yuan-li Liu, Ke-qin Rao, and William C. Hsiao, “Medical Spending and Rural Impoverish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21 (2003): 216-22.
[46] Hesketh, and Zhu, “Health in China,” 1616-18.
[47] Liu, Rao, and Hsiao, “Medical Spending and Rural Impoverishment in China,” 216-22.
[48] Blumenthal, and Hsiao, 1165-70.
[49] Yuan-li Liu,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9 (2004): 159-65.
[50] Hesketh, and Zhu, “Health in China,” 1616-18.
[51] Jim Yardley, “Rural Exodus for Work Fractures Chinese famil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04, A1.
[52] Ibid.
[53] Blumenthal, and Hsiao, 1165-70.
[54] Jim Yardley, “Xin-min Village Journal: A Deadly Fever, Once Defeated, Lurks in a Chinese Lak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005, A4.
[55] Joseph Kahn, “China’s ‘Haves’ Stir the Have Nots’ to Violenc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04, A1.
[56] Hui-lin Zhuan, “Urban Deprived Groups in the New Era: Stud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 Care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Chinese], Market and Population Analysis, May 23, 2003, 18-19.
[57] Ibid., 20.
[58] Zhong xiang Liu, “A Study of the Problem Related to Medical Assistance for Urban Poor,” Table 2, Sociology Department, Renmin’s University of China, 2003.
[59] Pei-lin Li, “Problems and Trend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http://chna.com.cn/chinese/zhuanti/2004shxs/483054.htm (accessed 14 May, 2008).
[60] Gordon G. Liu et al., “Equity in Health Care Access: Assessing the Urban Health Insurance Reform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 no. 10 (Nov. 2002): 1779-94.
第二章
絕症病患者在中國如何生活
2007年12月一個寒冷的冬日,我的朋友亞炳來小鎮的汽車站接我一同去探望李氏一家。[1] 他們住在郊外,巴士去不到,衹有靠亞炳的摩托車。鄉村小路都是沙泥路,摩托車過後都是沙塵滾滾。路上的村落都沒有路標,屋子也沒有門牌,所以若果沒有亞炳帶路,我一定會迷失路。路上不時見到農民手緊緊的握著韁繩,以防黃牛跑掉。在農民來説,耕牛是他的命根,售價是以萬元計算。也見到一些農民挑著擔子,載著肥田料囘去農耕,或載著新鮮瓜菜到鎮賣。路上一些魚塘養了不少鯉魚、䲞魚、鯰魚和鱸魚。魚塘旁有外厠,人的排泄物就直接流進魚塘,完成了自然的有機性循環。
我們很快就到達目的地。在我們前面有幾棟未上漆的紅磚房子, 看來已經是抛空了一段時間。我們停放摩托車在附近,沿著屋與屋間的狹窄石頭巷子往前走,來到一個殘破的房子後面。我們停下敲門。一個滿頭銀白髮的女士應門,與我們打招呼。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李太。她額頭佈滿皺紋,看來疲憊殆盡,眼肚滿是黑圈。我的朋友亞炳曾告訴我李太大約是四十多歲,但看起來她比她的歲數還老。房子裏彌漫著很重的中藥氣味。在相鄰的廚房裏,鍋正沸騰著煮藥。客廳變為臥室,傢俬很少。在左邊靠近窗口處是李先生的床。他正閉著眼睛。看來,他真是瘦得皮包骨一樣。
“你好嗎?李先生?” 亞炳說。
李先生睜開眼睛,回答說, “還可以。” “”
“你昨晚睡得如何?”亞炳說。
“還是一樣,難以入睡。”
“是嗎?”
“背還很痛。無法舒服。甚至不能轉側。左又痛、右又痛。”李先生說這話時,非常惆悵。
“真要命。醫生怎樣說?”
“我…不看…醫生了,”他逐個字慢吞吞的說。
“為什麼呀?”
“又何必呢!錢都用光了。醫生根本不會爲我做任何事情。”
“如何説起?”
“自從醫生切掉我的結腸癌,我們已沒有剩下多少錢了。爲了手術,我們賣掉我們所有一切。賣掉黃牛,才凑得二萬元左右,但所有的錢都全是用來支付醫藥費。更糟糕的是,命運似乎總是捉弄我們,我的背又變得痛不開交。哎!” 他嘆著說。
“聽起來你很沮喪,李先生。你的背痛又是怎樣一回事? ” 我好奇問。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幾個星期前,我開始劇烈咳嗽。當我用力咳嗽之時,背突然劇痛。從此這痛就饒不了我。每一動就痛…… ” 李先生試圖繼續與我們談話,但被劇烈的咳嗽打斷了。臉上通紅。痛苦扭曲了他的臉。
“慢慢來,李先生,” 我說。
“沒關係。我想告訴你我的故事。”李先生停下来,呷了一口水後繼續說。“我妻子用騾車送我到鎮裏的醫院急診室。車程很長。每遇上路上顛簸,我的背痛就差不多要了我的命。”
“那一定是很難受啊!”
“是真的!我們在急診室等了很久。最後醫生來了,給我檢查。他沒有說什麽,衹是開單給我做CT (X 光造影) 掃描。當我告訴他,我實在付不起這費用之時,他雙手朝天,只想送我離院回家。”
“真氣人!”
“我……我…… ” 李先生很想說話,但是他的情绪極爲激動,説不出話來。
李太代她的丈夫接著說,“即使我向主診醫生下跪求情,他也不允許我丈夫入院。你知道這醫生怎樣說?他滿不在乎的回答:‘對不起,太太。沒有錢,就沒有同情可言。’這是什麼樣的醫生啊!”
此時,李先生才可以恢復說話。“我真不怪醫生。他只是跟著醫院的規條來做。當我需要手術時,要入院就要我放下一萬元定金。恐怕這就是現實吧!”
“那你現在可以做什麼呢?”我問。
“不多。我既然不能買得起醫生所開的止痛藥,唯有用中藥來止痛。也許上天會善待我。”
“你什麼意思?” 我問。
“我意思是,解除我的痛苦…” 他開始啜泣。我拿紙巾給他。
“李先生,我理解。你的故事深深的感動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問你一個很直接的問題。這問題聽起來可能有些輕率。請問你在這一切痛苦的煎熬下,為什麼不考慮了結此生呢?”
“謝謝你理解我的感受。我不介意你率直的問題。在最黑暗的日子裏,我也曾多次問自己同樣的問題。儘管痛苦無情的折磨我、再加上我的病情回轉不了,我還是為著我的孩子活著。我不希望看到他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冷酷無情的世界裏而沒有父親。我希望我能藉著面對問題、而不是逃避,給孩子一個好榜樣。如果我停止與病魔爭戰而自殺,孩子看我是什麼的一個榜樣?”
當我離開這對夫婦時,我的心很沉重。他們的創傷、憤怒,失望、沮喪和無奈都深深刻在我心坎裏。我真感到無能爲力,但他們對配偶的愛和支持、對孩子的承諾、和對未來所存有的盼望,實實在在的幫助他們超越了苦難。九個月後我再回到中國,才知到“上天已善待”李先生了。
這個故事説明了我們在第一章所述及的大部份問題。說明了窮人和弱勢群體在今日的中國是怎樣帶著絕症來過活。李先生是農民,有報名參加農村合作社新設的衛生保健制度。這體系與城市的基本醫保不同。由於其微薄的資助,這合作社所贊助的只覆蓋住院費用(農民需自掏腰包來付頗昂貴的醫療費用)。一旦入院,更需付上爲數不少的按金,這使到許多農民都不能獲得他們需要的衛生保健服務。在我短短的關懷輔導服務中,這種令人心傷的故事在中國比比皆是。現在我們不妨研討一下中國人對苦難、對人生意義、和對“安樂死” 是怎樣的看法。
中國人對苦難的看法
中國人常常都是倚賴他們傳統信念的教化和智慧來超越苦難。這些信念包括佛教、儒教和道教。儘管儒家一般來説對中國人的思維影響最大,但佛教卻對苦難探討至多。佛祖教導生命有四個崇高的真理:[2](1)生、老、病、死、和失去都是人免不了的自然現象;若我們對這些太執著,就會有痛苦; (2)這痛苦是來自我們的慾望(例如追求快感或關注存活等等); (3)如要逃脫這痛苦,就要放棄我們的慾望; (四)而結束痛苦的方法,就是要我們放下身體、情感、思想和意識上的執著,[3] 通過“八正道”而達成。正是因爲意識上執著,所以要用四道(即正念mindfulness、正見view、正定concentration和正志intention)來消除其阻礙;並且用其他四道(即正語speech、正業action、正精進effort和正命living)來擴大意識的清晰度和範圍。美國和尚傑弗裡·德格拉夫Geoffrey DeGraff(又名阿傑夫)指出,這些步驟會令我們想起基督教的“求寧靜之禱文Serenity Prayer”(傳統作者是理查德·尼布爾Richard Niebuhr):要心靈安詳,就要用首四正來接受不能改之事,而後四正則是以行動來改變可以改之事。[4]
相反地,儒家(孔子)認為苦難是來自天(“上天”)。他認為上天是掌權整個宇宙、也是對與錯的最終裁判。皇帝被視為天子,是上天授權他來統治國家。如果皇帝無道,天將降苦難於百姓。如果皇帝忽視了引水道來灌溉禾田、忽視了開運河來用船載米來救濟國内的飢荒、忽視了疏通渠道來防止洪水汎濫、忽視了保持道路安全,那麽國民就要遭殃了。那時國民可以否定上天給予皇帝的任命,或者可以作反。若革命成功,一個新皇帝會被上天任命為天子,一個新皇朝會因此而成立。這是中國一貫的作風;多年來都是一朝跟著一朝。不過,儘管人民相信苦難是來自上天,他們仍可以力圖改革:改變政府或努力克服逆境(例如增加生產、或設立合作社來互相幫助)。這上天與勞動人民之間的的互動信念,可以在我先前説及的李先生身上展示出來。作為一個農民,李先生深信上天會祝福他、賜給他勞力所帶來的果子,並且會減輕他那難以忍受的苦難和痛苦。
道教也像佛教一樣,認爲苦難在人生中是不可避免的;這包括生、老、病、死和失去。萬事都會有因果:以前種下的因,會帶來今日的果。這些都是很自然的因素(或稱道)。既然如此,人就要平靜地接受人生一切不如意的事。道家認爲痛苦的兩個主要原因是依戀和自我。每當我們企望抓住一些事物、或抓住人或關係之時,我們便會難免有失落感,因爲這些都只是暫時性的,遲早會從我們的手指滑落。此外,大多數痛苦的來由是因為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真正的自我。痛苦都是我們自己憑空構成的。 原因是,我們無法擺脫我們自私自利的思想(如徒勞的思維)、擺脫我們的情緒(如恐懼、仇恨)、擺脫我們的看法(如虛假的盼望)和擺脫我們的慾望(如貪婪)。甚至有時痛苦也可以是從憐憫所引起,正如道家所認為,“衹要世上仍有苦難,那些滿有同情心的人又怎能完全快樂?”因此道家的理想是主張生活反璞歸真(即道),這才是應對苦難和滄桑最好的方法。
儘管道教的道德經沒有“苦難”這兩個字,但這經典文本很廣泛的談到如何解脫苦難這個問題。 道教的做法是採用輕鬆愉快的方式和精闢的比喻來解脫苦難,就好像是暗示著太過認真的談論苦難反而會令讀者深陷苦難中。如果苦難真是來自依戀和自我,那麼解脫苦難應從自我開始—就是與自我疏離和接受自然(常道)。[5] 道德經告訴我們: “常(道)無慾以觀其妙,常(道)有慾以觀其徼(表現)。”這就是說(根據林安梧教授的翻譯):從慾望中解脫出來,人會發現常道的奧妙;但如執著慾望,人衹會看到常道的表現(即苦難)。[6]
此外,“致虛極,守靜篤…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 就是勸人要“極力的回到虛靈的本心,要篤實的守著寧靜的元神…一切存在如此錯雜紛紜的生長著,它們總是個自回復到自家的生命本源,歸根就是寧靜,這生命的回歸就是常道。沒體會得常道,胡作非為,那就會產生了禍害。體會得常道,就會生出包容,體會得包容就會變得廓然大公。”[7] (根據林安梧教授的翻譯)
再者,人要接受:“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8] 也就是說:“凡在生命裏接受自然大道的人,自然大道也樂與相伴”(根據林安梧教授的翻譯)。
加拿大溫哥華知名哲學家和基督教文學研究者梁燕城博士曾深入探討過佛教、儒教和道教的教義。他不認爲苦難是一個有前因而出現的惡果,[9] 也不是飄浮在我們生命裏的實體。他跟道家思想一樣,認為這苦痛是因失去而感受到的一種感知。這失去可以包括失去舒適(孩子出娘胎之時)、青春(老化之時)、健康(疾病之時)、生命(死亡之時)或對我們有價值的一切(悲傷之時)。苦難的來源,可能是天災或人禍;後者可殃及我們或他人。
作為一個基督徒,梁燕城博士提議苦難是可以有積極的意義。耶穌受難和死是為救贖全人類。耶穌沒有心懷任何苦澀、怨恨、憤怒或報復;相反地,耶穌的心是充滿著悲傷、憐憫、無盡的愛和寬恕所有拒絕他的人。他的心只關注到最美善的全人救贖。他的死換來我們生命。他的受難讓我們意識到他能夠同樣地分享我們的痛苦,並且他是以身作則來教導我們怎樣分享他人的痛苦。使徒保羅也提醒我們如何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就好像神在我們患難中如何安慰我們一樣。[10]
梁燕城博士還提議一些步驟來幫助我們克服苦難。這些步驟其實是基於中國文化信仰與基督教的組合而成。[11] 首先,我們應盡量避免追問我們為什麼會受苦,而致力改變我們對苦難的態度,積極的面對苦難,並且確認苦難好像所有事情一樣,都是暫時的,必將成為過去。他認爲採取行動來避免苦難不一定行得通。更好的方法是接受苦難、視苦難爲生活的一部份,就好像呼吸一樣的自然進出。接受本身就是以“無爲”成“有為”(道家觀念)。每一個人都會有苦難,所以不要太過放在心裡,而應學會接受它,不要讓它令我們沮喪。相反地,若哀働我們已失去了的東西,不如簡單地感謝我們還擁有的東西。這樣我們將會心存知足。最後,梁燕城博士還建議我們學習仁愛和寬恕,使我們在苦難中好過一點。
中國的文化信仰
中華人民的苦難歷來都比比皆是:地震、水災、乾旱和風災經常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戰爭和飢荒更不用説了。因此,中國人普遍來説都大多認爲生命是負面的、是超乎人的控制、並且在應對苦難時,往往都是倚賴中國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因爲這些觀點和美德都曾經幫助他們克服過極端的逆境來活下去。現在就讓我們瞭解一下中國主導的文化信仰吧![12]
世事難以控制
中國人相信世上一切都是由上天掌權、不是他們容易控制到的。他們相信人是不能防止或控制强大的自然力量或影響著他們生活的政治力量。歷來中國人都很少能通過投票來選擇他們的政府。每個皇朝的統治都是天帝授權,而在更替政府的過程中,人民生命的犧牲可説是數以萬計。農民的生活更是受著天災、劫匪和腐敗官員的擺佈。一次又一次的戰爭把國家撕裂,難怪中國人大多認為需要接受殘酷的現實和改造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才不至於變得瘋狂、生活變得充滿怨憤。因此,儒、釋、道的思想也很自然的流行在中國。
世事變幻無常
對中國人來說,世事不僅是控制不了,也不能預測。普通人既不能控制世事,也無法預測到世事將會如何變化。誰會想到在一夜之間,皇朝可以變更、工人可以掌權、大學教授與學者會被下放作農民、作孩子的會清算父母、作父母的會清算自己的孩子?這些都是嚴酷的現實。世事和天氣一樣,都是難以預料的。
孔子(儒家)試圖在制度混亂的春秋時代引進規律,但道家卻強調生活要如水的靈活。其實,以道家的教導,人之所謂美德(例如孝慈和愛國)只不過是人努力應對已破碎的家和國而已。道德經18章有云: “大道廢,有仁義; 智慧出,有大偽; [13] 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14]”(翻譯:“當社會紛亂、人慾横流之時,才會提倡仁義作為補救;當天下失去了質樸之時,才會有靈巧;當家庭已沒有坦誠、和睦之時,才會產生孝慈;當國家陷入昏亂之時,才會誕生愛國的精神”) 相對而論,佛家强調世俗無常;這包括了生活上一切苦難全都是錯覺,因爲它們都是暫時的、都會過去。這些教導使中國人能以平和的心態來面對眼前生活的滄桑。
宿命論
基於先前這兩種信念(即世事難以控制和變幻無常),中國人普遍會接受命運,認爲命運是宇宙所操縱。[15] 一個母親曾對我說,“我兒子出生時已患上先天性心臟病。命運真的帶給我一個爛攤子。”她已經放棄了弄清原由。宿命論令人認識到理性的局限,打開了一個神秘、超現實的大門。許多人都認爲,只有聖人才能洞察這超現實的奧妙。要知算命在中國很流行,是通過相掌和占卜來滿足迷信之人想預知未來的慾念。此外,風水在現今的中國也很流行。這些都只是試圖保持一己對世事的控制慾。宿命論是可以幫助人更容易容忍一些無法解釋的逆境。當這個患有心臟病的兒子出生時,他的母親將自己所遭遇的不幸和苦難都歸咎於命運。是命運令她無法控制一切事的發生。這樣,她就可以放下心頭的恥辱和內疚。
自然界的二元性(陰與陽)
道教強調陰陽兩極。這二元性的信念認識到對立可以共存、思想不和也可互相遷就。這陰陽符號是表達出人性和人生的兩極平衡。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醫學上的治療與預防其實,在一般來説,是沒有明確的區別,因為兩者之目的都是一樣,旨在恢復生物系統的平衡。同樣地,中國人一般都不會斷言正面的人生觀可以擺脫苦難,或斷言美德可以防止邪惡的發生。中國人從過去的歷史中學到,無論我們如何努力避免或防止,邪惡和苦難都會臨到我們頭上。關鍵是接受與否那不可避免的事,和能否整合對立的兩極:比如苦難的正面和負面,以及好與壞這兩方面。若人能整合光明和黑暗這兩極,説不定會帶來成長。加拿大心理學家王載寳博士Dr. Paul T. P. Wong認為這二元對立的做法是卓越的,因為“每個人的最强項是局限於個人的最弱點。人若漠視自己的要害,可能會最終付出高昂的代價。”[16]
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不論是用在道德、政治或社會觀點上,都是描述人類相互依賴的一個術語。集體主義所强調的並不是獨立個體。這是很重要的區別。集體主義是關注著社區和社會、捨棄個人目標、力求將團體目標放在首位。[17] 孔子的教學重點是強調國家和社會的集體主義。因此,集體主義在東亞文化中非常普及。[18] 在這些文化中,良好的工作關係至為重要,而對家庭、朋友和國家忠心也是同樣重要。集體主義有助於增强社會資本:團結就是力量,可以增加打敗共同敵人的可能性。當家庭中的一份子患上絕症,其他成員或相關社區人士(例如鄰居或教友)都可以幫助病患者與病魔爭戰。
有毅力就有成果
這信念提醒我們,如可能的話,應盡己所能來塑造未來。這包括尊崇職業道德(勤力工作和工作認真)、努力修身(自我培養各種美德)和改善關係(對親人孝慈、對朋友忠誠、對掌權者尊敬、和對家庭與團體和睦)。“愚公移山”的故事教導我們,不斷努力所結的善果可以延伸到萬代和造福人群。這個典故説及一個老頭子用一把鏟子在山邊挖了又挖。旁人覺得奇怪問他。他回答說:“我正在努力去鏟除這座山,免得我們要爬過它才能到對面的村莊。” “但老伯,這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啊! ”老頭子擦去前額的汗水,回答說:“你説得對。我是老了,但我的孩子和孫兒們會繼續做下去,直到完成這份工作爲止。説不定其他村民也會加入啊!”
應對生活滄桑所帶來的强項和美德 [19]
以上説及的各種文化信念在發展中國人所重視的一些强項和美德實在有很重要的影響:
世事難以控制的信念帶給國人接受、忍耐和自我改造等强項,因爲如果改變不來世事,我們至少可以改變自己,比如自己的慾望、看法和態度。接受不僅是意味著認知和同意,還涉及謙卑順從和接受命運。忍耐也不止意味著堅持目標,還涉及明智的撤退和隨後的反撲(正如毛澤東進行游擊戰一樣)。成語有云:“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這就是說,只要還是活著,就有盼望和將來。同樣地,自我改造不止意味著超越重構認知,還涉及心靈的更新和啟發。
世事變幻無常的信念可以引來盼望、靈活和智慧等强項。盼望出自逆境中面臨絕望。有誰會預料到上述的李先生,會因爲强烈咳嗽而引致背部劇痛?有誰會預料到這家庭會因李先生的病而傾家蕩產?又有誰會想像到身爲濟世爲懷的醫生會說這樣沒有職業道德的話?當情況改變不了時,李先生將意志轉移到尋找意義。結果他找到了。意義能給他盼望。
宿命論的信念可以促進接受、提升信心和超越困境等强項。它認識到理性是有局限的。李先生談到掌控人生的上天。他懇求上天憐憫他。這表明他對一個至高無上保惠師的信心。這信念在中國已經持續多時,甚至許多人也試圖尋找上天的旨意,或尋覓風水師的建議。他們大多相信貧富由天。
陰陽二元性的信念可以釋放思想的局限、帶來包容和應對環境的轉變等强項。這信念有利於走中庸之路 — 便利整合和整體的思維,而不是擇一或二,也不是衹靠單方面的直綫思維。李先生就是這樣才能理解駐院醫生爲難之處。即使這醫生滿有同情心,他的手也是受著醫院規條的捆綁。李先生似乎已接受了這事實。唯有接受人生的全面,不論是正或負,人才能忍受得住生命之苦。要滿足、要幸福,這平衡就是關鍵。中國人常說柔中帶剛,而美德(例如仁義、孝慈等)也可能隱藏著毀滅自己的種子(例如不義或不孝)。因此普遍來説,不宜低估溫柔順服或自誇德行優勢。當李太跪地懇求醫生同情和憐憫她丈夫之時,這溫柔順服也同樣帶著堅韌剛强在裏面,因爲如果這樣做可以讓她所愛的丈夫舒適一點,她是絕不會猶豫跪下來求的。
集體主義的信念可導致合作、為他人設想、和提升社會資本等强項,也導致更穩定的家庭和組織。當問題對個別來説是太大、解決不來,團結就有力量。李先生得到妻子及其子女的支持,這有助他應對他的苦難。
有毅力就有成果的信念可導致工作認真、勤奮,和負責等強項。如果宿命論鼓勵對上天保惠的依賴,那麼這信念可以促進個人努力。就讓我轉述有關這可能性的一個故事吧!
2007年12月我在廣東新會經過一位朋友介紹遇上了曾女士。[20] 那時我聽説曾女士正在接受淋巴瘤的治療。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上,我和我的朋友抵達曾女士精心打掃過的工作點,一個位於死胡同的髮廊。那天是星期六,大約是上午十一時左右。,通常這時間是比較忙碌,應該有不少客人來恤髪,準備參與週末的活動。不過在那天,除了曾女士自己在看電視外,並沒有別人在。我們都很驚奇。曾女士的頭髮看來很疏落、臉頰下沉、膚色很黑、額頭打了皺纹。她看起來比我預期的33歲年齡還要多。
“你好嗎?”進去時,我問候她。
“我覺得不太好。這化療真讓我失望。我不能吃、不能睡、非常累。這影響了我的工作和我的家人。你看看,即使我的常客也避而不來,就好像避瘟疫一樣。”
“我真替你難過。”
“首先醫生說我需要手術。手術後,正當我想往前走時,癌症已蔓延的壊消息卻令我倒退幾步。這化療需要不少錢,而我們又沒有這麽多錢。”
“聽起來你是很失望和擔心。這些治療一定令你苦不堪言。”
“是啊。有時我真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什麼,令我的時運轉得這麽壊。”
“嗯。真很難弄清楚。”
“你知道嗎?我可能要賣這個髮廊啦! 我不捨得呀!我一直都很努力來經營它啊!”
“有沒有其它方法?”
“我丈夫提議招請其他理髮師用我們的髮廊,賺一些錢來支付髮廊的開支。你看如何?”
“聽來可行。有志者事竟成。你丈夫好嗎?”
“他一直都非常支持我,但我有一天無端端對他生氣。我已對他道歉了。”
“真好。有孩子嗎?”
“有。我有三個女兒。他們都盡可能幫助我清理髮廊。我覺得很有福氣。”
“我高興聽到你家人非常支持你。你的生活環境轉變很多,不知你現在對你的生活感覺如何?”
“坦白來說,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樣走進這困境。我嘗試做一個好妻子和好媽媽,又非常努力省錢來開展這業務。我不吸煙。我不明白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癌症。生活是多麽困苦,不是嗎?但我是不會屈服的。我一直是個好鬥之人。我還年輕。我相信我還有許多活要幹。你說是嗎?”
“聽到你這樣說真好。你喜歡幹什麼活呀?”
“我最喜歡自由、自由來選擇我想要的。高質量的生活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我並不是說我喜歡亂花錢。我是説評估下我生命中還有無可貴之處,才再決定是生或死。”
“你是什麼意思?”
“我指的是預設醫療指示和憑醫師的協助來達成安樂死的事情。當我的生活質素惡化到我無法忍受之時,我希望我還能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指示我個人的醫療方向,而不是加重別人的負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未到那時,我還希望能活得豐盛。我認爲生命是可以充滿奇蹟和值得敬畏。我希望能和丈夫、孩子們同渡剩下來的光陰、有更多甜蜜的擁抱。只要我還可以,我希望繼續作髮型師、做有創造性的工作。我更希望繼續園藝,觀賞那些播種後綻開的花朵,帶給我無限的驚嘆。俗語說貓有九命,但我只有一條,所以更應珍惜現在的生命。”
中國有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都與曾女士一樣有相同的看法。他們相信因果,認爲一切行為都會影響到過去、現在和將來。換句話說,他們認爲苦難和不幸都可能是過去做錯事的結果。但不論曾女士所遭遇的苦難是來自何因,她都沒有計較著。相反地,她選擇改變自己的將來。即使死神敲著門,她也渴望對自己的生命能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儘管她的人生歷程充滿崎嶇,她也接受下來,繼續追求自己的人生意義和目的、盼望活得豐豐盛盛。這是可以理解的。儘管她和她丈夫要面對很多障礙,但他們對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大大的幫助他們應對她的病情發展及其後果。他們學會了接受好與壞、開放思想和明智行事。這些强項幫助他們同步應對逆境,從而找到有創造性的解決方法(比如邀請其他髮型師來分租髮廊)。
中國崇尚的人生觀與生命意義
以下圖片展示了三位中國先哲如何從不同的角度看生命:

這畫“品嚐醋”是用寓言形像來代表佛家、儒家、和道家(道教)三家對生命哲學的看法。[21] 這畫描繪三名男子把手指放進醋缸裏來品嚐醋,但表情各異:一個男子的面上表情滿是苦澀;另一個男子的反應是酸溜溜的;而第三個男子的臉容卻是甜甜蜜的。這三個人代表著佛陀、孔子和老子,亦代表著中國的三大哲學傳統:佛家、儒家和道家思想。每個人的面上表情正好代表著不同傳統對生命的不同主導態度。佛家認為生命是苦澀的,是由痛苦和苦難來主宰。儒家認為生命是酸的,原因是現在的社會陷入混亂狀態,與過去的秩序脫節。道家卻認為生命是甘甜的、在自然的情況下基本是美好的。
有人將這畫的主題描述為“生命趣劇”,又有些人以調解方式來解釋這畫,因爲既然這三名男子都同聚在醋缸前,所以這三種教導實際上可以說是同出一系。鑒于這三種傳統在中國悠久歷史中已經有相互影響,所以這説法可能有些道理。比如,道家的教義曾流入古典儒學,引起新儒家思想。在今日中國,同時認可這三個傳統信仰的,也大不乏人。
佛教徒普遍認為生命的苦難是我們抓緊慾望所構成的, 因此生命的意義是(1)放下一己私慾和放下身、心、社、靈的渴望來脫離苦難;(2)從而達到永恆極樂世界(捏槃)或靈命蘇醒,從擔憂、捏造和煩惱中釋放出來,並結束生、老、病、死的反複循環。[22]
儒家則強調生活正常便是生命的意義。平常人可以在人生經驗中找到“生存的終極意義”。[23] 儒家確認紀律和教育為準則或美德,通過理性與人際關係來維繫秩序與和諧,人才能實現美好的生活。
另一方面,道家相信“人生的苦澀和酸楚都是來自内心的干擾和沒有感激的心懷。衹要理解生命本身、順道而行,人生基本上是甜蜜的、是美好的。” [24] 既然一切都來自道(自然),人必須修煉和用自我實現的方式來歸回自然或與道聯結。道教徒的人生意義就是盼望在短暫的人生中能最終與道合一,修練成仙而達至長生不老。“只有自我反省才能找到我們最內在的生存理由。簡單來説,答案就在我們心裡。”[25]
要知道人生意義與生存原因是不一樣的。生存原因通常是指個人的生命意義,是指那具有終極存在意義的個人生命意義。根據個人的價值觀,人生確實有許多重要的意義,但其中“持有最高價值、比其他重要人生意義更突出的,”可能就是這個人的生存原因。李先生希望為孩子而活。[26] 孩子便是他生存的原因。對曾女士來説,[27] 生活的質素是她生存的最大理由。[28] 在我實地觀察當中,晚期病人常常想知道,當他們發現自己吃重的人生價值和生活質素大大降低之時,他們是否有任何理由繼續活下去。事實上,“為什麽要活?”這個問題,常被那些繼續要剋服百般困難或面臨痛苦和苦難的人多次提問到的。這些人經常想知道,他們的生命是否有意義、值得他們繼續生活下去。這意義涉及人類生存的意義、甚至目的。[29] 它與人的積極價值觀有很大的聯繫,因為人生的目的一般都是增加內在價值。
似乎人類是需要意義。意義是我們人性的一部份。我們的知覺是憑著整合感覺刺激物為模式而組成的。比如,當我們看到一個不完全的圓圈時,我們會自動將其視為完整,將外部刺激物自動組成圖形與背景。有些人會看重圖形,而別些人則會看重背景。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文化信念、價值觀與行爲會各有差異。同樣地,當人要面對生存現實(比如無意義感或死亡)之時,人往往會尋找一種模式來解釋為什麼、或(簡單地說)尋找生命意義、生存原因。總體而言,當生存現實與我們的感知模式不相配時,我們會感到不安,直至我們能將這扭曲模式變爲可識別的圖形與背景。許多人,尤其是年青一輩,會很難接受末期病症,或接受不可理解的情況。我曾遇到一個女孩子毫不明白為什麼她的母親,雖然沒有吸煙習慣或家族歷史,還是患上末期肺癌。[30]
我們需要意義的另一個原因,不止是憑著它來告訴我們為什麽而生活,還告訴我們應該如何生活。這涉及我們生活的目的。一般來説,生活的目的是一個預期目標來引導人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生活的目的與盼望實在是息息相關,因爲真實的盼望是人生中期待成功地達成可以實現(而不是虛幻)的完美。盼望提供生命意義來維繫我們。它令我們明白為什麽儘管苦澀的生活是如何折磨我們,生命仍然是有意義的,因爲有盼望就可以指引我們如何生活。本人認爲每個活著的人都有一個生活目的,儘管這個人可能沒有察覺到。
中國人對 “安樂死” 的看法
什麼是“安樂死”?中文和日文都有這個措辭。簡單來說,是“平安、無痛苦的死亡”。現代化來説,安樂死可分爲被動和主動。被動的安樂死是在病重時撤消生命支持。主動的安樂死是憑醫師的協助來自殺,簡稱P.A.S.,即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在中國,人稱“仁慈地終止末期病者的生命”)。每個中國人都熱切的盼望在死亡時能夠有平安。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安樂死”又是什麼?儒家普遍認為死得有意義是一種美德、比生命本身更為重要。人應該“願意因維護美德而死。”[31] 如前所述,佛教徒認為死亡是通過輪回轉世來達成般若 prajna(即最高智慧) 的途徑。道教徒則認為“安樂死”是自然死亡。老子的道德經50章開始曰:“出生入死”(意思是既有生,必有死;生是自然的化育,不必喜;死是向自然的回歸,亦不必悲)。生死相互融合,與道合一:“死亡,像生命一樣,是錯覺;沒有始,也沒有終,唯有道在無止境的流動。與道合一之人大可無畏。”[32] 道德經亦教導我們,“如果你意識到一切都會變,你就不會執著。如果你死也不怕,就什麼都可以達成。”[33]
至於西方支持醫師協助病人自殺P.A.S.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的道德觀也與儒家的倫理思想達成共鳴。首先,儒家以仁為基本美德的思想可以強有力的支持PAS。[34] 仁是仁慈,是對父母或同胞的一種同情和尊重。看到別人痛苦,自己也會有同感心來分擔這痛苦。中國傳統上都一直視這同感心為醫德,是醫師應有的仁心仁術。這仁心令不少醫師願意協助末期病者終止他們的生命。
其次,一貫的儒家道德思想都認爲生活質素比生命本身有更高價值。當末期病者的生活質素已無可再低時,儒家倫理認爲與其生不如死,倒不如讓他們從這“地獄般的生活”解脫出來。儒家並不認同“神聖的生命”。為了顧及人的生活質素,儒家認為PAS是合理的。[35]
再三,是關乎尊嚴的問題。當一些末期病者在失去控制身體功能之時,他們覺得是奇恥大辱和盡失尊嚴。對他們來說,這侵犯可能比身體的痛苦更難承受。儒家思想歷來都認為寧自殺也不屈服來維護尊嚴,避免在外來勢力(如昏君、惡勢力或政治壓迫)威逼下受到羞辱、丟臉、或侮辱。 在這些情況下,儒家認爲自殺(最後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沒有家人或朋友的愛和支持。在現代PAS個案中,香港浸會大學的羅秉祥博士曾指出,這些所謂侵犯人尊嚴的襲擊往往來自個人本身(例如疾病、老化、以及身體和精神的惡化),故此都涉及人類不可避免的普遍現象。除非人類的病患、老化、和死亡真的被視為人類公敵,否則實在很難苟同儒家倫理説及的尊嚴侵犯。[36]
第四,關乎自主的問題。儒家倫理思想並沒有廣泛重視個人的自主權,[37] 也沒有討論太多人權。個人自由是在家庭和社區情況下確定其限度。
總括來說,儒家在支持PAS 與否的問題上,認同了仁慈的心和生活質素為支持PAS的道德觀念,但並不認同身體尊嚴問題和個人的自主權為支持PAS的原因。畢竟儒家認爲身體髮膚受於父母,我們有責任來照顧自己身體,不應自殘其身。“論語”中描繪一名孔子的學生曾子,因重病垂危,[38] 讓他的學生看他的手腳,並引用詩經說:“爲著履行我對父母的責任,我一直都在照顧這身體,唯有現在(垂危之時),我才能確保免除這責任。”[39] 這個想法出自對父母感恩之心,也是一直在中國文化中流行的一個中心思想。[40] 在跨文化的比較中,羅秉祥博士指出,雖然西方文化高度重視自主權,但孔子思想並不重視這點, [41] 怪不得儒家傳統只能對PAS作有限的認可。道德觀念有所差異,是因為不同文化將重點放在不同的價值觀上。湯馬士·卡蘇利斯Thomas Kasulis提供一種視覺隱喻來解釋這現像:一種文化所認可的前景卻可能是另一種文化所認可的背景。[42]
同樣地,佛教徒對PAS也沒有劃一的看法。佛陀的教義並沒有明確地教導如何處理PAS。巴利大藏經中最顯然的自殺 例子包括僧侶闡陀 (Channa)、瞿低迦(Godhika) 和跋迦梨 (Vakkali)。[43]這三個僧侶都有重病帶給他們極度的痛苦,最終都是取去自己的生命。雖然他們在死時可能得道開悟,[44] 但終究他們在自殺之時並沒有達成覺悟的標準,也就是說沒有平和心態、沒有解脫憤怒、仇恨或恐懼,所以難以得佛教徒公認爲已覺悟到人生真理的阿羅漢;[45] 結果他們仍然會受輪迴生死所控制。
佛教徒視死為過渡。死者將投胎重生,而新生命的品質將會視乎他們前生的善惡因果。這會產生兩個問題。一、我們並不知道新生命將會如何。如果新生命比目前的生命還差的話,末期病者的PAS便會適得其反。以爲了斷生命可以逃避苦難,但來生甚至會更糟。至於那些得道開悟的末期病者,並不需要擔心PAS會帶給他們更痛苦的新生命,因為他們既然已得道開悟,是不需要經歷到投胎重生了。二、自殺會干擾到因果關係。縮短了生命就會影響到人的緣份。佛教徒的假設是:當受苦的人考慮到自殺時,身體的苦楚會帶給他精神上的痛苦,心靈處於不平衡狀態,導致錯誤的判斷,也失了因果的平衡。[46]
況且,佛教徒認爲,不論是奪走自己或別人的生命,都是不合理的。要有優質的生活,佛學首要的戒律是不可殺生。這適用於各等級的人和動物。這教條所約束的,不止是佛教聖職人員,也包括信佛的普羅大衆。[47]
佛教傳統在日本不乏僧侶自殺的許多故事,而在越南戰爭期間,僧侶自殺也有被用作政治武器,但這些都是僧侶,與普通教徒有很大分別。在佛教,生命終結的方式對新生的開始會有深遠的影響。佛教視一個人在死亡時的心態為重要因素,應是平和的、解脫憤怒、仇恨或恐懼。
自殺也是日本武士傳統之一。他們剖腹自殺seppuku的儀式確實非常接近安樂死 – 牽涉到一個助手斬其首來加速死亡。這些武士的自殺動機類似尋求PAS的人:他們可能是打了敗仗,將被敵人處死(就好像末期病者無力反抗病魔、面臨死亡一樣),或者是嚴重受創、不能再有什麽作爲(就好像病重之人覺得自己豪不中用一樣)。正如前述,日本武士剖腹自殺時的心態,在佛教來説,也是非常重要。總而言之,這些案例表示佛教只支持已得道開悟的佛教徒自殺(包括PAS),但不贊同其他人了斷自己的性命。
道教的“安樂死” 是自然死亡。世上一切(包括人的生命)都來自道;人死時,便歸回道(生命的源頭)。明白與道合一這道理,便會欣賞到人生、欣賞到人生中無時無刻的奇蹟。就像晝夜一樣,陽和陰的雙重性是自然的兩極、又是同等、又是互補。生死也是一樣。有生命就有死亡 ;避不了。凡有生命的,都必然要死,又從死入生。自然界的四季,是在循環變化中達成和諧。既然死亡是自然的,就不應為它過份悲痛。
生存在道教來説也視乎三方面的相互影響:(1)個人; (2)社會(及其人為的價值觀);和(3)道(自然原則)。要過滿足的生活,人必須了解自身內在的渴望和需要、社會的價值觀和自然原則。生命和死亡的意義,不僅是取決於個人的渴望和需要,也取決於文化和社會的影響與自然原則。
道家的主調是無爲而治、不動便是動。這藝術意味著不採取行動,實際就是一種行動。這並不是“無所事事,只靜觀其變,” 而是描述一種通過適當的行動來完成事情的做法,是根據個人能力、願望、和道的認識,知道自己在大自然的位格,才知道何時應動、何時應不動。換句話說,唯有信靠自然的我才能生活滿足,而不是絞盡腦汁來與現實生活或無憑的困擾持續鬥爭下去。因此,道教並不輕易贊成干擾別人選擇的道路(包括PAS)。
基於憐憫(道教三個基本美德之一 [48]),道教是允許末期病者放棄積極的醫療措施來了卻殘生。然而,道家的倫理並不贊同任何方式的PAS。道教看殺人是一種積極行動,可以說是最壞的一種自然干擾、與道不合。相比之下,讓病人自然死亡才是帶有平安和尊嚴的“安樂死”。
在中國,多次的民意調查顯示出,當面臨難以忍受的痛楚和無休止的苦難之時,許多人都願意選擇PAS ,要求醫師仁慈的協助自殺。[49] 但是我們應該留意到採集的樣本數目比較小(最多是171個被訪者),而大多數被訪者是城市居民,有可能引進抽樣差誤。畢竟,近百份之六十的中國人民是在農村生活的。
至於子女是否願意接受父母選擇PAS,調查結果並不明顯。這並不奇怪,因為孝道在中國傳統社會裏是非常重要,孩子們從小已知道應該盡力來照顧患病的父母。如果父母患有末期病症,孩子們可能會覺得遵從他(們)PAS 的意願是相等於離棄他(們)。當他們看到父母受苦時,他們的無奈和破碎的心,我都有好幾次感受得到。他們更難受的是當父母表示希望死亡可以減輕兒女的經濟負擔,這實在令孩子們充滿內疚。
儘管有許多案例要求醫師仁慈的協助自殺,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還沒有立法批准任何機構或人士從事此措施。[50] 醫院迄今仍拒絕同樣的要求(主動的安樂死,即殺死病人),但在病人或其家屬的要求下,醫院允許被動的安樂死(即撤回生命支援系統)。實際上PAS已暗暗的通行一時。有醫師會將大量的止痛藥或麻醉劑注入末期病者體内,主要目的是止痛,但實實在在的是在幫助病人脫離苦海 (正所謂“雙重效應”)。[51]
到目前為止,我在本章試圖给讀者簡短的一瞥,了解一下末期病者在中國是怎樣生活,而中國人又是用何等心態來應對難以忍受的痛苦。同時,我們亦探討過生命意義和中國人不同的自殺觀。在接下來的幾章裏,我將嘗試將西方思想對生命意義和盼望的哲學觀點採納入我們的討論,因為筆者認爲它們與關懷和輔導末期病者有很大的關係。
End Notes for Chapter 2 第二章尾注
[1] Interview #6, Appendix.
[2] Donald S. Lopez, Jr., “Four Noble Truth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214989/Four-Noble-Truths (accessed May 20, 2008).
[3] The teachings on the five khandhas: form (body), feelings, perceptions, thoughts, and consciousness, give us the tools to relieve suffering.
[4] Geoffrey DeGraff (a.k.a. Thanissaro Bhikkhu), “Life Isn’t Just Suffering,” rev. 2005, http://www. thaiexotictreasures.com/suffering.html (accessed May 20, 2008).
[5] Jos Slabbert, “How to Deal with Suffering,” http://www.taoism.net/theway/suffer.htm (accessed May 26, 2008).
[6] Jos Slabbert, on Lao-tzu, Tao Te Ching, Chapter 1, “attachment brings sorrow, but joy too,” http://www.taoism.net/theway/suffer.htm (accessed May 20, 2008).
[7] Jos Slabbert, on Lao-tzu, Tao Te Ching, Chapter 16 “the source is our true self,” http://www taoism. net/theway/suffer.htm (accessed May 20, 2008).
[8] Jos Slabbert, on Lao-tzu, Tao Te Ching, Chapter 23 “a willingness and courage to face reality is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suffering, especially when the suffering is inevitable. It is when you “embody” the Tao, accepting the inevitable, that you can face suffering with true equanimity,” http://www.taoism.net/ theway/suffer.htm (accessed May 28, 2008).
[9]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omas In-sing Leung, Ph.D. (University of Hawai’i), Director of the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in Vancouver, B.C. He was on the faculty of Regent Colleg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and has served in several Chinese universities (Sichuan and Shandong) a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dvisor.
[10] 2 Cor. 1:3-4 KJV, “Blessed be God, even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the Father of mercies, and the God of all comfort, who comforteth us in all our tribulation, that we may be able to comfort them which are in any trouble, by the comfort wherewith we ourselves are comforted of God.”
[11] Thomas In-sing Leung, From Suffering to Hope [in Chinese], CD-ROM (Vancouver, BC: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Productions Association, 2004).
[12] Paul T. P. Wong, “Chinese Positive Psychology,” Encyclopedia of Positive Psychology, ed. Shane J. Lopez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ub., 2009), 152.
[13] Jos Slabbert, “Body’s ‘intelligence’ refers to wisdom and compassion. It represents the intuitive, natural intelligence – the gut feeling of what is right – of someone living in harmony with the Tao,” http:// www.taoism.net/theway/suffer.htm (accessed May 28, 2008).
[14] Jos Slabbert, on Lao-tzu, Tao Te Ching, Chapter 18, http://www.taoism.net/theway/suffer.htm (accessed May 20, 2008).
[15] Kerry W. Bowman and Peter A. Singer, “Chinese Seniors’ Perspectives on End-of-Life Decision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3, no.4 (2001): 455-64.
[16] Paul T. P. Wong, “Chinese Positive Psychology,”152.
[17] Carl Ratner and Lu-mei Hui,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3, no. 1 (2003): 72.
[18] Harry C. Triandis,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94), 161.
[19] Paul T. P. Wong, “Chinese Positive Psychology,” 152.
[20] Interview #12, Appendix.
[21]The Vinegar Tasters was mentioned in Benjamin Hoff’s book The Tao of Pooh (New York: E. P. Dutton, 1982), 2-7,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negar_tasters.with picture (acessed May 14, 2008).
[22] Donald S. Lopez, Jr., “Four Noble Truth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214989/Four-Noble-Truths (accessed May 20, 2008).
[23] Wei-ming Tu,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23.
[24] Benjamin Hoff, The Tao of Pooh (New York: E. P. Dutton, 1982), 6.
[25] Ming-dao Deng, Scholar Warr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o in Everyday Life (San Francisco: HarperSanFrancisco, 1990), 253.
[26] See story in Interview #6, Appendix.
[27] See story in Interview #12, Appendix.
[28] “Quality of Life” means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as suggested by Matthew Edlund and Laurence Tancredi, “Quality of Life: An Ideological Critiqu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28, no. 4 (Summer 1985):591-607. This will be further discussed in Chapter 3 of this dissertation, page 91.
[29]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he Meaning of Life,”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life-meaning/#MeaMea (accessed May 14, 2008).
[30] Interview #10, Appendix.
[31] Mencius, “To die to achieve ren (compassion)” and “To lay down one’s life for a cause of 義 yi (righteousness)” in Mencius 6A: 10, trans. D.C. Lau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32] Jos Slabbert on Lao-zi, Tao Te Ching, Chapter 154, “acceptance of the inevitable makes suffering bearable,” http://www.taoism.net/theway/suffer.htm (accessed May 20, 2008).
[33] Jos Slabbert on Lao-zi, Tao Te Ching, Chapter 74, http://www.taoism.net/theway/suffer.htm (accessed May 24, 2008).
[34] Mencius, “I would rather take dutifulness than life” in Mencius VI A: 10, 166.
[35] Ping-cheung Lo, “Confucian Values of Life and Death and Euthanasia,” Annu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19 (1999): 318.
[36] Ibid.
[37] Kantian philosophy has long cherished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autonomy, which emphasizes the freedom to decide on things that matter much to one-self. Some of its followers believe that human beings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for themselves.
[38] Arthur Waley, trans.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New York: Everyman’s Library, 2001), 8.3.
[39] A paraphrase from the Classic of Poetry, one of the Five Classics (ancient Chinese books) used by Confucius and his followers as the basis of studies. Believed to be compiled or edited by Confucius himself. The others are Classic of Changes, Classic of Rites, Classic of History,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40] David Wong, “Comparative Philosophy – Chinese and Western,” rev. 2005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parphil-chiwes (accessed May 24, 2008).
[41] Lo, “Confucian Values,” 322.
[42] Thomas P. Kasulis, Intimacy or Integrity: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156.
[43] The Pali Canon is the primary sacred text in Buddhism, especially in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44] An arahant is a “worthy one” or “pure one,” an enlightened person who is not destined for further rebirth. It is a title reserved for Buddha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his noble disciples.
[45] Damien Keown, “Buddhism and Suicide: The Case of Channa,”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3 (1996): 8-31.
[46] “Euthanasia: The Buddhist View,” BBC Religion & Ethics Forum, Feb. 24, 2004, http://www.bbc. co.uk/religion/religions/buddhism/buddhistethics/euthanasiasuicide.shtml (accessed May 24, 2008).
[47] Bhikku Dhammavihari, “Euthanasia: A Study in Relation to Original Theravaden Thinking,” presented at the Y2000 Glob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Singapore, June 3-4, 2000, http://www.metta.lk/ english/euthanasia.htm (accessed May 24, 2008).
[48] Chad Hansen, “Tao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v. 2007. Simplicity (in Tao Te Ching, Chapter 37) and humility (Tao Te Ching, Chapter 7) are two other cardinal virtues in Taoism.
[49] According to Xinhua National News, these surveys have found a high percentage of people, from 95% (among medical workers) to 64.6% (among Beijing residents), in 2003 opting for “mercy killing” if they ever become terminally ill with intractable pain. Legal Daily, June 12, 2007 edition [in Chinese], http://www.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6/12/content_6230138.htm (accessed May 20, 2008).
[50] The March 6, 2006 edition of China Daily reported in an article “Local Experiments on Euthanasia Proposed” that a province-level hospital in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each year would encounter one or two cases in which patients with terminal illness would ask for “mercy killing,”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6-03/06/content_527285.htm (accessed May 20, 2008).
[51] William David Solomon, “Double Effect,” in The Encyclopedia of Ethics, 2nd ed., ed. Lawrence C. Becker and Charlotte B. Becker (Florence, KY: Routledge Press, 2001), 418. The principle of “double effect” is often invoked to explain the permissibility of an action that causes a serious harm, such as the death of a human being, as a side effect of promoting some good end, such as pain relief.
第三章
西方哲學思想如何看生命的意義
我的朋友亞鳳和我正氣喘喘的爬上樓梯,因爲這7層樓宇並沒有電梯。梯級處很暗淡,每一個角落都有垃圾。腐臭的氣味洋溢在空間。牆壁掛滿電錶,電線縱橫交錯、無處不在。幾乎每家每戶在他們的木門前都有一扇不銹鋼防盜門。我們爬梯越爬越高,樓下的汽車聲也漸漸變弱。最後我們到達張先生住在七樓的公寓來按門鈴。[1] 他的門口貼著一塊紅色招貼,寫上“上帝是愛”四個字,是用黑色墨水寫的。
應門的亞姨是一個大約四十多歲的壯健女子。經過介紹後,知道她是張太。來訪之前,亞鳳曾告訴我,這是張先生的第二個妻子。第一個妻子與他離婚時,留下三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給他養大。亞姨自己也有一個與前夫生的22歲兒子,現在和他父親同住。張太很熱烈的歡迎我們進入她的家。這家雖小,但很溫馨。報紙整齊的疊在桌上。餐桌旁邊的牆,掛上一個木十字架。桌上的花瓶裡有鮮花。在小小的電視機前坐著張先生。他看來很消瘦和憔悴。亂蓬蓬的頭髮已變為銀白色,頂頭也有些削薄。未來之前,我從亞鳳處已知道張先生患上末期肺癌,應命不久矣,但他還不知道他健康問題的嚴重性。
“亞鳳,歡迎你和我的朋友,” 張先生說。他試圖從沙發上站起來。
“謝謝你讓我們來探望您和亞姨。您好嗎?”我回答說。
“我這身體現在沒用了、一日比一日差。”
“不是嗎?我們年紀都不輕了。”
“你覺得梯級如何?你是不…… ”他問,但卻要停下來喘一口氣。
“對我來説,梯級真不容易。您呢?”
“我容易累、氣促。醫生說我的肺水腫,所以我很少出門。我想找一較低層的公寓住,但租金高得很。我希望有電梯,但除非建築物是超過七層高,否則電梯設備不是強制性的。”
“這豈不是要您終日呆在家裡?”
“亞姨會帶我出去走走。她背著我落樓。”
“真難為您啊!”我對亞姨說。她就坐在張先生旁邊的沙發上。
“她常用她的摩托車帶我外出郊遊。我喜歡坐她的車探訪新的地方,沿路欣賞美麗的風景。這樣我可以放鬆和自由自在。當我們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沿著鄉村小路漫游之時,微風愛撫著我的頭髮、掠過我的面孔,那種輕鬆感覺實在是難以形容,而腦海裡的憂慮和惱怒也一掃而空。這外出休閑游玩促進我的創造性思維,並給我們提供優質的時間在一起。我感到不論是身體或精神上還有自由、還可以到處游歷、可以順利的進行我一切终究實現的人生目標。”張先生說這話時,他的眼睛充滿著興奮和驚嘆、他的手輕搭著亞姨的肩膀。
“太好了!”我回答。
“在我最需要家人幫助之時,我的家人卻趕我出門,唯有亞姨願意收留我。我自己孩子拒絕幫助我。他們要我們答應許多不公平的要求才肯幫助。我做父親也真是太良善了、過份溺愛自己孩子,並沒有好好的教養他們。這是我將會帶入棺材的一項遺憾。”
“可以與他們和解嗎?”我問他。
“沒有多大用。與他們的媽媽一樣,他們真的很歧視亞姨。”
“亞姨,你覺得如何?”我轉向問亞姨。
“做爸爸的最好與他的孩子和好。其中有很多誤會,但我會盡我所能來平息它,” 亞姨說。
“亞姨,你的心真好。”
“亞姨是天賜給我的,”張先生插口說。“我愛她比我愛自己家庭更多。如果不是她,我已在絕望中自殺了。她是我還活著的原因。我希望我能為她做更多,但她卻是很容易滿足。她說她會樂於與我在一起同舟共濟。我喜歡與她在一起。當一切看起來是灰暗之時,她是我抱緊的唯一盼望。”
“那真棒!”
“我每天都感謝上帝的賜福。上帝是美好的。自從我退休之後,生活很艱難,尤其是沒有多少錢,但神每每都足夠提供給我們所需要的。我們學會了依靠祂的信實和恩典;對我來説,這些都足夠我們用了。我錯失了不少家庭溫馨與和諧,但我現在可以數算到與亞姨共同建立一個家的喜樂,和將來回歸天家的平安。”
幾個月後,在2008年3月, 張先生便與世長辭了。同年十月我回到中國,再探問亞姨。當時,她仍為死去的丈夫傷心,但卻有很多美好的回憶來珍惜。她期待有一天她會與丈夫在天家重聚。他們已找到他們的人生意義 (就是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他們的真我(就是能夠選擇自己喜歡過的生活)、找到被人愛的肯定、並且找到確實的平安和喜樂(就是在地上暫時的家和在天上永恆的家)。
我在中國的臨床關懷輔導事工上,發現有很多中國人的生活是受到基督教神學或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哲學影響不少。張先生是我採訪過的幾個基督徒之一。他的人生意義與先前所述及的曾女士不同。[2] 曾女士並不信教。她更關心的是活得淋漓盡致、生活質素凌駕一切。換句話說,她是法國諾貝爾文學得獎者加繆寫作中的典型“女英雄”。[3] 她希望做她自己選擇做的事,就好像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尼采或二十世紀的法國哲學家薩特所敘述的中心人物一樣。在張先生和曾女士的兩個故事上,我們發現在當代中國有兩種非常不同的人:張先生是被西方神學(基督教)所影響,而曾女士則被西方哲學所影響。事實上,中國與西方傳統都 有彼此互動和充實。[4] 在探討“生命意義”這樣一個難以捉摸的概念,每個傳統都有它的見地,並可以納入其他傳統的貢獻。不論是在中國或是在西方社會,這富有成果的互動和相互影響會對我們理解現今所述及的人類故事有所幫助。本章會探討一下在哲學與存在方面,西方思想是怎樣看人生意義,包括信仰、自由、仁愛和盼望。這樣一來,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傳統,我們都可以反思我們最根深蒂固、但絕無疑問的議程,和反思我們自己傳統的假設。
哲學上的所謂真實世界
這真實世界理念是起源於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與弟子的對話。柏拉圖賦予生命意義的方式,主導了幾乎整個西方思想和情懷史;不僅影響到基督教 ,也變相的影響到後基督教時代。
作爲蘇格拉底Socrates的學生,柏拉圖相信靈魂是不朽的。他解釋靈魂爲何會有苦難。蘇格拉底說,驅使一切行動的“靈魂是不朽的。”靈魂可以自由決定,因爲它不受驅使。舉例來說,當我們沒有什麼驅使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我們便能自由地決定如何做事。因此,蘇格拉底認為靈魂不朽,是因為它的存在既沒有始、也沒有終。它沒有存在的開始,是因為它不受任何因素所驅使。它也沒有終結,是因爲終結需要除去開始的驅動因素。既沒有開始的因素驅使,就沒可能有終結。 靈魂是本於天賦的“真滋養”來維持它的存在。[5] 柏拉圖相信理性是靈魂的向導,是用來管制身體的慾望,也即是柏拉圖的所謂 “胃口”。[6] 貪婪的“胃口”可引來精神病和靈魂受苦。爲了管制身體的慾望,有些靈魂在爭鬥中“斷了翅膀、再不能飛而落下地來成為肉身,被判處輪流轉世,而命的好壞是視乎前世所積下的功德。然而,隨著“理念Forms”的追求,靈魂能再次回歸天堂。在許多方面,柏拉圖的哲學(發展期是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影響了佛教(發展期大約在公元前3世紀),兩者同樣地相信慾望會導致心靈的痛苦、因果報應、輪回轉世直到得道開悟。
究竟什麼是柏拉圖的理念論呢?在他的作品 共和國 Republic裏,柏拉圖把現實分爲兩個世界:一個是成形的世界(也是理念的世界),而另一個是逐漸成形的世界。[7] 理念的世界是真實的世界。雖然看不到,但仍然是絕對真實的。柏拉圖稱之為“本質永不改變的世界”。在這真實世界裏,理念真真的存在,而另一個逐漸成形的世界卻是一個變幻不常的感官世界,衹能是模仿真實世界中理念的本質。這二分法是柏拉圖哲學的中心主題。當靈魂被捆綁在日趨敗壞的肉身時,人會覺得有苦也有甜:苦是因為人的靈魂感覺到被捆綁在肉身的無奈和痛苦,而甜是因爲靈魂可以盼望有一天能回到在天上真正的家。換句話說,認識到天家的理念會帶給在這塵世受苦的靈魂安慰與平安,令他們能再渴望回歸天堂。
由於柏拉圖認爲理念是上天的標準、理想或完美,所以世俗的一切都只是最佳的模仿品而已。鑒於此,勇敢、公正、行善、聰穎等理念變成人類的美德,即勇氣、公義、善良和智慧。事實上,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柏拉圖的弟子)藉著這個美德概念還邁進一步,開發了他的中庸之道(平均主義)。[8] 根據亞里士多德,美德可以被看作為兩個極端(虛與實)的中等級數。比如,勇氣的美德可以被視為懦弱(缺乏勇氣)和魯莽(過份性急)之間的平均級數。雖然亞里士多德並沒有詳細說明,盼望也是一種美德,可視之為絕望和過份自信的中間含意。
因此,概要來説,柏拉圖的總體構思是敘述什麽賦予生命意義。這故事有三部曲:(1)最起初的恩典 – 靈魂合宜的住在天家; (2)從恩典中墮落 – 被流放到一個生疏之地(地上的肉身); (3)被救贖重回天家 – 再次沐浴在恩典中。根據哲學家楊教授Professor Julian Young的解釋,柏拉圖所敘述的進一步表明(一)生活的目標和意義是受過去生活所影響; (二)我們有時會被離棄,引致流離失所,和對我們的存在覺得有威脅; (三)這都是我們的錯,無法管制我們的慾望/胃口,所以引致現今的病痛和苦難;(四)我們不止應該知道何謂美德,更要實踐美德才可以實現我們的人生目標。[9]
顯然,柏拉圖的總體構思對基督教來説有巨大的影響。即使柏拉圖的話語沒有提及萬能的造物主(上帝),也沒有提及上帝犧牲自己的獨生子來拯救罪人,然而基督教基本上是柏拉圖哲學的一個版本,反映相同的現實概念:真實世界和真正家園;靈魂是不朽的、是無形的;而所經歷的三部曲也很相似:就是本活在恩典中,但從恩典墮落,和終得救贖重囘恩典中。在這兩個故事中,還有同樣的兩組分類:就是自然世界和超自然世界、天與地、逐出和回歸家園。在這兩個故事中,都是靈魂自己犯錯。故此,從大約公元前4世紀初一直延續到公元後18世紀,柏拉圖哲學對西方思想的影響力可以說是巨大無比。在這期間,生命的意義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原因是基督教(也就是柏拉圖哲學的版本)似乎已提供了很明顯的答案。
直至公元後18世紀,德國哲學家以馬利·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發現柏拉圖 – 基督教傳統所敘述的真實世界出了問題,因爲在那時啟蒙運動的誕生和科學實驗的成果開始挑戰傳統的基督教。啟蒙運動的基本特色是極爲樂觀的看好人類理性的巨大力量。中古時代的信念(相信知識是來自上帝)已不再可信。人的啓蒙是經過仔細觀察這個可見的世界,再加上理性的推論而達成。在理性主義大行其道之時,上帝與靈魂的概念變得微不足道。柏拉圖的非物質理念和超自然的真實世界竟然變成一個神話。
康德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又是一個宗教保守派的支持者。他試圖分別出超驗世界和感官世界來挽救傳統的宗教信仰。[10] 他堅持認為真有一個超自然的真實世界,不斷將信息輸入我們的感官,好得過濾以後,能令我們在表面上體驗到那個真正(超驗)的世界。他建議我們所認識的空間、時間和事物,只是模仿真正世界的理念形式。比如我們戴著綠色的太陽眼鏡,那麼我們看到的所有東西都會呈綠色,儘管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的只有一些是真正綠色。康德相信科學所描述的自然時空衹是表面現象、是我們直覺的產品,[11] 而超自然的世界才是真實世界,是人衹有憑信心,而不是理性或肉身感覺,才能充份理解的世界。這信念是基於一個無上智慧的原由、所有理性的典型代表。[12] 這信念也是人存在的理由、盼望的根基。
此外,作為一個理性主義者,康德認爲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他的論點大致是這樣:(1)當我們承擔道德觀念之時,我們是相信有懲罰和獎賞; (2),但由於許多惡人興旺、好人早死,所以必須有一個來世和公義的上帝來懲罰和獎賞; (3)既然有來世公平待遇,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必定有來世的生命,令我們有理由相信靈魂是不朽的。這些基督教信念(公義的上帝、不朽的靈魂、來世的生命)都很合理,也賦予我們生命的意義。
康德以後的另一個德國哲學家,即通常被稱為悲觀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的阿瑟·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1788 1860)

廣汎的批評康德試圖挽救基督教的努力。雖然他完全接受康德區別的兩個世界論(表面的和現實終極的),但叔本華認為表面的感官世界既然是如此極盡殘酷和痛苦,他實在很難想像到在超自然世界裏會居住著一個基督徒信賴的慈愛上帝。此外,他對“事物本身”的認識與康德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爲要真正認識“事物本身”,包括上帝在内(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不但止可以慿心靈或感官來認識,也可靠種種微妙的體驗來認識。他認為親身體驗“事物本身”肯定能幫助人更了解“事物本身”。[13]
儘管叔本華的意見與康德有別,他還是相信“事物本身”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他附議基督教思想中的塵世是滿有“淚水的面紗”,需要從中得以拯救。不過他認為這拯救不是來至上帝,而是通過“自我的超越”。看來叔本華和基督教之間的區別是:他的真正世界不是上帝和天使的居所,而是佛教的無神論世界,也就是人的慾望所驅使生存的絕對性現實世界。叔本華認為“事物本身”(包括基督教的上帝)並不是什麽美好的祝福,而是“絕對應該受到譴責的本質”。[14] 在這個無神論的真實世界,叔本華認為人生的目標和生活意義是放下個人的意志和慾望才可得救贖、達成靈裏深沉的寧靜和永恆的極樂世界,也就是佛學説及的涅槃。[15] 所以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 1900)在他的後期作品裏,稱叔本華的哲學為“歐洲的佛學”。[16]

尼采在他早期作品 悲劇的誕生 告訴我們,人都是嚮往和希望尋找到(1)在悲傷中的意義和(2)幫助人超越生活悲哀的方法。[17] 尼采的問題重點是關乎希臘悲劇對觀衆的效果。這問題一直困擾著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哲學家。問題的本質是:“為什麼我們願意觀看悲劇,讓自己看到這世界的種種災難?這災難不止是人類生命的滅亡,也是人類最佳成果的滅亡。”悲劇是否可以滿足我們的需要?尼采與康德都用同一字眼“升華”來描述這種“悲劇效果”,就是觀衆可以從悲哀“升華”為超越現像世界、歸回自然的感覺,可以暫時逃脫個人苦難(現像)的辛酸和生活的折磨。雖然悲劇裏的英雄在劇終被殺害,但他的犧牲提醒觀衆,人可以有另外一種存在、一種更崇高的快感。[18]
關於以上的問題,尼采的回答是:“在生活的藝術上,希臘的阿波羅神Apollo(光明之神、藝術之神;重理性和負面看法的神)教導我們應在現實生命中雖苦猶樂;而酒神迪奥尼修斯Dionysus卻教導我們要在現實世界背後來尋求快樂。”[19] 關於苦難這現像,尼采的解釋與叔本華的不同。[20] 尼采認為,要逃避痛苦生活,我們必須超越“善惡之源頭”(即超越生命的創造和策劃者)。尼采認為一切存在的源頭,不宜是維持我們生計的仁義之君, 也不宜是加諸我們百般苦難的惡者,而是一個 “完全魯莽、沒有道德、愛開玩笑的神”。 這神動不動就將那些已建在沙堆的堡壘 (或世界) 摧毀,再重新建造新的世界來替換它。
在他後期作品中,尼采對叔本華的評語是,“在反對‘事物本身’ 必然是美好、神聖、信實和獨一這論點上,叔本華詮釋‘本身’為意願實在是踏出必要的一步,但他並不知道如何奉這意願若神明。既然他一直都離不開基督教的道德觀念(有善也有悪),他所看到的只是悪的那一面,引致他認爲‘事物本身’ (包括基督教的上帝)並不是什麽美好的祝福,而是惡劣的、愚蠢的、絕對應該受到譴責的本質。”[21]
早期的尼采,像叔本華一樣,也被稱爲歐洲的佛教徒,相信人的個別性格是一切苦難的根源,[22] 要得拯救必須要超越這根源。在尼采的著作悲劇的誕生 裏,他解釋說,“苦難是個人主觀上的需要與客觀上的發現脫節所帶來的結果。”因此,根據尼采的意見,如果人能夠放下慾念(自己想要的,而不是自己真真需要的)、超越自己的個性,便可以避免受更多的苦。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另外一位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黑格爾Georg Hegel(1870 – 1931)。

他支持真實世界的存在,但反對以康德的基督化、超自然世界為實。黑格爾將康德假設的真實世界搬遷到現實世界的未來。他認爲人的拯救不是慿基督,而是慿這世界未來的和平與和諧。在他來説,自然與超自然世界之間的區別,不過是重新解釋為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區別吧。
有鑒于此,黑格爾強調社區中合作,注重彼此團結和與自然合一。[23] 在黑格爾的論文中,“我”這個字可是意味深長。“我”實質上是解為“只為別人著想”。[24] 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家約翰-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e(1905-1980)改述這句話的中心思想:“我”是意味著你持著我存在的秘訣,幫助我認識自己和周圍的世界。舉例來說,如果我認爲自己是一個愛妻子的丈夫和慈祥的父親,我實在需要妻子和孩子認可才成事。
對黑格爾來説,生命的意義是在歷史終結時實現世界大同:你和我之間沒有隔離、衹有和諧。[25] 這才是真實世界。在黑格爾而言,生命的意義就好像基督教所説的一樣,實現“上帝之城”,但區別是,這城並不是在天上,而是在未來的大地。在尼采而言,黑格爾所提供的真實世界,不外是一種變相的“抽象安慰”,與目前環境疏離,盼望終有一天烏托邦Utopia降臨、人能活在和平與和諧中。在黑格爾而言,幸福的生活是生活在和諧合作中,是鑒于每個人在民族或社區團體的公益貢獻方面,都能認識到一己的真實自我。
再者,黑格爾認為所有人,不論社會階層,都有一個豐富和相同的意志。這是人類的本質。衹要做好自己本份,大衆的公益便可以實現,就好像個人的努力會帶來團隊的成功。[26] 黑格爾認為,個人的努力來實現貢獻公益的意識,就是人生的目標。沒有努力,什麽都不會存在。這共同努力的意志,可以克服人際間的隔離、 削減階級的差別。法國大革命就是其中一例:共同意志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壓迫。歷史展示黎明帶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更前進的社會。至少這是黑格爾的看法。這也令我們想起共產主義者在中國的革命和中國集體努力的傳統信念。這呼應了愛倫·馬歇爾教授Professor Ellen Marshall (我的母校 –克萊蒙神學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 – 前教授) 所說有關盼望的一句話:“盼望是高潔的,尤其是當這盼望是導向幸福的整體,因爲這要求我著重我的幸福是與你的幸福息息相關。”[27]
當尼采在1882年說“上帝已死了”,[28] 他不僅是說及傳統基督教的上帝,他還包括任何在人類生活中起神聖作用的個體。他所指出的真相,是根據社會學來説,西方文化已不再是宗教文化。既然一切宗教都是假設或承諾有一個真實世界,那麽在這定義上,基督教和“歐洲佛教”都是宗教,而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主義也同樣是宗教。
黑格爾認為歷史在一般情況下是體現人類的活動,而卡爾·馬克思(1818 – 1883年)Karl Marx德籍猶太人、共產主義的創始人

卻認為歷史所體現的只是純粹一種活動:就是經濟活動,是有關物質財富的生產和擁有。馬克思認爲衹有經濟活動是提供歷史的根基;其他一切 – 藝術、宗教、政治、法律 – 都是純粹建立在經濟之上,就好像啤酒上的泡沫一樣。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就是“宗教是大衆的鴉片。”馬克思好像黑格爾一樣,假設有一個天堂、一個烏托邦,能夠在歷史結束時成爲真實世界。因此,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是暗下的變相“真實世界”哲學家。馬克思也好像黑格爾一樣,棄掉柏拉圖哲學和基督教之自然與超自然世界的區別,而單單用一個藉著未來世界的烏托邦來賦予人生意義的真實世界來取代之。當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了”時,馬克思主義已是最後有關真實世界存在與否的答案,從此再沒有更多版本來詮釋能令人相信的生命意義。既然沒有“真實世界”或宗教來作盼望的基礎,人類便進入了虛無主義的世界。傳統的價值和信仰變得毫無根據。人類的存在也往往變得毫無意義和作用。
歐陸哲學
從19世紀末期到現在,“上帝已死了” 引起不少哲學家的爭論,回應所謂“生命意義”這個問題。這包括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後期作品、和約翰-保羅 ·薩特Jean-Paul Sartre、馬丁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的著作等等。他們的思想統稱為歐洲“大陸哲學”Continental Philosophy。 [29] 其主調是反對真實世界 的存在。歐陸哲學所反對的不僅是基督教的上帝,甚至酷似上帝的影子 [30] 如黑格爾的世界大同,和馬克思的烏托邦所體現的真實世界,歐陸哲學都認爲是海市蜃樓、豪不現實。這些只是人意促成來滿足人的冀望,而不是真實世界、不能詮釋生命的意義。尼采認爲“上帝之死”促使人慣常視爲最崇高的價值觀受到大大的貶值,[31] 不能再提供我們生活的方向和意義。這真空令人隨著尼采說及的“虛無主義”來應運而生(即適應時機而生)。尼采問:“如果現實是一片混亂,生命失去意義和價值,人又怎能活下去呢?”[32] 尼采的回答是:“個人故事可以令人活得有意義。”
尼采建議故事可以創造意義。無論如何,每一個真實世界論哲學家都是故事大王。從柏拉圖開始,不論那一門真實世界論哲學都藉著敘述“靈魂的旅程”故事,賦予人世界性的意義。那麼,個人故事又如何?尼采說,如果個人生活要創出意義,我們必須成為個中的英雄或主角。這裡說的英雄,並不是完成什麽偉績的英雄,而是指故事的中心人物、小說中的主角。尼采提議我們退一步來省察自己的生活,從中創建個人意義。他要求我們思考一幅圖畫:如果一個人太接近面前的東西(比如山),他所看到的前景都是細節、都是樹木。但如果這人退後一步、與所看的東西保持一些距離,這人會看到的是整個山的輪廓。尼采說看生命也是一樣。如果我們保持一些距離、彷彿是從生命的尾端來查察我們的一生,或許我們能看到全個大局、看到自己如何在個人故事中是一個如何出色的英雄、看到自己生命的意義。
這樣做,尼采稱我們為 “個人生命故事的詩人”。他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要活得有意義,就要視生活為一種富有創造性的藝術。抓緊自己所演的角色,從個人故事中體驗到自己的人生意義。尼采還說,要成為故事中的英雄,我們需要向藝術家們學習、學習眺望自己前景、用簡化和美化的藝術角度來看劇中的我…如果沒有做到這點,我們只不過是劇中的前景罷了,而不是主角。用短淺眼光看到的前景,往往誤會是何等宏大、甚至誤會爲現實。[33] 在許多方面,苦難只不過是我們用短淺眼光看到的前景誤會為現實,但如果我們稍微退一步來看、或等一刻才看,我們會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圖畫。
其實,個人故事與先前柏拉圖或基督教所述及的宏大叙事很相似,都是明察過去、實現目前、和預測未來。個人故事述及三件事:(1)過去的歷史; (2)個人的現況; 和(3)將來的生命。明白個人的過去和現在,就是明白個人的身份。明白個人的身份就會給人生存意義和目的,使人在混沌和逆境中得到支撐、對自己將來的生命加强信心、藉著盼望來“給人力量和支持、使人的生命得以完全。”[34]
尼采認為人面對生命的十字路口時,有機會選擇不同的重大決定。前述的張先生在痛苦難當之時選擇盼望。[35] 相反地,曾女士選擇自盡來解脫痛苦。[36] 但不管他們怎麼抉擇,這都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個人故事。尼采認為,我們是誰是由我們自己來創造。他認爲“存在先於本質”,這是存在主義的精髓。正因如此,他經常被視為首要的存在主義者。
尼采也相信救贖。對他來說,個人故事應該是與全人類故事同等重要,[37] 兩者都需要最終的救贖、都需要找到生命的意義來彌補人生的痛苦。但並非所有個人故事都是如此。有些故事所反映的是自我厭惡和絕望,都是主角認爲自己是受害者或惡棍而不是英雄。要有一個有救贖性的個人故事,這人必須創立一個自己所渴望和敬重的自我,才可以在個人生命中尋找到意義。要做到這點,尼采認爲,我們必須相信自己才是個人的保惠師,覺得世上的一切經歷實在是為自己好。如果能夠在每個時刻,不論是失去朋友或健康,或是失敗,都持著這態度,我們就會一次又一次看到明證,生活中每件事都缺少不得,都是對自己有深遠的意義,可為我們所用。[38]
但如何才能實現這種心態?尼采提議回憶過去的重大成就,[39] 忘卻小事和無關重要的事。[40] 他稱這為有創造性的健忘。他這樣解釋說:“米拉博Mirabeau已忘記了別人對他所做的卑劣行為。他不需原諒,因為他記不起了。”[41] 以現代心理學來解釋,這聽來就非常像看半杯水的例子,看杯是半空還是半滿。
這概念 – 心態的改造 – 為現代敘事治療奠定了基礎。回憶過去的成就可能有助於減輕現在的痛苦和苦難,“激起充沛活力來應付將來。”[42] 這力量會有助於鼓勵病者達成一己所定的目標,在絕症的陰影下也能繼續活下去,沐浴在盼望的曙光。
相比而言,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認爲生命的意義不是人自由選擇的,而是在傳統及具體的歷史情況或社會文化下發現出來的。海德格爾主要認爲傳統文化是與我們有生俱來的,而不是歸我們選擇。相反地,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社會文化已經奠定了我們心裏崇尚的不少英雄人物和與他們相關的價值觀。[43] 這些模範角色示意我們如何生活。當然,每個人仍然可以不顧社會文化的期望,選擇自己喜歡的角色。因此,鑒於每個人都有一個合一的共同目標與個別自主權,生命意義也就因人而異。
約翰-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

並不同意海德格爾的説法。薩特認為唯一真正的生命意義是在乎擁有真實的自我。如果人不接受真實的自我,而讓自我被社會文化來構成,那麽生命就沒有意義了。他拒絕接受心理決定論:他認爲人是什麽的一個人(包括將來的選擇和行動)並不是完全取決於人的個體(如生命機理、經驗等)和社會(如文化遺產、歷史等),而是由人自己去選擇。他有句話:“我是我選擇的那個人。”薩特認為我們不僅選擇自己的身份,還選擇我們的世界,用我們的價值觀來看世界如何帶給我們意義。我們的價值觀,在薩特來説,肯定是我們自己的選擇,從而創造自己的世界。李先生患結腸癌時,[44] 他可以視之為可怕的經歷、令他成為受害者;或者,他可以持著正面的心態,將這經歷視爲有啓發性、積極的體驗,促使他說:“我希望面對問題,而不是避免問題,能夠成為孩子的好榜樣。如果我停止與病魔爭戰、了結自己,我給孩子什麼的榜樣?”在任何情況下,薩特提醒我們,我們的不幸是我們自己的創造,我們要對後果負全責。既然我們的世界是我們自己的創造,我們實在沒有藉口來推卸責任。薩特的個人自由和責任説法,明顯是受到尼采的創造自我論很深的影響。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

在西西弗斯神話 的開端寫道:“只有一個真正嚴重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定自己是否值得繼續活下去。”[45] 其實,自殺這問題只是提出生命價值問題的一個戲劇化方式而已。加繆指出,人類需要相信上帝、或相信在時間的盡頭會有一個奇蹟發生。但如果這信念與現實不符之時,生命可能會變得毫無意義、變得荒唐,與現實疏離和脫節。當人的一切價值都完全流失之時,人可能會有“致命的疲勞”,甚至渴望死亡。[46] 但雖是如此推論,加繆卻拒絕接受這種説法。他認爲即使人不相信神,自殺也是不合理的。加繆認爲,“人身處沙漠中,也可以生活和創造。”[47] 事實上,加繆指出,即使人生如何的荒謬、如何的沒有意義,人也能過燦爛的生活,[48] 因爲他認為人性推動我們繼續生活下去,我們的本性都不究生命旅程的艱辛而接受過來。加繆認爲我們應該簡單地承認生命的荒謬,以勇氣、誠信、毅力和尊嚴來活得更精彩。他建議我們享受人生的旅程而不是目的地。他認為人“不需逐步建立生命,而是應燃燒起生命來發熱發光。”[49]
明顯地,加繆的英雄是活在當下的人物。先前説及的曾女士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50] 她過去常常擔心自己的業務,但自從她被診斷為轉移性淋巴瘤患者後,她學會了全力活在當下,享受著看似普通但感受非凡的生活。她說,“我覺得生活滿有驚嘆和敬畏。我盼望能和我的丈夫與孩子多些時間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話,我盼望繼續做一個有創造力的髮型師…我盼望繼續做園藝,能見到播下的種子長出令人驚嘆的盛開花朵。人人都說貓有九命。我只有一條生命,更應享受餘下的時間吧!”[51]
加繆認為期望將來會扼殺眼前的喜樂。這實在是有點道理。叔本華也以同樣的方式作如下的觀察:“人的一生都期待著會有更好的事發生…而另一方面,眼前的一切都被認爲是暫時的,都被置之不理,只看作為通往目標的路徑。因此,當這些人的生命將結束之時,大多數人回頭看都會發現他們的生活一直都沒有踏實。 他們會驚訝地發現錯失良機,在過去不經眼的和不欣賞的竟然是他們一直追求的生活目標。”[52]
生活質素
生活質素,與生命意義一樣,都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概念,所指的是意義的重要性、生活中事物的重要程度。它被定義為“促進人們心理健康和運作能力的整體满足感。 廣汎來說,生活質素可以被看為在社團生活中對成員的身心健康有直接和定量影響的每一環節 。”[53] 這是一個描述性的術語,關乎人的身、心、社三方面的健康,以及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運作能力。在身體方面,人可以營養良好和身體壯健,或是骨頭枯乾和面臨死亡。在心情方面,人的情緒可能是正面的(充滿快樂或喜悅)或負面的(經歷巨大壓力或憂慮)。在社交方面,關係可能是啓發性的或是殺傷性的,可成爲至交或孤立。可是這定義卻缺少了靈的健康:在靈性方面,人可以有平靜心靈和滿足,或是煩躁心靈和苦澀。
生活質素是因人而異、是取決於個人價值和生命意義,所以實際上很難預測到任何人的生活質素,因為不同人有不同的滿足程度。生活質素是一個概念,所以也不容易測量,與生活水平不同。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流行病學家安娜·唐納Anna Donald指出,生活質素可以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來衡量:主觀來自調查對像本身感受(如疼痛與否或痛苦的程度);客觀則來自調查對像的日常生活運作能力。[54] 她强調這兩方面的測量缺一不可。
生活質素的含義,也因用戶而異。 Matthew Edlund和Laurence Tancredi提出五種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 QoL 的看法,都是基於不同的個人觀念:(1)自我實現觀;(2)囘復正常觀;(3)社會效能觀;(4)理性觀;和(5)個人主義觀。他們建議,如果要了解生活質素QoL這短語,先要了解不同用戶的個人含義。[55] 首先,有些用戶認為QoL是實現個人目標(或自我實現)。其次,有人把它視為“正常生活”的能力,或者是“對社會有用的生活”;後者包括作爲家庭和社會的有用成員,比如在社會任職或實現許多社會的期望。第四個含義在理性人士來説,QoL的評估是離不開正義與平等,而第五個含義是以個人主義為觀點,以主觀性為主。這裡的QoL定義和生命意義是由個人所定,歸個人自由選擇而不是遵循一般傳統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在安樂死的問題上,這個衝突特別明顯:即使個人有許多理由不想活下去,甚至尋找醫師來協助安樂死,社會的公意可能會極力阻止這個人所選擇的行動。
要評估生活質素,不應只局限於身、心、社範圍內,還應包括屬靈領域在内。在苦難中的末期病患者,會利用這個最後機會,來見證他們的信仰是如何令他們死得安詳。在屬靈領域裏,生活質素的表現尤其出色,所以關懷末期病者的社區團體,更應促進病者在信仰上的見證。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榮譽客座講師羅伯特·鄧洛普Robert J. Dunlop說:
生活質素問題有助我們決定是否應採取積極措施來維持生命。如果目標不是延長生命,而是維持生活質素的話,行醫者應致力為病者提供愛心的支持和安慰。[56]
探索生存意義
如果有任何人質疑生命是否有意義或價值的話,維克托·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 1905 – 1997

提供了不少滿有啓發性的見解來回答這個問題。弗蘭克爾是奧地利籍的精神病專家,也是纳粹大屠殺的幸存者。他寫的書意義的探索Man’s Search for Meaning是基於他對人生的肯定:
我只想通過具體的例子來向讀者表明,不論在任何條件下,甚至是最悲慘的,生命都有潛在的意義。我認為,如果在集中營那樣極端的情況下證明這觀點,那麼我的書可能會得到申訴的機會。因此,我覺得我有責任寫下我所經歷的一切,因為我認為這書可以幫助那些容易絕望的人。[57]
弗蘭克斯在他的書中記載他在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作為一名長期政治囚犯的經驗。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死難營,入口就好像進入地獄一樣,令人想起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在地獄之門所題的字句:“你進入此門,就放棄所有希望吧!”

弗蘭克爾發現自己的存在被完全剝奪:他的父母親、兄弟和他的妻子都在集中營裏過世,甚至被送到煤氣爐去殺戮。除了他的妹妹,他全部家人都在集中營裡滅亡。當他失去了一切財產,一切價值都被摧毀,身體挨著飢餓與冷酷殘暴的虐待,和知道霎時間會遭受滅絕,他又怎能找到理由繼續活下去?難怪有些囚犯在絕望中完全放棄。他們拒絕早上起來作勞工,繼續睡在營裏滿有尿液和糞便的稻草上。沒有什麼可以改變他們的主意或行為。接下來的四十八小時,明眼人都知道他們正慢慢踏上死亡的道路。[58]
弗蘭克爾認為人需要一個活命的理由。他清楚地看到,那些在集中營中沒有活命理由的人,就是最快死亡的人。他認為當生命不再有意義之時,就沒有任何活命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囚犯發現自己的生命有意義之時,即使活在最惡劣的環境裏,還是會肯定生命。弗蘭克爾還認為,人不僅“有能力,如果可能的話,令世界變得更好,”而且特別是,當人不能令世界變得更好,“有必要時改變自己會更好。”[59] “試想想如有不治之症,正如不能動手術的癌症,我們將面臨挑戰來改變自己。”[60] 通過發現生命的意義,我們有能力用創造性和建設性的方法將生命的消極變為積極。[61]
因此,基本來說, 即使在最殘酷的情況下(例如在集中營裏),任何人都可以在心靈上決定自己的將來、保留自己的尊嚴。弗蘭克爾說,“我們已了解人真正是什麽。別忘記是人發明了奧斯威辛集中營裏的煤氣爐;然而,那個嘴邊掛著主禱文或希伯來詩歌、昂然進入那煤氣爐的,也是人。[62] ”信仰是生活下去的重要原因。“那對自己的將來失去信心的囚犯注定會滅亡,因爲他也失去了精神支柱;他讓自己衰亡、受到精神和肉體的腐蝕。”[63]
弗蘭克爾認為意義是不能賦予,否則會相等於説教。生命意義必須靠自己來找到。它因人而異,也時時不同。故此,生命意義不能以一般方式來定義,也永遠不能清晰的回答生命意義的問題。“生命”不是模糊的東西,而是非常真實和具體的,就好像生活任務一樣,塑造一個人的命運。每個人都有不同和獨特的命運。人與人不能相比,而個人的命運也不能與其他人的命運相比。每個情況都是獨特的,需要不同的回應。有時人會發覺,自己的情況可能需要行動來塑造自己的命運。其他時候,沉思或會對他更為有利,利用這機會來意識到對他有價值的人或物。更有時人可能只需要接受命運、背著自己的十字架。每一種情況都有其獨特之處為特徵,而對目前局勢所造成的問題,可能只有一個正確的答案。[64]
我們如何才找到這個生命意義呢?弗蘭克爾提議我們可以通過三種不同方式來找到它:[65](1)創造一項工作或做一件事; (2)經歷某事或遇到某人; (3)我們對不可避免的苦難所採取的態度。換句話說,生命意義不僅可以在外在的世界中找到,也可以在內在體驗的世界中找到,例如信仰、盼望、仁愛和自由。如果苦難可以避免,要做有意義的事就是消除其原因。但是如果苦難避不了,我們可能要改變對苦難的態度。
弗蘭克爾發現,要支取為生存而奮鬥的力量,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想著他的妻子,經常將她的樣子放在他眼前。
在我腦海裏,我竭盡所能抓緊我妻子的樣子。我聽到她回答我、看到她的笑容和她坦率而令我鼓舞的樣子。不論是真是假,她的樣子比起那旭日初升更加燦爛…我第一次看到生命的真相… 那真相就是:愛是人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也是最高目標…愛在人的心靈裏找到它最深層的意義…如果在那時,我知道我的妻子已經死了,我相信我仍然會凝視她的樣子,不會受這消息絲毫影響… [66]
弗蘭克爾發現他的生命意義和生存理由都是安息在愛懷中的盼望。這愛是“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標”。這“愛就好像死亡一般的堅強”(雅歌8:6)。即使在集中營的凄慘不幸當中,弗蘭克爾也可以發揮他最難能可貴的自由 – 就是肯定自己所選擇的態度和確認自己靈的福祉。納粹黨特勤警衛雖是殘暴至極,也無法拿走他這自由,更不能強制他的靈魂。
在弗蘭克爾來說,生命意義(或生存理由)並不是什麽哲學之談,而完全是切切實實的。簡單來說,他所發現的意義就是“意識到在現實環境中還有什麽其他可能性…意識到是否可以在某種情況下做什麼事。”[67] 弗蘭克爾認爲我們對生活的期望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生活對我們的期望。他認爲我們需要停止追究生命的意義,而把自己當作是受著生活無時無刻催逼著的人。我們對生命不應過於空談或深思熟慮 ,而應付諸行動去適當的活下去。生活最終會有什麽意義?豈不是要我們負起責任來解決生活的難題、完成生活不斷要求我們去辦的任務?[68]
批評與討論
尼采的個人意義是自由選擇。這論點出現兩個問題。首先,如果我知道我選擇的生活,不是基於情理而是隨意選擇,那麼當有困難之時,我可能會忍不住簡單的撤消我所選擇的,而重作新的選擇。結果是,有某一段時間我會扮演某一個角色,然後隨著我心情的帶領,在另一段時間我會扮演另一個角色。後果是,雖然每個角色都有意義,但我的生活會變得沒有任何意義、會變得荒謬。這是我對於視自由選擇為人生意義的第一個保留。我相信自由應該包含堅定的承諾,就好像先前在張先生的故事裏,亞姨的存在是張先生的生活理由。[69] 即使他早期婚姻所生的孩子反對他娶亞姨,他還是選擇娶她。這顯示了承擔和愛,為他的選擇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如果我可以選擇為自己編寫任何生活角色,我是不可以輕鬆地將黑手黨教父寫成“英雄”人物,一個可以對動物或小孩子善良,但當自己領土被侵犯時,可以毫不猶疑的殺人?我這例子,只是一個戲劇性的方式,來展示我的觀點,就是自由也應受道德責任所束縛。[70] 當曾女士談到找醫師協助她自殺時,[71] 她也許應該考慮到道德責任;這責任不僅是涉及自己,也涉及她的丈夫和女兒。
海德格爾似乎已經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他的觀點 – 認爲生活意義不是隨意選擇,而是在文化傳統和當時情況影響下發現出來的 – 可以接受承擔。再者,似乎道德問題也同時消失了,因為文化傳統可以作爲道德的基礎。然而,如果遷移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圈子裏,就好像筆者在現今北美已經生活了四十多年,請問這變化可會重新引入隨意選擇個人的生活方式?要知道,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道德價值。
在他後期的著作中,海德格爾提議我們的生命有一個世界性的意義, 就是作為世界的“守護者”,令我們所做的一切,總是有建設性的改變這世界,[72] 而不是妨碍這世界的發展。這生命意義反映著我們的決心來維護賦予我們的基本事物次序。這自然世界給人的感覺,是一種肅然起敬的神聖感,使我們實在無需選擇我們是否應該成為它的守護者。這維護自然的本質是與生俱來的,不是我們踏入這世界後隨意選擇的。估不到在所有人中,竟然是德國首任宰相、人稱“鐵血宰相”的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説出如下這話,“永遠不要相信一個對自然奇觀失之驚嘆的人。”[73] 海德格爾和道教徒會同意這樣的說法。現在似乎除了自然界,天地間還能令人肅然起敬的事物已是寥寥可數了。
儘管海德格爾多次否認基督教傳統神學的“上帝”存在,但毫無疑問地,海德格爾還是有一個宗教性的對像、一個令人敬虔和敬畏的對像。在他最後的公開演說中,[74] 標題是“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們。”海德格爾肯定了人是自然世界的守護者。這樣説來,他承認了人的生命意義也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個人選擇的,但他並不顧慮到人類歷史的最終命運,也沒有暗示到穿過彩虹橋、進入末後的天堂或烏托邦。相反地,衹要人還有生命氣息,守護者的任務是持續不斷的。它還提醒我們,生命是上天賦予我們的禮物。我們應該存著感激和敬畏之心來珍惜生命。
加繆否認生命意義的重要性。他說,“如果沒有意義,生命反會變得更好。”[75] 不過,我注意到,即使加繆之英雄人物過著荒謬的生活,但他們仍然有一個生活目標。比如他的英雄人物西西弗斯,終生用勞力生活在一個看似沒有理由生存下去的世界中,但如果反叛才是他的人生意義,那麽這就是他生活下去的理由。同樣地,西班牙傳説中的淫蕩人物唐璜,看似生活荒唐,其實他也有生活目標,就是盡可能多勾引女性。因此,在我看來,當加繆認爲有價值的生活並不需要“意義”之時,他所排除的意義並不是通常的生活目標,而是非常具體性的生活目標。他反對的人生意義,是“死板的跟著劇本去追求對自己有益處、對世界有和諧的人生。”但即使如此,又有何不可? 我認爲人生可以期望達成所定的未來目標,但也不必扼殺現時的喜樂。患了癌症的曾女士仍然可以成功的發展她的髮廊業務,但也可以同時“用驚嘆的心來觀賞那些播種後綻開的花朵。” [76] 我個人認為,隨著提高意識和加强自保,現在和將來都可以帶給我們喜樂和滿足。
對臨終病人的影響
我在中國採訪了不少病者,許多都是以盼望為生命意義的依歸,成為他們活下去的理由。他們的盼望是在別人的愛和支持下找到意義。這愛和支持往往來自家人,也來自朋友、社區以及醫療人士(例如醫生、護士等)和輔導員(心理和心靈)。在信仰和靈性中可以找到意義,賦予病者力量來忍受痛苦和苦難。一位做丈夫的對我說,“我妻子新信了耶穌基督,有了永生的確据。這給予她盼望,使她能夠繼續活下去。”[77] 一位做兒子的對我説,“我的父親和我都知道,無論我們的情況如何艱難,上帝都會照顧我們。我們相信萬事都會互相效力,使愛神的人得到益處…奇蹟可以發生。沒有信心,奇蹟是永遠不會發生的。”[78] 一位做女兒的對我説:“我的主、我的上帝給我力量,與我同行…當一切都失敗之時,信心和盼望支撐著我和我的母親。”[79] 一位做父親的對我説,“上帝幫助我的女兒從癌症中康復過來。我相信上帝也會幫助我。”[80] 一位垂死的少年人對我説:“有耶穌在我旁,負擔也輕省了。祈禱使我有能力活出新的一天。”[81] 同樣的見證層出不窮。誰說神已死了?無論生活看起來是多麼的艱難,信仰可以為人生和苦難提供意義來活下去。
海德格爾談論到“被判進入永生” 。他認為永生是沒有意義的。他說“如果現時的生活不能告訴他究竟他是誰,那麼永生又會有什麽意義呢?”[82] 海德格爾以為永生是永遠都有生命;現時有,死後也有新的生命。否也。永生是永恒的生命、是“有神同在的敬虔生命”。從宣告信仰那一刻開始,神的靈便進入信徒的心,與信徒同在。盼望不錯是期望將來達成目標,但切切實實的可以給現在意義。當盼望之目標實現時,自我價值會得到提升,自信也會得到肯定。
尼采所說及的“個人意義” 和“個人福祉”其實也有類似上天保佑的含意,都是人力圖萬事亨通、心態平和,但如何才能達到這心態呢?尼采稱之為“心理學上的藝術”。[83] 在現代心理學術語來説,也就是半杯水的看法,是看杯是半滿還是半空。當我回顧病人的生命故事之時,尼采的敘事方式給我很大的幫助,因爲我發覺帶出病人的人生意義來,實際上有助於減輕病人現在的痛苦和苦難,並可賦予足夠力量與病魔爭鬥來維持生命。
顯然,生命有意義時,它是值得活下去的。一個年長人在耶穌裏,找到自己的生活意義和目的,大大幫助他重燃生命的火焰。[84] 一個垂死的母親在她種植的花園裡看到新生命滋長時,她的精神振奮了。[85] 當死亡被視為生命週期的一部份時,生命就有了新的意義。此外,如能與自然合一生活,自然的死亡是好的。[86] 苦難也會有新的意義,如果人能意識到生老病死都是每個人所必然經歷之事,就好像雨水落在善與惡的人一樣,不分彼此。[87]
再者,與末期病人提及任何未了之事,也會有助於激發起求生慾,盼望完成這些事。
“我垂死的妻子極度希望看到她第一個孫女的誕生。這盼望使她積極地活下去。”[88]
“他渴望在死之前與長期失踪的兄弟聯繫,希望了解他們的家族有沒有男丁繼後。”[89]
“我曾經想到自殺,但我不能,因爲我的兒子還正在戒毒康復。”[90]
“我想為我的孩子而活。我不想他們生活在這個冷漠無情的社會裡而沒有父親。”[91]
這些都只是一些回應,表明幾方面的想法和行動來實現人生目標。在這些回應中,生命意義是非常個人化的,是根據個人的需要和情況來選擇。
文化和傳統也會使人發現意義。“我的爺爺相信殺死自己會帶給全家恥辱。”[92]“沒有一個男孫來繼後,他會感到很失望。”[93] 當然,這些人不一定會採納文化和傳統賦予的意義,仍然可以自己來選擇。
在作健康決定之時,薩特認爲“我們為自己(的健康)來選擇是天賦的權利。”他認爲生命中唯一的意義就是做一個真正的我。他鼓勵我們跟隨真我,不受傳統文化或過去的束縛。他認為文化傳統經常給我們很多負荷,或者過去也給我們不少情緒反應,但如果我們要過一個自由、豐盛、和有意義的生活,我們必須扔掉這些。相信他提出的生活方式,肯定有許多追隨者,特別是在中國的年輕人當中。
意志就是權力。這是尼采的所謂建議。他認爲這也是個人的生活意義。這建議遭受到不少批評。我們不清楚這權力是否對別人或是對自己。然而,另一種方法來解釋這點是考慮到這樣做,是為了保持對個人生活的控制。這對那些失去許多個人控制的病患者來説,尤為重要。他們要在冰冷的醫生診療室裡毫無怨言的脫衣服、逼自己在病床上不睡來等醫生巡房、和全身都插着導管 來屈辱受氣。在這些情況下,保留個人控制權是非常有意義的。
黑格爾承諾在歷史(或時間)結束之時,將會有一個充滿和平與和諧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隔離也將會一掃而清。這給人不少欣慰,特別是末期病者,因爲他們往往會退縮一角、與人疏離、避免尷尬或傷害。儘管黑格爾是一個無神論者,他所承諾的大同世界令我們想起傳統基督教的“上帝之城”。不過,黑格爾認為人的存在與否,標準是“有否效用”。他這道德觀念,“不應存在,除非有用,”是功利主義的開始,明顯地影響到社會和政治對安樂死的看法:既然末期病人對社會的貢獻有限,就應考慮到“有義務去死。” 這道德觀念帶來公意與個人意願很大的衝突。
在中國,我與病患者及其關顧者(家人和專業人士)有不少的接觸。我一再而三的聽到同樣的問題:“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我還年輕。我不應該有癌症。如果上帝是愛,為什麼上帝會給我這樣的折磨?”[94] “她從不抽煙。為什麼會有肺癌?”[95] 對這些問題,我沒有好的答案。弗蘭克爾引用的比喻,説來很有意思。
試想你在看一部電影。它是由數以千計的圖片組合而成。每張圖片都有它的獨立意義和重要性,但整部電影的含意只有在結尾才顯示出來。如果你沒有首先了解每張圖片,你根本無法理解整部電影的含意。生命(與苦難)不是一樣嗎?生命(與苦難)的最終含意,不是也在結束之時、在垂死之際,顯示出來嗎?並且,最終含意不也是視乎你盡一己的認知和信靠,來體驗生命每一環節的潛在意義嗎?[96]
“生命不貴乎長短,在乎活得有意義。”當我聽到這陳詞濫調的時候,我不期然想起雷門女醫師Dr. Rachel Naomi Remen(加州大學教授; 身心健康與疾病研究所創始人)的話,“健康不是一個目標; 健康是做有意義、有目的之事的生活方式。” [97] 在下一章,我們將會討論到盼望,這“導向幸福整體”的期望、這“賦予我們力量來生活得有意義、有目的”的動力、和“支撐我們渡過苦難”的盼望。[98]
第三章尾注
[1] Interview #8, Appendix.
[2] Refer to her story in Chapter 2, and in Interview #12, Appendix.
[3] A narrative is a 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me aspect of the world that is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grounded and shaped by human personality.
[4] David Wong, “Comparative Philosophy.”
[5] Plato, Plato’s Phaedrus, trans. Reginald M. Hackfor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247d.
[6] Ibid., 247b.
[7] Plato, The Republic, introd. Charles M. Bakewell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928),Book 7, 518C, 278.
[8]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Roger Cris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ook II.6-7, 34.
[9] Julian Young, The Death of God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3).
[10]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John Miller Dow Meiklejohn (Mineola, NY: 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2003), 238.
[11] Kant, 41-42.
[12] Ibid., 377.
[13] Arthur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vol. 2, trans. E. F. J. Payne (Indian Hills, CO: Falcon’s Wing Press, 1958), 182.
[14] In the word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8), sect 1005.
[15] Schopenhauer,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324.
[16]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109.
[17]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Francis Golffing (New York: Doubleday 1956), 124.
[18]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Birth of Tragedy,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6), 21.
[19] Ibid., 17.
[20] Ibid., 5.
[21] Nietzsche, Will To Power, section 1005.
[22] Nietzsche, Birth of Tragedy, 10.
[23]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rnold V. Mi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Preface.
[24] Ibid., parag. 642.
[25] Nietzsche, Birth of Tragedy, 26.
[26]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aragraph 584.
[27] Ellen Ott Marshall, Though the Fig Tree Does Not Blossom: Toward a Responsible Theology of Christian Hope (Nashville: Abingdon, 2006), 98.
[28] Nietzsche, Gay Science, 125.
[29] Ironically, this term is a creation of philosop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focus on the work of post-Enlightenment thinkers in continent, especially those in France and Germany. It is an umbrella concept that covers many movements, the European including German idealism,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 See “Intersections between Pragmatist and Continental Feminism,”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approach-prag-cont (accessed May 20, 2008).
[30] Nietzsche, Gay Science, 108.
[31] Nietzsche, Will to Power, section 2.
[32] Nietzsche, Gay Science, 4-5.
[33] Nietzsche, Gay Science, 78, 335.
[34] Marshall, 97.
[35] See Ch. 3, page 71. Interview #8, Appendix.
[36] See Ch. 2, page 54. Interview #12, Appendix.
[37]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ake Zarathustra, trans. Thomas Common (New York: Heritage Press, 1967), 20.
[38] Nietzsche, Gay Science, 277. This saying resonates well with what the Christian Bible says, “All things work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the Lord” (Paul’s Letter to the Romans, 8:28).
[39] Reminiscence is defined as “the act or process of recalling past events or experiences” in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0).
[40] Friedrich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 trans. and ed.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Penguin, 1976), IX, 8.
[41]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8), I, 10.
[42] Nietzsche, Gay Science, 370.
[4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Oxford: Blackwell, 1978), 384-85.
[44] Story at beginning of Chapter 2, page 40. Interview #6, Appendix.
[45] 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yphus, trans. Justin O’Brien (London: Penguin, 2000), 11.
[46] Ibid., 14-19.
[47] Camus, 7.
[48] Ibid., 53.
[49] Ibid., 133.
[50] Story of Ms. Zeng in Chapter 2 of this dissertation, page 54. Interviewee #12 in Appendix.
[51] Ibid.
[52] Arthur Schopenhauer,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Short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 E.F.J. Pay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2:285-86.
[53] Quality of life as defined by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tlanta, Georgia, http://www.cdc.gov/healthyplaces/terminology.htm (accessed May 24, 2008).
[54] Anna Donald, “What is Quality of life?” 1st ed. (2003), http://www.whatisseries.co.uk/whatis/pdfs/ what_is_QOL.pdf (accessed May 25, 2008).
[55] Jerome R. Wernow, “Saying the Unsaid: Voicing Quality-of-Life Criteria in an Evangelical Sanctity-of-Life Principle,”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391, no. 1 (March 1996): 103-22.
[56] John Dunlop, “A Physician’s Advice to Spiritual Counselors of the Dying,” Trinity Journal 14, no. 2 (Fall 1993), 206.
[57] Viktor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1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46 as Trotzdem Ja zum Leben sagen: Ein Psychologe 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Rev. and enl. ed. Trans. Ilse Lasch.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58] Frankl, 141.
[59] Ibid., 133.
[60] Ibid., 116.
[61] Ibid., 139.
[62] Ibid., 136.
[63] Ibid, 82.
[64] Ibid., 85-6.
[65] Ibid., 115.
[66] Ibid., 49-50.
[67] Ibid., 145.
[68] Ibid., 85.
[69] For Mr. Zhang’s story, see Chapter 3 of this dissertation, page 71. Interview #8, Appendix.
[70] Young, Death of God, 120.
[71] For Ms. Zeng’s story, see Chapter 2 of this dissertation, page 54. Interviewee #12, Appendix.
[72]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28.
[73] Otto von Bismarck, c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2nd ed., r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0.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for Bismarck not provided.
[74] 1966 interview with the German magazine Der Spiegel.
[75] Camus, Myth of Sisyphus, 53.
[76] Ms. Zeng in Interview #12, Appendix.
[77] Interview #1, Appendix.
[78] Interview #2, Appendix.
[79] Interview #3, Appendix.
[80] Interview #4, Appendix.
[81] Interview #14, Appendix.
[82] Martin Heidegger’s assertion that I am the only person fit to run my own life is, in a way, resonant with Martin Luther’s assertion that the ultimate authority which determines the right and the good is my own conscience. Thus, it can be argued that Martin Heidegger’s “authenticity” can be seen as preserving the essence of a Christian theology in spite of the pronouncement of “God is dead.”
[83]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IX, 8.
[84] Interview #2, Appendix.
[85] Interview #20, Appendix.
[86] Interview #21, Appendix.
[87] Interview #16, Appendix.
[88] Interview #1, Appendix.
[89] Interview #7, Appendix.
[90] Interview #15, Appendix.
[91] Interview #6, Appendix.
[92] Interview #7, Appendix.
[93] Interview #7, Appendix.
[94] Interview #12, Appendix.
[95] Interview #10, Appendix.
[96]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145.
[97] Rachel Naomi Remen, cited in Healing and the Mind by Bill D. Moyers, Betty S. Flowers, and David Grubin (New York: Doubleday, 1993), 357.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for Remen not provided.
[98] Marshall, Though the Fig Tree Does Not Blossom, 97.
第四章: 盼望
余女士是我的教友。在我們查經班結束後,她因爲知道我是醫師,所以問我對Iressin藥物有否認識。這藥是醫生開給她的媽媽麗英服食的。[1] 余女士對這藥的價錢和效用有所質疑。說真,我對這藥所知甚少,但我答應她我會查閲有關它的資料。
我以前曾見過她的母親一面。那是一年前有多。我到醫院探她時,她正因慢性咳嗽接受檢查,不幸結果竟然是肺癌,而且預後欠佳。醫生建議化療來延長壽命,但她的家人怕她完全放棄,不想讓她知道。
一年後,余女士和我同意再次探訪她媽媽。她開了摩托車來接我到他們家。他們是住在繁忙的城市中心。公寓的樓下是商舖,其中包括麵店、旅行社和文具店。路邊停放著許多摩托車。它們已經成為非常流行的交通運輸工具。在中國,20世紀後期的自行車已被摩托車和汽車淘汰了。
我們上到三樓。麗英開門來歡迎我們。一年過後,麗英的容顔已有大大的改變。那健壯結實的麗英已大不如前了,看來比她的年齡大了至少十多年:面容枯乾、眼睛凹陷。但有一樣沒有改變的,是她迷人的笑容。
“你去哪裡啦?一年啦!你幹嗎這麼久才來拜訪我這個老人家呀?”麗英說。
“老人家?在哪裡?”我開玩笑地回答說。“我剛從美國回來。麗英,你如何呀?”
“這咳嗽真要命。我不明白。已經一年半了,仍然沒有改善。醫生似乎也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媽媽,醫生不是要你入院做更多檢查嗎?你為什麼不去?”余女士插口說。
“小寶,費用很高呀!我老了,沒用了。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我寧願看到你省下這筆錢,作為你結婚用。我一直等你結婚,等了很長時間呀,小寶!”
“媽媽,如果你不舒服,錢是要花的。我剛剛有一份新工,雖然薪金不多,但至少可以喂飽三餐。我們不能再自耕自食了,對嗎?”
“是啊,小寶。稻米的收成真令我沉醉,” 麗英若有所思地說。“我還記得那豐收的場面:稻田都變成燦爛的金黃色。我最愛看的是沉甸甸的稻穗。我記得當時與其他農家女一起在初熟的稻田上工作,笑著的相互開玩笑,同時又掛上稻草人、布和繩索來嚇走飛鳥。我們做女人的邊要在外耕種,邊要在内打理家務,真吃力啊!但在收割之時,這一切勞力都變爲值得。我們把成熟的稻桿割下,捆綁起來,放在陽光下晒乾,然後將它們拖到打穀場。我真想再一次返回禾場,看看收成,即使是最後一次。”她說這話時,眼睛滿是淚水。
“媽媽,我們愛你。我們希望你快樂,”女兒急忙說。
我再補充說,“麗英,我們都愛你。我理解你對未來有百般的憂慮和恐懼。我相信你一定很難忍受這不明不白的疾病所帶來的折磨。你哀悼健康的敗壞、逝去的青春、和失去的朋友、自我價值與效能,但我真佩服你:你對家人堅定的承諾、你對工作的忠忱、你對別人的關愛。正如你驚嘆嘉禾之美,你的家人和朋友也驚嘆你對他們的愛心和忠誠之美啊!”
最後,麗英回答說,“我很感激你們所有人的支持。不錯,人生真是美妙。我希望能繼續維持下去。非常感謝你的光臨。”
在這以盼望作為結束的當下,我們就此分手。儘管死亡是迫在眉睫,麗英仍能欣賞到生活簡單自然之美,品嚐到這生命結出的甜美果實。道家説得對。大自然真令我們驚嘆、甚至令我們忘記呼吸。正如海德格爾宣稱,“現在似乎除了自然界,天地間還能令人肅然起敬的事物已是寥寥可數了。” 麗英心裏渴望回家享受那純樸生活,也盼望能看到她女兒早些結婚。就是這盼望幫助她堅忍她的痛苦,直至她四個月後安然離世。
什麼是盼望?
盼望是一個經常使用的詞,但其定義還沒有確鑿。在韋氏Webster詞典裏,動詞“盼望”的意思是“用期待的心來撫育一個願望,或是帶著信心來期望。” 這涉及到渴望和帶著信心來耐心期待美好的將來。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經文裏,這“盼望”名詞是指信靠上帝- 盼望的對像。[2] 中世紀神學家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視盼望為一種美德,是以“未來的美好”為它的對像;“很難達到,但可以達到。”[3] 在心理學術語來説,美國臨床心理學家查爾斯·斯奈德Charles Snyder視盼望為“意志力與毅力之總數”來實現個人目標。[4] 美國教牧輔導博士安德魯·萊斯特Andrew Lester視盼望為生命裏的綜合認知和情感反應,對未來的可能性和祝福有信心。[5] 美國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則視盼望為一種心態,“篤信熱烈渴望的可行性。”[6] 從這些不同類別的定義裏,我們可以看到,要給盼望一個確鑿定義,實在有些困難。
在眾多人類生命特徵之中,盼望似乎不容易解釋。我們以爲我們認識和了解它,直到我們試圖解釋它之時,才發現它似乎無視我們的最大努力。美國神學家唐納德·卡普斯Donald E. Capps指出問題出自動詞hoping與名詞hope的混亂。[7] 動詞盼望hoping是表明“一個過程或持續性體驗形式” ,就好像其它持續性體驗如“深愛著”和“正在創造”等等。至於名詞盼望hope是表明一種現像或事物,一種可以與其他現像或事物相互比較,如“信念”,“判斷”或“技巧”。所以,卡普斯將盼望hope定義為一種感知,就是堅信被剝奪了的强烈慾望終會實現。他進一步界定了盼望hope 為一種預感,可以設想到成功達成那可以實現的目標。從教牧角度來看,美國教牧神學家雷·安德森Ray S. Anderson將盼望hope看作為一種異像,是用信心的眼睛和心靈最深處的渴望來展視將來。[8]
此外,要精確地給盼望一個定義,同樣重要的是指出對盼望的誤解。[9] 第一,盼望不等於樂觀。盼望並不等於輕易或必定成事,儘管所渴望的事情在現在看來是多麽容易達成。盼望實在並不容易。盼望是知道要達成目標,會有困難、會有代價。其次,盼望並不等於默然期待。正因為盼望會有困難,個人努力實不可缺。要達成盼望的目標,過程會很艱苦,要積極參與。事實上,盼望能夠在困難之時推動我們。老實説,如果沒有期望著成功,我們一定不會辛勤的追求任何目標。第三,盼望通常不是單獨達成的。盼望之能夠成事,通常需要別人的關愛和支持。這支持可能來自家庭、社會、朋友、醫療人士(例如醫師和護士等)或輔關員(包括心理和心靈輔導與關懷者)。
盼望是人生中最早有的美德
在理想的生活情況下,我們會默默地深信未來是充滿無限的可能性。我們不一定會相信一切事都會順利,也不一定會對未來持著樂觀的態度,但我們總可以滿懷盼望stay hopeful、持著盼望hope來付諸行動、達成目標。
有兩位傳統精神分析心理學家 –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 和保羅·普鲁依塞Paul W. Pruyser – 認為這持著盼望的態度,可以追溯到人類作嬰孩時的最早人生經驗。埃里克森對盼望的主要聲明出現在他寫的一篇文章“人的長處與世代週期”。[10] 文章指出,每個人在生命週期的過程中,會形成不同的長處(埃里克森稱這些長處為“美德”)。在古代英語,“美德virtue”的意思是“固有的强度”或“强有力的性質”,都是形容藥物或烈酒的效力保持不變。因此,“ 酒精spirit”和“精神spirit”曾經有互相替換的含義,都是表示出活力來。埃里克森指出,每個人的生命週期有八個不同的特別階段,而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美德”。這八個美德都是緊扣著每個發展階段的心理動力,其中以盼望為人生最早形成的美德,其次是意志、目的、能力、忠誠、仁愛、關懷和智慧。
既然力量是建立在力量之上,這意味著盼望是其他七種動力的基礎。埃里克森並沒有說在名義上,盼望是最為重要的一項,因為他畢竟知道傳統基督教的使徒保羅,是看重仁愛比盼望和信心更多。然而,埃里克森説,在生命發展過程中,盼望真個是最為重要,因為所有其他美德都是建基於盼望。他説,“在生命中,盼望是最早發展、也是最不可缺少的美德。”[11] 如果盼望發展不來,其他所有隨後而來的美德 – 包括仁愛 –也會因此而被削弱。
埃里克森給盼望定義為“持久的忍耐,篤信可以達成熱切的願望。”[12] 他認為盼望是一個“持久的信念”。盼望不會在其生命發展階段過後突然消失。相反地,它會繼續影響整個人生發展過程。而且,在盼望的定義中,埃里克森還提議有忍耐的成份,因爲盼望是受著與它共存但對立的感知和情緒(如絕望、冷淡和內疚)之威脅。[13] 埃里克森認為加上忍耐會更好,因爲“單是將持久的信念用在各種可以想像的世界上(例如自然界的極樂、社會的烏托邦、和超自然的天堂)是不足夠給盼望定義。對於個人的現在情況來説,這持久信念只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樂觀態度。”[14] 因此,埃里克森認為,基於忍耐的成份,盼望是與樂觀有別。
埃里克森又是怎樣將盼望定位在人生最初發展的階段呢?
首先,埃里克森指出,很多人將“信心”放在最早期發展的積極態度排行榜上;他稱這“信心”為“信任”。但他反問,“當信心或信任受到損傷時,生命又有什麼動力來維持呢?” 在他來説,答案是盼望。[15] 盼望是一種基本動力,正是因爲當我們沒有客觀理由來信任之時,盼望仍會存在。盼望也是在人生中一種有獨立性的基本素質,因爲它並不會因爲所盼望的有否實現而消減。埃里克森說,“一旦成為人生經驗的基本素質,盼望會保持它的獨立性,不會受到盼望有否達成所影響。這就是成熟盼望的本性,可以隨時準備好再新一項的盼望來悄然取代已過時的盼望目標。”[16] 所以,盼望是一種生活態度;而作為一種態度,盼望並不須單單或壓根兒倚賴所定的目標達成與否。
此外,另一個支持埃里克森的因素是有關小孩子如何盼望。“在細察盼望成熟之時,人皆可以看到盼望是在所有自我意識中,帶著一種最天真的素質。”[17] 即使成年人在禱告中懇求那看不見、但掌權天地的全能上帝之時,這天真素質也會在盼望中同樣地出現。盼望對嬰兒和育嬰者(通常是母親)之間的互動萬不可少:“嬰兒的微笑激發了母親的盼望,也令母親微笑來回饋盼望給嬰兒。”[18] 這樣的互動非常重要。通過互相信任,嬰兒的盼望就因此而生。最關鍵的是嬰兒有一個初戀對像,給嬰兒安全感;也就是說,嬰兒感受到育嬰者是有條有理、值得信賴、能夠確保自己一切需要的人。所以對嬰兒來説,這初戀對像,不論是人或物(如安樂毯),就是“盼望的第一個感知和第一個驗證,從而成爲盼望的基礎。”[19]
埃里克森特別強調,育嬰者驗證了嬰兒的盼望。這育嬰者不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就好像“嬰兒視大自然為母親”一樣。這母親不僅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還可以代表大自然的養育。通過母親,嬰兒洞察人與物的持久性。故此,埃里克森強調,育嬰者所扮演的特有角色是盼望的基礎:“這育嬰者必須是盼望的最早驗證,直至現實提供其他更廣泛的角色為盼望作驗證。”[20]這育嬰者提供“令嬰兒信服的養育典範”,[21] 使嬰兒的盼望得到滿足,從而給嬰兒内心的獎賞。也就是說盼望如果能在嬰兒時期得著體驗和驗證(即驗證盼望之事能否達成),會賦予我們能力來看自己、識別自我、和處理唯我感。[22] 有盼望,嬰兒就不僅能洞察人與物的持久忍耐性,也認識到自己的持久忍耐性。
加拿大心理分析學家克利福·斯科特Clifford Scott建議,盼望之先有一列不同的動態,包括 願望wish、等待wait、預期anticipate、渴望desire、和到最後才是盼望hope,[23] 但教牧心理學家保羅·普吕瑟Paul Pruyser(荷蘭出生)卻認為,盼望與願望不同:願望是不切實際的希望,而盼望的特色卻是基於現實情況。例如在母子的關係中,嬰孩和母親雙方都會洞察到對方渴望滿足自己的期盼。[24] 在這回饋的情況下,大家都會直覺地和確實地認知盼望。這相互回饋反映著現實情況,確實肯定盼望的可信性。因此,普吕瑟認爲盼望hoping是基於現實情況,與憑空想要得到的願望wishing截然不同。[25]
當雙方的需求都能達成,盼望便因此而生。我曾探望過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她的爺爺待她不好,因爲她不是爺爺想要的男孫,但她仍然盡心盡力的照顧患病的爺爺。[26] 她的需求是爺爺的認可和接受。當他最後感謝她孝順和堅定不移地致力於照顧他時,她真是非常感動,因爲爺爺滿足了她的需求、肯定了她、接受了她,而爺爺自己的需求也基本上得到滿足,因爲他終於認識到自己已找到一個充滿愛心和信實的孫兒來完成他的盼望。當人的盼望得到驗證時,這盼望就得到培育。培育這盼望的不僅是人,也可以是物,[27] 如慈愛或支持。普吕瑟説得對,“盼望包含著豐盛的慈愛,與心裏的仇恨爭鬥,力圖修復和還原仇恨加諸人的痛苦。” [28]
盼望的發展過程
埃里克森認爲,隨著嬰兒成長為孩子,嬰兒的盼望會帶出生命的第二項美德–孩子的意志。當嬰兒微笑或將手伸出來時,這都顯示出嬰兒心存盼望,而這舉動也會隨著嬰兒的成長而增頻,直至嬰兒不單只渴望,更會在成長爲孩子之時,憑著意志來積極追求渴望的目標。此外,埃里克森還認爲嬰兒是會學到放棄自己起初的盼望,“從失望轉移盼望到更好的前景,”以及訓練自己來 “預期目標是否可以達成。”[29] 這樣,盼望的變化會越來越多,會有更多新的期望和更廣泛的選擇。在這新的環境裏,盼望會變得更加靈活和更能適應:我們不再堅持明確的盼望目標,而會接納另一個有同等價值的目標來替代它。我們會學到分辨什麼是我們想要的,與什麼是我們可以達成的;這樣的鑒別可以減少我們失望的機會。而最重要的是,即使我們沒有達成我們所盼望的,我們仍然會抱著盼望。在生命週期的第二階段裏,這持久抱著盼望的心態主要是來自兩個原因:一是因爲我們已有更佳的能力來放棄起初的盼望;但主要原因,是因爲盼望無時無刻都令我們向前望。即使某個盼望已成泡影,“另一個新的盼望會悄悄地取代它。”[30] 因此,盼望是否能達成並不會影響我們持久抱著盼望的心態。這心態會確定我們是什麽類的人,並且會繼續在我們整個人生中發展下去。
中國人對盼望的看法
中文字典有不同的字眼來形容“盼望hope”這名詞,其中有希望hope、願望wish、期望anticipation、渴望desire等,並蘊含信心faith(信任 trust 或信賴 reliance)、期待anticipation和耐力endurance(忍耐patience; 堅定或毅力perseverance)。在筆者的臨床經驗中,聽到不少個人故事,都有自動提及以上關於盼望的特點。盼望似乎帶給他們一瞥未来的機會,讓他們能夠平靜地安心接納現在的生活。一位做父親的,雖然已經病入膏肓、痛苦萬分,但他期待兒子會很快戒毒成功、有彻底康復的機會。這盼望令他内心平安。[31] 另一個做母親的,雖然已經奄奄一息,但仍然希望能看到女兒生產順利。[32] 這盼望使她奮力與病魔爭鬥、不願閉眼,直至孫兒平安誕生。人生是有苦亦有甜,有危機亦有轉機。華夏兒女正不住學習接受和忍耐苦難,但同時我們亦可以學習憑盼望來整合人生的悲歡離合:在困難痛苦之時,我們可以盼望苦盡甘來;在悲傷分離之時,我們可以期待快樂的重聚。
知足是中國人的心靈精粹,幫助我們在富足時克服慾望,在不景時克服憂慮。因此無論是順或逆境,知足都常存在我們心坎裏。知足還可帶給我們一種謙虛、無私的精神來造福人群。記得有一位女基督徒,被癌症折磨已久,但她卻能在祈禱中不忘為別人代求。這令她在慘淡的生活中仍然找到滿足感。[33]
許多知足的中國人都希望過上平淡的生活,與家人和鄰居和平共處、樂在其中。 中國有句成語,“家和萬事興。”難怪一位做父親的,因爲中了風,在醫院醫治,但當他看到自己孩子在他面前爭吵時,他情願拔掉靜脈滴注,不想活了。[34] 他盼望家庭和諧,但這盼望落空了,他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
儒家的盼望是用禮治來創造社會秩序與和諧,達成世界大同(天下為公)與小康(人各有份致力公益)。在禮記Book of Rites第九章(禮運篇),孔子論及何謂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份,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翻譯:大同實行之時,天下是屬於普及大眾的。(爲政者)須選拔道德高尚的人、推舉有才能的人;(爲民者)須講求信用,須調整人際關係、力求和睦。(在禮治下)各人不只是孝順自己父母、不只是疼愛自己孩子,還使老年人得到善終、使壯年人發展所長、使青少年和兒童都有成長。(並且)老而無妻者、老而無夫者、少而無父者、老而無子者都得到供養。男的有職份、女的有夫家(作依靠)。若是厭惡財物,棄之於地,就不必藏在己家(而應獻於公益)。 若想出力(即悔恨力量不是從己身出來),也不必只為自己(而應為他人出力)。故此,奸詐之心會閉塞而不生;盜竊、造反和害人的事也不會出現。從此,各人外出不必反鎖門戶。這就是大同社會… [35]
要達到這個目標,國家須治理合宜,而個人亦須持之以恆地勤奮修身和齊家,才能治國和平天下。現時中國國務院正努力實行醫療改革,務求全民都能得到廉宜的衛生保健服務。
孔子倡導的美德,如孝順、忠誠和敬重,對關顧末期病者方面,實在起了不少强有力的正面影響,尤其是關乎家人或朋友作爲關顧者。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這些充滿愛心和忠心的關顧者毫不猶疑把自己擺上,照顧這些面臨絕望的家人或給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培養盼望來重找生命意義和繼續活下去的理由。然而,孝道也可能有負面的影響。以中國傳統孝道來説,做孩子的有責任為父母做到最好的,令父母身心愉快和滿足他們的需要,包括他們的安全和健康。因此,難免孩子們會出於孝道往往選擇積極的醫療方案給他們的父母。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人會指責他們、批評他們不孝、不為父母做到最好的。[36] 這給做子女的極大壓力。
此外,儒家重視代代相傳的觀念。爲了尊敬祖先,中國人普遍盼望秉承先祖的遺贈,再將這遺產傳給下一代。這觀念和這盼望幫助了不少身患絕症的病者超越他們的痛苦和苦難,因爲絕望而自殺可能會帶給家族恥辱,也不是什麽有價值的遺產來傳給下一代。至於什麽才是有價值的遺產?這可能是關乎心靈(如永生)、血親(如血統)、聯係(如家庭和諧)、經歷(如意義)、經濟(如繼承財物)、道德(美德如毅力或堅持)與文化(如家族的好名聲)。這些都是考慮安樂死的病者所要顧及的。
佛教對盼望又有什麽看法?雖然佛教的苦諦(佛教有四諦:苦諦、集諦、滅諦、道諦)認為衆生皆苦,但佛教卻提供給受苦之人喜樂和盼望。經歷苦難是盼望最大的挑戰,但苦難同時也生盼望。每一個佛教徒都盼望悟道成佛(即道諦 – 進入涅槃nirvana),而佛教也提供給信徒進入涅槃的方法。美國和尚傑弗里·德格拉夫Geoffrey DeGraff(也被稱爲阿傑夫)很清晰的描述了如何從盼望的角度來看苦難。[37] 他描述盼望的過程是逐步的,就好像一個人因爲苦難而爬上盼望的梯子上。開始的第一個梯級是念住 mindfulness; 然後鬆開脚來逐步爬上梯級;下一梯級是定力concentration(使能精確的洞察人心的渴望),再而是明辨discernment。換句話說,越爬得高,視野會變得越廣闊,令人在體驗苦難中明辨生命哪一部份是歸屬哪一個真諦,並且明辨到究竟應怎樣處理不同的真諦:應否接受衆生皆苦(苦諦)?應否力圖探索和理解苦難的原因(集諦)?應否消滅這些原因、斷絕執念和煩惱、允許靈性成長(滅諦)?或是在最終爬到頂端時,能否得道成佛、進入涅槃(道諦)? 在那時候,人大可以放開梯子,得到完全自由。
阿傑夫認爲,在某種程度上,苦難是我們的導師。通過苦難,人可以明心見性、得証菩提、進入涅槃(即悟道成佛,得享永恆的極樂)。這是每個佛教徒所盼望的目標。隨著苦難的結束,盼望也就得到驗證。
阿傑夫提醒我們,如果有人認為死亡可以結束痛苦,這人就誤解了佛教四諦之中的苦諦。誰會知道輪回後的生命是怎樣的生命?很有可能會比現在的更糟。相反地,阿傑夫建議我們持著四諦來過活。既然人生必有苦難,也必有苦盡甘來。如此想法就會有盼望,盼望在世之時,終會有一天不再有悲哀、哭號和疼痛。
道家的二元性duality(或對偶性,如陰陽)對許多中國人的生活影響也不少,促使他們接受和整合對立的生活情況(如正負或光暗的兩面),並容許他們從實踐盼望中成長,學到同時考慮盼望所帶來的危難與轉機;因爲沒有危機,就沒有轉機;沒有苦難,就沒有甘甜。老子(道德經第58章)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38] 意思是:“災禍啊,幸福依傍在它裡面;幸福啊,災禍藏伏在它之中。”因此,當危難之時,我們不應該沮喪。當幸福之時,也不應沾沾自喜。生命有辛酸與痛苦,但也有甘甜。雖然有恐懼,但也可以有盼望。兩者都是我們的自我感知。如果我們真的不執著自我,多爲別人著想(得道的驗證),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懼怕危難,所盼望的一切也都可能發生。危難就好像自然界的事情(道)一樣,既來之,也會去之。老子有云(道德經第13章):“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意思是:“我為何有這大禍患呢?正是因為我老執著自我!要是我能不執著自我,我又何須懼怕禍患呢?”[39]
基於中國的動蕩歷史和有限資源,人民只好抓緊盼望來應付人生的滄桑。中國人學會改變自己來應對不可控制的情況和不可預知的將來:學會接受和寬容、適應和靈活;學會預知危難,並且用持久的耐力和信心來應付危難、用開明和直覺來探索事情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學會憑信心來展望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憑毅力走向未來和追求盼望的目標、慿互信來大家和諧共事、慿謙遜來為他人服務。然而,儘管中國人有許多美德或長處,但畢竟力量有限、人也脆弱,經不起盼望的死敵猛烈攻擊,因而會變得漠然、無望和羞愧,促使人期望“安樂死”而不想繼續活下去。
西方人對盼望的看法
盼望的四维
卡羅爾·法倫Carol Farran,凱·赫氏Kaye Herth和朱迪思·波波維奇Judith Popovich建議盼望有四個維度,可以幫助我們區別盼望與生存意義。這三個護理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員描述盼望為一種含有四維度(特性)的過程 (即身、社、靈、心四維度):1. (身)體(經)驗的過程;2. 互動(社交)的過程;3. 屬靈的過程;和4. (心理上)理性思維的過程。[40]
盼望是體驗的過程。對立辯證法可以幫助我們嘗試理解何謂盼望;也就是說,多了解絕望會幫助我們多理解盼望;反之亦然。因此,即使不少研究文獻述説何謂盼望,但也只能給我們一個概念。除非我們親身體驗苦難(如患上癌症或艾滋病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簡稱AIDS)、感受到絕望,否則我們難以充份理解盼望。苦難不僅是區區生活壓力,而是引致人感到無奈(無力改變周圍環境),因而挑起絕望的暗流。但儘管如此,“任何人都可以在心靈上、或精神上,決定自己的將來,” [41] 因爲在人的內心裏,仍然可以找到建基於個人生命意義的盼望。 在先前述及的故事裏,主角麗英雖然無法阻止自己的身體日漸消瘦,或無法停止哀悼青春的消逝、健康的敗壞、朋友的離別,和力氣的衰退,但她還可以盼望著在陽光下收成的日子,和盼望看到女兒出嫁的喜樂。[42] 她已經找到她活下去的意義 – 這就是完成豐收和做媽媽的責任。這意義賦予她盼望和活力,令她期望著好日子的來臨。我們不知道麗英是如何在逆境中仍然堅持活下去,但照我們推測,很可能是在她眼裏,禾場上勞力所帶來的豐收,和家庭中努力所賺得的成果,很可能就是她的生命意義,從而建立起她的盼望。[43] 就像尼采確鑿地指出,在她的故事裏,她情願“獻上她生命中引以爲傲的成果”,來將從前的“小器和微不足道的事”一掃而清。
盼望是互動(社交)的過程。盼望是建立在愛和支持之上。也就是說,盼望是在親密的人際關係中成長。家人、密友和護理人員的愛和支持都有助於維持病者的盼望。一個最早把望與愛聯係起來的人是法國哲學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他的翻譯員珍·諾沃特尼Jean Nowotny是這樣描述馬塞爾的立場:
在現像學的思維中,盼望無疑是本於愛的扶持。正是由於盼望是依靠著愛來扶持,所以盼望的持久信心,也是依靠著一位能確認和確保愛的主宰。就是這樣,信和愛在望中合而為一(也就是說,不論是病者或關顧者,兩者都是因爲愛才有信心來維持盼望)。[44]
馬塞爾認爲“盼望是涉及人際間的相互信任,最終是對主宰的一個回應。”[45] 這與埃里克森描述的母嬰關係極爲相似。在同樣相互信任的環境下,盼望就因此而生和發展。母親無條件的愛,驗證了嬰兒的盼望。母親就是嬰兒的主宰,就好像“上主是盼望的絕對源頭和保障”一樣。[46] 在理想的母嬰關係中,雙方都可以洞察到滿足對方的願望就是滿足一己的願望。
基督教主流神學一直都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創造,因此可以料想到人畢竟會反映出神屬性的一部份。由於神是三位一體的神,關乎聖父、聖子和聖靈之間的互動,因此人與人之間也是相關的。況且,基督教相信神是愛,是無條件的和自我犧牲的愛agape。既然愛的本質是需要在關係上來表達, 因此神無疑是相應的,而人也同樣是。
馬塞爾認爲愛與望是親密的盟友。除非愛能夠在關係上表達或活出來,否則這愛是沒有意義的。怪不得馬塞爾說,“盼望只能在關愛上存在,而不能在孤獨、自我的層面上存在。”[47] 舒伯特·奧格登Schubert Ogden說,愛神 “不單止是每個基督徒所盼望的目標,也是基督徒盼望的基礎。”[48] 既然盼望是基於愛神,而愛意味著關係,那麼盼望也必須是一種互動過程,即如人際關係或人與神的聯繋。
盼望是屬靈的過程 。 盼望,正如其他真情流露(例如悲歡離合),是不可能沒有心靈的聯繋,因為它是從心靈中活出來的。猶太教神學家亞伯拉罕·赫舍爾Abraham Heschel建議,儘管熱心能推動自我,但心靈卻能使自我邁向目標和活出盼望。他説,“雖然心靈包括了熱心和情感,但心靈並不單只是熱心或情感。心靈意味著在靈裏共享一個至高無上的權貴、旨意和智慧。在情感方面,我們可以意識到是關乎自己,但在屬靈方面,我們更可以意識到共享那從上澆灌我們的聖靈(以賽亞書32:15)。熱心是人的推動力, 但心靈所盼望的卻是人邁向的目標。”[49] “因此,盼望的根源是‘聖靈的充滿’,是慿著屬靈的信心來釋放個人的渴望,並憑著聖靈的能力邁向盼望的目標 。”[50] 基督教也肯定了人的靈是在神奇妙創造人之時賦予人的,並且還確認聖靈進入到每個信徒的内心,賦予他們能力來活出充滿盼望的人生。
哲學家和神學家都認為盼望與信心是分不開的,因爲普遍來説,盼望和信心都與心靈有聯繋。信心不能沒有盼望來維持。盼望就猶如“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希伯來書6:19)。盼望在靈裏的大能可以幫助人接受損失和容忍殘疾,而不失生活下去的信心。[51] 換句話説,信心就是盼望的依據。對己對人沒有信心,就沒有盼望。“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希伯來書11:1)。盼望可以幫助我們超越困難,因爲盼望有能力承担生活的重擔。我曾相識一位基督徒,雖然是不斷受著痛苦的折磨,但她在臨終時,仍然不忘禱告,充份表達出盼望的屬性。
盼望是理性思維的過程。幼兒階段是嬰兒繼續成長的第二期,也正是盼望在思想和行動上發展第四維度的時期。在盼望之餘,幼兒不再等待養育之人出現在眼前,反而會開始採取獨立行動,甚至會做出相反養育者期待的行動。因此,隨著能力的增加,幼兒會渴望有更多的選擇,而自主意識也就隨之而生。這發展過程都是與盼望息息相關。幼兒所盼望的不僅是期待養育者的出現,更期待有自由來思維和行動,好得發揮更多的個人選擇。
在心理學研究中最常見的維度就是這維度,分別有五個組件:目標、資源、步驟、控制和歷史感。[52] 如要理性處理,盼望的目標必須是可以實現,並且應有足夠的資源來支持。達成目標的步驟可以小,但必須積極地邁向目標。一定的控制不可少;因爲沒有控制,無奈或絕望會出現。最後,歷史感也不可少,因為盼望是展望將來,方可應付當前和過去。這些組件都指向盼望是理性的思維過程。當患了癌症的曾女士談到她的盼望時,她並不是單慿主觀渴望或樂觀的想法:
但未到那時刻(離世)之前,我還希望能活得精彩。生命真是充滿奇蹟和令人敬畏。我希望能和丈夫、孩子們同渡剩下來的光陰、和有更多甜蜜的相互擁抱。只要我還能夠的話,我希望繼續做髮型師、做有創造性的工作。我希望繼續做園藝。每當我看見那些播種後綻開的花朵時,我的心實在滿有敬畏。俗語說貓有九命。我只有一條命,所以我更應珍惜當前的生命。 [53]
曾女士有一個目標 – 就是盡量充實自己的生活。她有的資源是年紀尚輕和家人的支持。爲著達到目標,她採取的步驟包括負責任的理財和重視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努力保持一些對生活有規劃的控制 (例如在患病之餘還部份時間工作)。最後,但也是同樣重要的,她學會了放下過去的埋怨(“我究竟做了些什麼使我的運氣這麼壊?”),珍惜當前的生命(“生命只有一條”),並展望將來,期待播種後綻開的花朵。
基督教神學看盼望
依我愚見,多明尼加神學家艾丹·尼科爾斯Aidan Nichols所提供的神學定義是數一數二的合宜。他主張神學是對神的啟示作有紀律的探索。“基督徒在探索神有什麼樣的啟示時,神學所提供的建議好比‘礦脉中最豐富之一條’。” [54]“探索的目標會由傳統來設定,但方式…卻是用現今的…理論來實行。”[55] 神學專注於探索神的啟示。這啟示是神對人的自我表露。神學是有紀律的探索,因為它是基於聖經和傳統。這是探索而不是重複過去幾代所論及之事。每個神學家都知道這點,因爲每項神學真理的表達,都與當代的歷史背景有關連。故此,每一代都必須將其問題或關注付諸於神學的探索過程。雖然基本真理沒有改變,但我們對這真理的理解可以不斷增進。下面的討論會涉及基督教神學對盼望的探索。
基於聖經的盼望論。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聖經中,盼望通常是指對上帝的信任。這涉及到耐心等待上帝、尋求上帝的應許、或只是渴望和期待某事或某人來提供未來的好處。[56] 希伯來文中,有幾個動詞是用來表達盼望。其中之一,qāwâbāt (耶利米書14:22 的 ךָוֶיקֹ֭ )是滿有盼望的等待,是與信任 ḇā-ṭaḥ-tî(詩篇 25:2 的 בָ֭טַחְתִּ)同義。當耶利米稱呼神之時,他説,“我們滿有盼望的等待你”(耶14:22), 而且他還用這qāwâbāt ךָוֶיקֹ֭ 字根來形成一個名詞來形容神是以色列的盼望(耶利米書14:8; 17:13; 50:7)。另一個字根ḇā-ṭaḥ-tî בָ֭טַחְתִּ 也可作為動詞或名詞,意思是信任或依靠(詩篇25:2-3),[57] 但又往往被譯為盼望。這意味著耶和華(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是值得信賴和依靠的上帝。
在大部份的舊約時期,盼望都是寄望這個世界為主,例如被敵人圍攻時盼望得到拯救(詩篇25); 患病時盼望痊愈(賽38:10-20); 並且,以色列人信賴耶和華會提供他們土地、和平與繁榮。舊約早期的經節裏,很少説及寄望未來的世界:“下坑(死了)的人不能盼望… 只有活人” (以賽亞書38: 18-19);“與一切活人相連的,那人還有指望” (傳9:4-6)。拯救意味著從今生解脫出來。在申命記30:19,摩西引述生與死之間的選擇是明確的,“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耶和華),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該選擇不是摧毀個人生命,而是如何更好地活下去。
但這並不意味著以色列人對來世沒有認識或信心。羅伯特·查爾斯Robert Charles認為,在以色列人的早期思想中,離世歸陰間的人“還存有不少生命、活動、知識和力量,”並且“以色列人不是對來世完全沒有認識。”[58] 在舊約的尾端,盼望開始寄望於未來世界,特別是復活。上帝展示了他的計劃,就是另立永遠不敗壞的國度(但以理書2:44; 7:13-14),並使死人復醒(但12:2)。賽25:7説及上帝會 “除滅遮蓋萬民之物和遮蔽萬國蒙臉的帕子(與神隔絕的帕子),使“死人復活”(賽26:19)。這復活的盼望是信徒等候耶和華的拯救 (賽25:9)。有了信仰,相信靈魂 [59] 不死, 這便是永生的盼望,就好像與神同行的以諾被神從地上取去(創5:24),或以利亞乘旋風升天(王2:11)一樣。[60]
盼望在新約聖經的希臘文中一貫是elpizō (動詞)或elpis(名詞)。[61] 盼望是神“開恩賜給人”的禮物(帖後2:16)。舊約強調盼望為信任,而新約的使徒保羅則强調“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提前4:10)和“基督”(弗1:12)。耶利米宣稱耶和華(神)為以色列的盼望,而保羅則宣稱“基督耶穌是我們的盼望”(提前1:1),並且宣稱聖徒可以“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羅15:13)。
基督徒相信創造和供養天地萬物的上帝主要是滿有慈愛的上帝。上帝的創造和聖子(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人,是爲耶穌)正好顯示出這神聖無私的愛agape。基督是體現神的信實,使每個信徒都有原由來盼望、視未見之事為確據。雖然人不斷的拒絕上帝,但這滿有慈愛和信實的上帝仍然從不間斷的愛著人。因此,凡信上帝的人,可以將自己的未來交托這可以信賴的上帝。
耶和華對耶利米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29:11), 而在羅馬書5:5,使徒保羅相應而說,“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換言之,“信了基督 …就受了(神)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弗1:13-14 ), 可以藉著聖靈 “盼望神的榮耀” (羅5:2 ), 而不會令盼望落空。
“盼望”這詞很少在新約的四福音中出現,但同義詞是“期待”,就好像聖殿裏的西緬Simeon “素常盼望(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彌賽亞)來到 ”(路加福音2:25-26)。同樣地,聖殿裏的女先知亞拿Anna,在認識孩子耶穌之後,便“對一切盼望(期待)耶路撒冷得救贖的人講說”孩子的事(路加福音2:36-38)。盼望與等候也有密切的關連。使徒保羅“等候得著兒子的名份” (羅馬書8:23); “等候所盼望的義” (加拉太書5:5);和“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提多書2:13)。保羅熱切的期待、等候和“盼望…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保羅)身上照常顯大”(腓立比書1:20),並且接著說,“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願望)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腓1:23)。
由於盼望是與舊約的忍耐相連,所以在新約中,患難也會帶出盼望,因爲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羅馬書5:3-4),而且這盼望是“堅持到底”(希伯來書3:6)的。“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羅8:25),“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15:4)。
盼望亦是與舊約的“信賴”(上帝的應許)[62] 或 “投靠”(避難)相連。在新約,使徒保羅視盼望為信任。他“盼望立刻打發提摩太去,”但他也“靠著(信任)主,自信…也必快去”(腓2: 24)。同樣地,他把盼望與膽色相連(哥林多後書3:12)。新約的希伯來書6:18-19也提及避難和信賴神的應許,“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的人…有這指望,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 (希6:18-19) 。
舊約中不乏虛假的盼望對像,而在新約,使徒保羅也勤於勸勉信徒“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提摩太前書6:17),而是寄託盼望在上帝和基督之上,並且寄望於得救(帖前5:8); 寄望於神的榮耀(羅馬書5:2; 歌羅西書1:27); 寄望於復活(徒23:6; 24: 15; 帖撒羅尼迦前書4:13); 寄望於 “我們的身體得贖”(羅8: 23); 寄望於義(加5:5); 寄望於永生(提多書1:2; 3:7); 寄望於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提多書2: 13);和寄望於基督再來之時,“我們必要像他”(約翰一書3:2)。[63]
從上面述及的寄望中可以明顯看出,新約所述及的盼望與舊約有別。新約的盼望主要是基於末世論。復活的盼望是在舊約時代後期才開始引入,而這盼望在兩約之間的時代更大幅的增加,引致新約的使徒保羅說出復活是“以色列的盼望”(使徒行傳28: 20; 並參徒24 :15 和 26:6-8)。基督徒的盼望是在未來,若“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這實是“可憐”(林前15: 19)。當信徒離世之時,其他信徒在悲痛中寄望於主耶穌的再來,使死了的信徒能復活,不像那些不信的人在面對死亡時毫無盼望。基督徒認為,當耶穌基督再來之時,信他的人,不論是死是活,都會好像復活的耶穌基督一樣,有一個不朽的身體(林前15:20-23,51-52; 帖撒羅尼迦前書4:13-18)。
因爲上帝的應許,盼望便油然而生。基督徒的盼望就好如亞伯拉罕一樣,“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羅馬書4:18)。信徒相信上帝的應許是“擺在…前頭(的)指望”(來6: 18)。因此,盼望帶給信徒喜樂(羅12: 12)、膽大(哥林多後書3: 12)、信心和愛心(西1:4-5); 並確認信徒爲主勞苦的果效(林前15:51-58)和與主永遠同在的勸慰(帖前4: 18)。信徒可以“歡歡喜喜的盼望主(再來)的榮耀”(羅5:2; 參來3:6)和“潔淨自己、像主…一樣” ( 約翰一書3:3)。
傳統基督教的盼望是以上帝為目標,但基本上是建基於上帝的屬性。信徒與上帝所立的約 是基於上帝大能的作爲來顯示出上帝的屬性,而信耶穌基督的人更有進一步的啟示,就是耶穌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復活顯示出上帝的屬性和真理,作爲信徒盼望的基礎。
基於現代神學的盼望論 。在60年代的後期,很多基督教的教派(雖然不是大多數)都走向一種所謂“基督教無神論”的神學概念、一種認爲“上帝已死了”的神學論。在德國的神學家中,一個新的學說脫穎而出來反駁這“上帝已死了”的神學論。這學説的名稱各異,但普遍是叫盼望神學論或關乎未來的神學論。[64] 這學說的支柱是於爾根·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改革宗),沃爾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路德信義宗),和约翰尼斯·梅斯Johannes Metz(羅馬天主教)。[65] 這盼望神學論旨在引領神學指向未來,而不是過去或現在。當涉及歷史之時,這盼望神學論非常強調信心,但它堅持認為歷史所提示的意義只能在歷史終結時才趨明顯。
這盼望神學論是建基於二十世紀初阿爾貝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的末世論。借用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的話來說,莫爾特曼“説及一個走在我們前面、使萬物都會變新的上帝。我們現在認識他是因爲他的應許…令我們生動的意識到人類和社會在未來世界會如何存在,更令我們盼望著有意義的存在。”[66] 莫爾特曼認爲,現在之所謂意義,純粹是因為 它涉及未來的可能性。基督徒的盼望在乎未來歷史的發展。信徒期望那三位一體的神子(耶穌基督)所應許的能夠實現。同樣地,潘能伯格也說及“神的國度是在末世時由神自己 來引進。”[67] 但他提醒我們,這並不代表神只是在未來存在, 而不是在現在或過去。 “恰恰相反。神既然掌權將來,也掌權最遙遠的過去(包括現在)。”[68] 此外,梅斯也看到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穌基督)在世時,藉著他傳講福音和挺身出來釋放社會被排斥的人之舉動,其實已確立了神的國度,正期待著“神無條件的大愛在末世時成全神的國度”罷了。[69]
盼望神學論也是一種復活神學論。基督的復活是象徵未來新生命的開始和神所應許的將會實現。藉著基督的復活,神的應許也就好像火車頭一樣推動著歷史。它賦予心頭有重擔的人盼望。 這盼望是建基於信靠耶穌基督。憑著這盼望,信徒可以“深信神的應許將要實現。這盼望不斷賦予信徒新的推動力…邁向著自由…的實現。”[70] 梅斯認為,基督徒要迫切的期待耶穌基督的再來,才能真正跟隨耶穌、履行基督徒所應付起的社會和政治責任。
盼望神學論就好像馬克思主義一樣超越了傳統的神學界限,試圖包括整個世界,不論是政治、社會、倫理或生物各個不同領域。它自認是世俗文化的神學論。正因如此 ,盼望神學論也好像馬克思主義一樣,不止對第二世界(現有國家)有影響,對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思維也有一定的影響。
評論。這盼望神學派的德國神學家絕大部份都是寄望於神的應許會在未來實現。信徒會問:“我的上帝是未來的上帝嗎?如果我的盼望是聯繫於未來,那麽我現今活著又有什麼盼望可言?”“神的國度已來到嗎?”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M. Smith的評語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想法:
這盼望神學論是不是現今時代的趨勢?是不是物質主義和自我炫耀令到我們看不到上帝活生生的存在,因而想出這神學論來推想上帝是未來的上帝?盼望這美德是否已經悲慘的變為無可避免的心態?[71]
莫爾特曼在他跟著寫的書 結束是新的開始 裏,進一步解釋這些問題來澄清他的神學立場。 他説“耶穌的來臨是一個過程。” [72] 他指出我們可以憑著盼望來體驗到耶穌來臨時的感受。因此,即使神是在未來與我們相遇,神過去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爲和現今與我們同行已經顯露了祂自己。換句話說,對神持著盼望會帶給我們現今意義。此外,莫爾特曼也肯定了神的國度已經隨著耶穌基督臨到地上,正有待成全。這國度已經來到我們中間;我們不必再等候它。我們已經可以尋求它的義,並使其成為我們在世所追求的目標。[73] 基督教教義裏的盼望,是基於紀念聖子耶穌基督的降世爲人 、十字架上的死、復活升天、和將來的再次降臨。[74] 這盼望是源於 一個獨特的歷史事跡,並寄望這事實在未來完滿的實現:也就是說寄望在未來神的國度得到成全和掌權。我同意這樣的說法。
這關乎世俗文化的盼望神學論也導致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是否過於草率來改變世界,反而忽視了改變自己?在沃爾特·卡普斯Walter Capps的 時間進入教堂 一書中,作者説及時代的變遷如何影響宗教。卡普斯認為這盼望神學論的一個弱點是它大體上未能解決自我這問題。鑒於基督徒相當注重“關愛世界”,[75] 忽視了改變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但卡普斯指出,“隨著時代的變遷,面對壓倒性的自我問題幾乎是不可避免的。”[76]
以小弟愚見,莫爾特曼已簡潔的指出個人生活的變化實在需要盼望來支持。[77] 他指出,期待基督再來的盼望已為不少信徒創建了安穩的生活: 他們一方面等待、一方面忙著;一方面盼望、一方面忍耐; 一方面祈禱、一方面警醒;内心存著忍耐、也帶著好奇。換句話說,抱著盼望活在信仰中會令人相信有另外一個真善美的世界存在。這盼望使基督徒活得更有勁、滿有持久的活力來應付未來。莫爾特曼認爲基督徒在想不開之時,盼望會給他們安慰、給他們“一線希望”,使他們有勇氣堅持著站起來、不會在逆境中輕易放棄、更不會放棄自己、不會屈服於有毀滅性的黑暗世界中。這就是盼望的能力。[78] 在這方面,我衷心贊同莫爾特曼的看法。
然而,很少人注意到莫爾特曼並沒有把頌揚生命或活得幽默作為生存所需的不二伙伴。莫爾特曼的盼望論,似乎過於重視信仰、忽視了慈愛。畢竟這世界的創造和聖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來拯救罪人是彰顯著聖父的慈愛。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3:13所說,“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莫爾特曼的盼望神學論並沒有說及太多關於審判和懲罰。雖然他視罪惡為與神隔離、與聖潔生活脫節,[79] 但他並沒有說及人類的有限和墮落在盼望神學裏的角色。舉個例子:當一個患有絕症、飽受折磨的基督徒要求醫師協助安樂死(自殺)之時,盼望論又有何説法 ?這自殺行爲是否屬罪?這基督徒還有否復活和永生的盼望嗎?在聖經中,復活可分兩種:第一種復活是生命的更新、是獎賞;而第二種復活則是問罪、懲罰。如果真是這樣,這末期病者的自殺行爲又屬那一種?對這些問題,我一直都為答案而掙扎著。我相信上帝是一位慈愛、信實的神,“必不叫你們(信徒)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林前10:13), “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馬太福音10:22)。我同意莫爾特曼的說法:我們對神的信心和盼望能引導我們如何生活。至於永生,我知道信徒都有永生的確據,但又有誰能肯定哪個人會 不能 得救?要知道拯救來自上帝,也只有上帝能確定。
我亦同意莫爾特曼的另一個說法:作為基督徒,我們有責任促進神的國和神的義。我們這樣做不是專橫自大、而是當我們持著盼望、堅定的仰望神之時,神會高舉我們,並邀請我們帶著慈愛和憐憫的心去改變我們的世界。[80] 神的國度不僅是上帝的,也是我們的。克萊蒙特神學院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教授艾倫·馬歇爾Ellen Marshall在她所著的書 雖然無花果樹不開花Though the Fig Tree Does Not Blossom 裏力主基督徒應負起責任來實施盼望神學的論點。這無疑是贊同莫爾特曼的説法。她說,“為了達成盼望的目標,我們必須要群策群力,建立和維持有道德性的策略 。有鑒於開花結果實在是需要整體的努力,所以十分需要我們每個人的參與。”[81]
基於教牧神學的盼望論 。此外,如果不談談盼望在教牧神學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盼望論也不會完全。“教牧”pastoral 這形容詞可能會在不同環境下有不同的含義。在目前情況下,“教牧”是指合神心意的教導(或輔導)和牧養(或關懷)。事奉背景可能是個人、家庭或社會團體(例如教會、學校、醫院、軍隊、職業球隊等等)。[82] 這裡所說及的盼望論,是在教牧神學中的一種神學反思,試圖用盼望來認證一切教牧事工的實際體驗。[83] 透過這盼望神學論,從業教牧關懷和輔導 (或諮詢)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的人可以更加了解教牧的功能和從事更有效的回應來處理人的四大終極關切: [84] 絕望(無生存意義meaningless)、孤獨isolation(與人與神隔離)、信心崩潰(生活沒有踏實groundlessness)、與死亡death(生命的終結)。
在三十多年前,羅伯特·卡里根 Robert Carrigan 已經向教牧神學家和教牧輔關員pastoral counselor and caregiver提出挑戰,指出盼望在教牧關懷和輔導(或諮詢)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他説:“雖然盼望已經被神學家、哲學家、心理治療師和心理學家重視,奇怪的是:教牧神學家或教牧輔關員卻很少關注到盼望這現像。”[85] 他指的是基督教神學家(於爾根·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沃爾夫哈特·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和约翰尼斯·梅斯Johannes Metz)的盼望論。這些神學家在當時所發表的文獻已被大受重視;在討論信仰的未來定位方面, 盼望論和末世論已在基督教神學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莫爾特曼所採取的立場是:要確定一個人的基本身份並不容易,因爲人的真正身份還有待未來不同的可能性來塑造。他說,“人類總是邁向將來所期望的一切。”[86]
卡里根睿智的提醒我們,上帝現在所做的是考慮到過去和未來。這就是永恆的上帝。聖經裏所用的時間觀念,也只是把過去和未來聯結與現在,歷史學和末世論都是助長人在此時此刻的感覺和體驗,而盼望就正如卡里根所說,“把不同時間連在一起,把過去和未來與現在合併在一起。”再者,“盼望…是一種此時此刻的經歷;不單止可以令人在現在就首先嚐到‘初熟的果子’將帶來的豐盛,還可以是‘應許事情會來’的承諾。”[87]
當考慮到牧師、院牧或教牧輔關員所事奉的人(教友、病者或客戶)不時都會因爲苦難而沉溺在絕望之中,卡里根大爲不解的問,“為什麼我們這些研究教牧神學的人疏忽了盼望,沒有處理如此重要的一個論題?”[88] 遺憾的是,莫爾特曼和卡里根等人所開創的盼望神學論,很長時間都沒有影響到教牧關懷和輔導的文獻了。
直到1995年,當安德魯·萊斯特Andrew Lester 出版了他的著作 盼望在教牧關懷和輔導中的角色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盼望才受到教牧神學的重視。萊斯特認為,盼望之所以被教牧神學忽視,是因爲教牧關懷和輔導這一學科的教導和實踐都一直是受到社會和行爲科學的影響。[89] 精神分析學的世界觀使人重視過去對人類性格 [90] 發展的影響。然而實際上,我們忽視了人類是不斷期望著未來。如果我們真要清楚認識到安東·博森Anton Boisen(臨床教牧培訓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CPE之父)稱之為“活生生的人類故事”(“living human document”)[91],萊斯特認爲我們必須 同樣重視未來這維度來作全面的心理和神學理解(包括心、靈)。教牧神學的盼望論很有可能幫助到教牧關懷和輔導者更有效的處理人類所蒙受的苦難和絕望。
在萊斯特提議的教牧盼望神學論中,他提議變更範例:(1)在教牧關懷和輔導的實踐上,他仿效其他德國盼望神學家將未來這時間維度納入教牧神學裏 ; (2)他建議將教牧神學建基於人類學上,好得顧慮到人性和人情。[92] 約翰·麥奎利John Macquarrie曾經說過,“我一直都認爲現代神學的正確出發點是關乎人的教義 。”[93] 他的意思是,人類的生存環境會帶給人不同的神學反省,特別是當人面對生活中無可避免和不能理解的痛苦和折磨。 這境況可能包括個人的身份(本質或個人存在的實質 [94] )、個性、自我(包括身、心、靈)[95]、或經歷(個人的感受、想法、顧慮和慾望,以及外間世界的事物和人物)。
潘能伯格Pannenberg更進一步的提醒我們,“在現今世代,基督教神學必須建基於人類學的研究上。”[96] 這研究包括人文學科(如哲學、宗教、歷史,語言、藝術和文學)和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研究和經濟學)。他指出,要理解人類與世界的互動,不論是在實質上或文化上,都應該重視神學反思為依據。當我們試圖解釋我們的信仰或護教之時,我們都“必須在人類生存這個問題上有個好的解釋。”[97]
萊斯特跟隨著麥奎利和潘能伯格的建議,先從人類學入手來探討神學。他認為現代的神學家(包括教牧神學家),若要了解人的宗教經驗,必須從人類學開始來建立他們的神學論。他希望教牧神學最好能從對人類科學的認識和基督教傳統的智慧互取其長。通過理論和神學的整合和實踐,通過思考與行動的交替,這方法或許能在教牧關懷和輔導上有效的處理苦難和絕望。
在萊斯特所提倡的教牧神學盼望論裏,他確認了好幾個基於人類學的基本單位:[98](1)人類生存必須要有基本的時間意識; (2)這時間意識 必須要包括未來這維度,好使生命的意義和目的能夠實現;(3)凡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其中更有些核心故事會反映出個人原則是如何塑造出現今活在世上的自我 ; [99](4)這些核心故事的基本要素主要是關乎未來 ; (5)而所有破碎的人生都逃不了將來未知的困擾。萊斯特指出,儘管我們過去的經驗令我們感到危機、悲傷、焦慮等等,但真正的痛苦和折磨,實際上,是來自我們感覺到我們的未來會受到威脅或甚至已遭改變。 他認為人生的破碎,是與預測未來問題的發生息息相關;主要原因是我們往往會擔心我們的未來期望會遭受到打擊而中斷、丟失、或 失敗。
總結和討論
盼望是一個直覺的感知和不朽的信念,深信未來的期望會因爲事情的變遷或實體的介入而 得到成全。這盼望可以是上帝恩賜的一種美德,或是靠自己努力得來的一種堅毅態度,或是在人相互信任的情況下賺取的、又或者是在逐漸尋求、積極培養而發展出來的。盼望起源於一個 “轉換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就好像孩子珍貴的安樂毯一樣,讓孩子持有仍與母親融合的錯覺一樣。這客體被内在化後,再受到外界的影響而發展成名乎其實的盼望。
盼望也是一個過程。它需要認識清楚不同的可能性和困難,以及積極的參與來實現目標。盼望的盟友包括持久信任、耐心和量度(得放手時願放手)。它的敵人包括絕望、冷漠、和羞愧。與盼望對敵的,可以使盼望成為泡影;但與盼望為友的,可以幫助盼望實現目標、帶來滿足。盼望是一個可以歸因於意義的體驗過程;意義可以把盼望賦予那些身患絕症的苦難者。盼望是一個歸因於愛的社交過程;而愛是需要社群的支援。盼望是一個歸因於信仰和靈性的屬靈過程;信仰和靈性可以賦予盼望者精神力量。最後,盼望也是一個歸因於思維和行動的理性過程;理性可以促使盼望者向前邁進、努力達成可行的期望目標。因此,盼望不單只預示未來,其影響卻是在此時此地。
作爲一種態度和傾向,“負責任的盼望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勤勤實踐,因爲盼望是日常生活和道德生活 (甚至屬靈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100]“由於生活中的經歷往往壓到我們透不過氣來,我們所實踐的盼望必然也有起有落:有時結果令我們悲傷喊叫;又有時令我們雀躍不已,” “有時會驅使我們考慮多種的可能性,但有時也會逼使我們面對不少的限制。無論如何,盼望都會提升我們的心靈、 賦予我們勇氣和力量活下去。”[101] 在下一章,我們將會看到這方面的知識,在關切存在與否的事項上,如何培育盼望 。
第四章尾注
[1] Interview #10, Appendix.
[2] William B. Nelson, Jr., “Hope,”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ed. Walter A. Elwell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96), 355.
[3] 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trans. Wilfrid Lescher, vol. 2 (London: Thomas Baker, 1906), Q. 17, Art. 1.
[4] Charles R. Snyde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5.
[5] Lester,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62.
[6] Erikson,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118.
[7] Donald Capps, Agents of Hope: A Pastoral Psych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52.
[8] Ray S. Anderson, Spiritual Caregiving as Secular Sacrament: A Practical Theology for Professional Caregivers (London: J. Kingsley Publishers, 2003), 145-62.
[9] M. Cathleen Kaveny, “Cultivating Hope in Troubled Times” [online]. Lumen Magazin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November 2005), http:// www.nd.edu/~lumen/2005_11/CultivatingHopeinTroubledTimes. shtml (accessed May 25, 2008).
[10] Erikson,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111-57.
[11] Ibid., 115.
[12] Erikson,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118.
[13] Capps, Agents of Hope, 98-136.
[14] Erikson,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118.
[15] Ibid., 115.
[16] Erikson,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117.
[17] Ibid., 116. The egois the “I,” the center of consciousness, an entity comprising everything a person believes himself or herself to be, including thoughts, feelings, wants, and bodily sensations. According to Carl Jung, the ego mediates between one’s unconscious realm and the outside world.
[18] Ibid.
[19] Ibid., 117.
[20] Erikson,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117.
[21] Ibid., 116.
[22] Erik H.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W. Norton, 1968), 216-21.
[23] W. Clifford M. Scott, “Depression, Confusion, and Multival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1 (1960): 497-503.
[24] Paul W. Pruyser, “Maintaining Hope in Adversity,” Pastoral Psychology 35 (1986): 123.
[25] Paul W. Pruyser, “Phenomenology and Dynamics of Hoping,”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 (1964): 86-96.
[26] Interview #7, Appendix.
[27] Erikson,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117.
[28] Paul W. Pruyser, Th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Toward a Psychoanalysis of Cultu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19.
[29] Pruyser,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19.
[30] Erikson,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117.
[31] Interview #15, Appendix.
[32] Interview #1, Appendix.
[33] Interview #9, Appendix.
[34] Interview #17, Appendix.
[35] “On Utopia,” Chap. 9 in Liji: The Book of Rites [in Chinese], a Confucian classic believed to be edited by Confucius (Jinan, Shandong: Shandong Friendship Press, 2000).
[36] Bowman and Singer, 455-64.
[37] DeGraff (a.k.a. Thanissaro Bhikkhu), “Life Isn’t Just Suffering.”
[38] Yu-hsi Chen, “TheWay of Nature as a Healing Power,”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tress and Coping, ed. Paul T. P. Wong and Lilian Wong (New York: Springer, 2006), 92.
[39] Lao-zi, Tao Te Ching, Chapter 13.
[40] Farran, Herth and Popovich, Hope and Hopelessness, 6.
[41]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75.
[42] See story from Interview #10, Appendix.
[43] Nietzsc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9:8.
[44] Jean Nowotny, “Despair and the Object of Hope,” The Sources of Hope, ed. Ross Fitzgerald (Rushcutters Bay, Australia; Elmsford, NY: Pergamon Press, 1979), 66.
[45] Ibid., 57.
[46] Ibid.
[47] Gabriel Marcel, Homo Viator: Introduction to a Metaphysic of Hope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78), 10.
[48] Schubert Ogden, “The Meaning of Christian Hope,”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30 (winter-summer 1975): 159.
[49] Abraham Heschel, The Prophet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96-97.
[50] Anderson, Spiritual Caregiving as Secular Sacrament, 145-62.
[51] Erich Fromm,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14.
[52] Farran, Herth and Popovich, Hope and Hopelessness, 9.
[53] Story from Interview #12, Appendix.
[54] Aidan Nichols, The Art of God Incarnate : Theology and Image in Christian Tradition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80), 105.
[55] Ibid., 89.
[56] Nelson, “Hope,” 355.
[57] Ernst Hoffman, “Hope” in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ed. Colin Brown, vol. 2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76), 239.
[58] Robert H. Charles,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a Future Life in Israel, in Judaism, and in Christianity (London: A. & C. Black, 1899; reprint, Whitefish,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7), 41.
[59] Soul is defined here as the animating center of a person’s life. It is also believed to be the seat of relatedness to the divine.
[60] S. D. F. Salmond, Christian Doctrine of Immortality, 3rd ed. (Edinburgh: T. & T. Clark, 1897), 159.
[61] Hoffman, “Hope,” 238.
[62] Walther Zimmerli,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Outline, trans. David E. Green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78), 31.
[63] Paul S. Minear, Christian Hope and the Second Coming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4), 101.
[64] Some theologians wish to dichotomize these terms into two separate schools of theological thought, but they have enough similarities to retain them as a single entity.
[65] David L. Smith,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heology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92), 135-49.
[66] Stephen M. Smith, “Theology of Hope,” in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ed. Walter A. Elwell, 2nd ed.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2001), 577.
[67] Wolfhart Pannenberg, 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ed. Richard J. Neuhau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9), 53.
[68] Ibid., 62.
[69] Johannes B. Metz,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oward a Practical Fundamental Theology, trans. David Smith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0), 90.
[70]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trans. James W. Le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22.
[71] Stephen M. Smith, “Hope, Theology of,” 578-79.
[72] Jürgen Moltmann, In the End, the Beginning: The Life of Hope, trans.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04), 89.
[73] Ibid., 92.
[74] Ibid., 88.
[75] Walter H. Capps, Time Invades the Cathedral: Tension in the Schools of Hop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2), 134.
[76] Ibid., 137.
[77] Moltmann, In the End, the Beginning,94.
[78] Ibid., 90.
[79] Moltmann, In the End, the Beginning, 93.
[80] Ibid., 94.
[81] Marshall, Though the Fig Tree Does Not Blossom, 97.
[82] Taken from the Mission Statement of the Society of Pastoral Theology, accessed 4 April, 2009; available from www.geocities.com/societyforpastoraltheology/aboutspt.html.
[83] J. Russel Burck and Rodney J. Hunter, “Pastoral Theology, Protestant,”in Dictionary of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ed. Rodney J. Hunter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1990), 867.
[84] Yalom,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8.
[85] Robert L. Carrigan, “Where Has Hope Gone?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pe in Pastoral Care,” Pastoral Psychology 25, no.1 (Fall 1976): 39.
[86]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286-87.
[87] Carrigan, 49.
[88] Carrigan, 40.
[89] Lester,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21-22.
[90] Personality is defined as the totality of one’s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91] Anton T. Boise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ner World: A Study of Mental Disorder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2). The phrase “human document” is Boisen’s way of reminding us that any human being is a unique text that must be read (heard) and interpreted (the hermeneutical task).
[92] Lester,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23.
[93] John Macquarrie, “Pilgrimage in Theology,” Epworth Review 7, no. 1 (January 1980): 47-52.
[94]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vol. 2, pt. 1, trans. G. T. Thoms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7), 287-97.
[95] Anderson, Spiritual Caregiving as Secular Sacrament, 25.
[96] Wolfhart Pannenberg, Anthropolog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5), 15.
[97] Pannenberg, Anthropolog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15.
[98] Lester,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56.
[99] Similar to Georg Hegel’s “being-in-itself,” or “essence,” a nature that is fixed and immutable.
[100] Marshall, Though the Fig Tree Does Not Blossom, 107.
[101] Ibid.
第五章
與臨終病者培育盼望合理嗎?
倫理方面的考慮
當臨終病者已接受了死亡,與他們培育盼望合理嗎?[1] 詹姆斯•希利尼James Greek對末期病者的關顧有一個探討問題:“我們應否帶著盼望來接觸這些病者和家人,還是在‘情感上中立’ ?在名義上病者說是接受,但實質上是否可理解為絕望?”[2]
在我們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重要的是要知道末期病者接受死亡是採取什麼形式。接受可以是熱烈的歡迎,也可以是勉強的順從、或有其他不同的反應,包括悲哀或内心的安寧。[3] 關顧者須積極聆聽末期病者的心聲,與他們同感,理解他們如何接受他們的病情、並且洞察他們真正的需要。當垂死之時,病者往往盼望著脫離痛苦、一了百了的得到安息。對於有宗教信仰的病者來說,死亡並不可怕,反而會因爲他們可以見到上主的面容而感到高興,正如使徒保羅說,“我死了就有益處。”(腓1:21)。但若是勉強的順從死亡的來臨,便會有更多理由來盼望:例如盼望看到孩子長大成人、看到女兒結婚、孫兒誕生、和失散多年的兄弟重返家園。若是因與親人分離而悲哀過度,仍可以盼望有一天與他們歡聚。即使內心已經因接受了死亡而豁達平靜,還會盼望儘可能與自己心愛人同聚多一刻。事實上,有生命,就有盼望。即使我們沒有達到我們盼望的目的,我們仍然可以盼望。即使某些盼望目標已成過去,但更新了的盼望目標會悄然地進而取代之。盼望的目標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是因爲盼望是人的本質。
在伊麗莎白·庫伯勒 – 羅斯醫生Dr. Elizabeth Kuebler–Ross提出的“應對垂死之典型過程”中 ,[4] 最後的一個階段是接受死亡。這彷彿好像是暗示應對不來才接受死亡。許多照顧垂死病者的醫師覺得這是誤導。[5] 即使病者接受了死亡,我們還需要考慮到更基本的問題是否存在:例如“我怎麼活下去?”“我怎樣才能超越這籠罩著我整個人的陰鬱?”加拿大心理學家王載寳教授Professor Paul T.P. Wong告訴我們,
接受可以是一個積極成長的開始。要應對人生的苦澀和人的有限,就要充份利用生命最美好的。這意味著使用智慧來做最壞的打算、利用盼望來期待最好的結果、和做好準備來迎接任何事情的發生。接受正好預示人的不屈不撓奮鬥精神,照亮著人生的黑夜。[6]
這成長包括:正面的接受不好的,和憑著經驗來確認什麽才是好的。積極的接受就是當接受負面之事的同時,也不會對正面之事失去信心。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創始人維克托·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認為,即使在最可怕的情況下,人仍然可以發現正面的意義,對大自然的美善和人類的尊嚴保持驚訝。[7] 世人尊稱為老子的道家學派創始人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8] 指的是:至高的品性像水一樣,滋養萬物而不與萬物爭名利,處衆人所惡的卑微而不自高。人生之道莫過於此也。廣泛來說,“柔順和接受是道家對生活的態度,顯示出中國人樂融融和無憂慮的一面性格。”[9] 無論生活是怎樣的悲慘和惡劣,正面的接受總會帶來甜蜜的喜樂。即使在逆境之中,我們可以通過盼望,體驗到內心的平安和喜樂;通過接受生命的危難,我們可以渴望著應許的實現;通過悲劇的發生,我們可以看到生命的美麗;通過苦難,我們可以獲得啟發;再且,通過脆弱,我們可以找到救贖。
下一個要考慮到的問題是:在關顧末期病者的過程中,培育盼望是否意味著否認現實? 我所認識的一位清真寺教長跟我説,當他發現他母親需要長期的生命支持系統才能持續生命之時,他把她完全交給真主。“我知道我是抱著一線希望,但我一直告訴自己,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奇蹟隨時都可能發生。”[10] 這態度是不是否認現實?盼望末期病者的健康能夠完全康復的奇蹟,是不是否認現實或不能接受現實?這又是不是在面臨所愛的人將離世之時出於絕望的嘗試應對?如果這真是他在絕境中的應對方式,而它又能使到作兒子的心較爲好受,那麽即使他選擇了這不確定的可能性,他又應否被剝奪了這份盼望、應否被强逼面對“現實”、令他的“幻像”成空?
理論家默爾·米舍爾Merle Mishel指出,在不確定的病情之下,“幻像”可以被看為一種信念;這信念尤其是向好的方面看。[11] 換句話說,不確定的情況可以被看作為有利的機會。這與盼望有什麽關連,特別是在絕望中仍然懷有一綫希望?米舍爾認爲持著這信念的盼望可以“緩冲”無法忍受的際遇。她指出,“這緩冲作用可以阻止不利情況影響到看爲有利的可能性。”[12] 以筆者的個人意見,奇蹟可以發生。願望和祈禱奇蹟的來臨並沒有什麼不妥。然而,人們的生活必須得到帮助才能繼續前進,而不應依賴什麽神奇藥療。
有些病患者不喜歡談論自己的絕症,[13] 更有些完全避過死亡的話題,尤其是中國人。這是否意味著他們否認現實?需不需要提醒他們病情的嚴重性呢?拒絕接受,就像接受一樣,可以有不同的形式:1. 我沒有病;2. 我的病不嚴重;3. 我的病是嚴重,但不致死;4. 我的病是絕症,但暫時死不去。[14] 因此,當一個病者否認死亡是迫在眉睫,他很有可能已經接受了死亡這事實,知道自己快將死了,那又何必再提醒病者這個事實?
理查德·拉扎勒斯Richard Lazarus是一個長期研究壓力與應對的理論家。他説及維持意義不明確的好處。他舉例說,“一個懷有絕症的病者不願談論自己的病情,並不一定是否認這事實,而只是想保護自己的一種方法。不斷討論病情是會打消盼望,而當形勢不佳之時,人更需要盼望。”[15] 拉扎勒斯提到應對的兩個功能:調節情緒困擾和解決問題。有可能許多醫療人士太注重解決問題,而忽略了病患者所重視的反而是:調節苦惱、防止“失控”與避免“損害或破壞士氣和社交。”“藉著否認、理智化的分析、避免消極想法、或使用藥物等等 … 他們可能會覺得好過一些。”[16] 因此,如果病者選擇含糊一些, 輔關者又何必堅持理性的說實話呢?英格·科利斯Inge Corless認爲這兩種獨特的世界觀 (一方是基於信心和盼望;另一方是基於實證主義和科學探討)是可以在一個有創造性的協商情況下共存,而不需要彼此爭佔優勢。[17] 不論是回教徒、道教徒、佛教徒、或儒家學者(即無神論者)都應該有餘地來為自己選擇不確定的可能性。或者對輔關者來說,與末期病者談論死亡,不如更明智的與他們談論生活,鼓勵和支持他們維持正常的日常生活。
總括來説,筆者堅信在倫理上,幫助末期病者培育盼望是合理的。
存活方面的考慮
這一章的第二部份,是嘗試提出理由來説明盼望是否能(在不同的維度下)特別適合末期病者來應對他們常有的存活問題。歐文·亞隆Irvin Yalom確定人有四種存活關注:一、生存沒有意義meaninglessness;二、陷入孤獨狀態isolation;三、過著虛無生活groundlessness;四、憂慮死之將至death。[18] 在人生不同的階段中,人都會意識到這些關切,其中最令人擔憂的無過於死亡。
面對存活關切又可稱為面對“虛空void”。[19] 當人患上癌症、或喪親、或有其他個人悲劇令他們感到痛苦和受盡折磨時,他們會感到絕望和虛空。 “不少生活情況都會令人提出有關意義和盼望的問題。例如:當你看到心理失常的持槍者屠殺無辜的浩刧、或探訪兒童醫院的腫瘤科病者、或步過德國大紹博物舘Dachau Museum的集中營展覽、或聽到所愛的和信任的配偶告訴你要離婚、或參加那個在診所被槍殺的醫生葬禮,這些都會令你想及生命意義和盼望的問題。”[20]
當人面對虛空,可能有兩個不同的體驗。有些人會體驗到超自然的主宰,也就是基督教所敬拜的上帝,在虛空中也可與人同在。詹姆斯·洛德James Loder說過,我們可以在虛空中看到“上帝的臉”;在生存掙扎中, 意識到超自然的盼望源頭。[21] 然而,有些人會有一個可怕的體驗,就是在虛空中發現虛無groundlessness和絕望。不少評論説過,在面對存活問題之時,人只會專於擊退無意義的存活,但很少重視如何努力來應對現實生活的絕望。
生命毫無意義meaninglessness與盼望的關連
當人在痛苦中邁向死亡時, 他們常常會問:生存下去又有什麽意義?末期病者在疼痛之餘會問:“活下去又何苦呢?我如何活下去呢?”這些問題曾在第三章討論過,不容易有答案。爭論總是不絕於耳。問題是:究竟生命意義是因人而異,抑或是普及呢?如果 “上帝已死”是真的,如果人的生命不再有神賦予目的,那麽我們豈不是要靠自己來構造生命意義,或通過傳統文化來得到啓發?儘管這些問題聽起來好像不切實際、過度哲學化,但它們確實是末期病者一直在考慮存活與否所關注的問題。
意義和盼望是相關但不同的概念。兩者都涉及身體的經驗(包括事件的發生、相關情緒、擔憂和需求)、別人的支持(社團關係)、靈性的依靠(信仰或信念)和理性的心思(富於創意/見識的心思或態度)。[22] 兩者都非常受文化、傳統或社團影響。然而,正如此論文的第三章指出,生命意義是指一般關於生命價值和重要性的概念,而盼望則是關係到生命的預期目標,是用來引導人的一切生活舉動。這盼望就好像生命目標一樣,不止關係到未來的展望或預測,還影響到現在,緊扣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
滿懷盼望Hopefulness與盼望Hope其實也有些不同。滿懷盼望不是概念,也不是期望目標,而是一連串的過程,是憑直覺來持久相信在未來將會達到可以實現的目標。滿懷盼望與意志也不一樣。滿懷盼望是嬰兒期中發展最早的一項美德,比意志發展還要早。滿懷盼望不止是(1)持久相信所渴望的福祉將會實現(這福祉甚至包括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安樂”死);還涉及到(2)積極運用資源來克服各種障礙;從而(3)逐步邁向目標的達成、(4)更新生命意義和期望目標和(五)辛勤地達成目標。 既然滿懷盼望有這些特點,那麽培育末期病者更新他們的生命意義和盼望又有何不可?這盼望似乎是特別適合幫助他們來面對似乎再無意義的生活、及積極應對他們的病痛和苦難。
基於生存意義的盼望。這並不是簇新的概念。[23] 維克多·弗蘭克爾Victor Frankl所作的書 人對意義的追尋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最先令我們注意到這一點。盼望不一定是相信結果完滿,而是持久相信,將來無論發生什麼事或結果是如何,也會有其意義。[24] 黛布拉·帕克-奧利弗Debra Parker–Oliver認為,滿懷盼望是對將來發生的事件所附著的意義 (而不是事件本身或結果)帶著積極的期望。[25] 不錯,這個定義的取向是“積極的”,因此抵消了“虚幻盼望false hope” 或盲目樂觀的說法。然而,這定義似乎是否定了盼望是寄望於可以實現的目標。既然寄望的重點是人生意義,而不是事件本身能否達成,那麽寄望的目標又何須真能實現?不過,這定義最大的貢獻是認識到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追尋新的人生意義來塑造新的盼望。這種盼望可以幫助人在最無奈的生活情況下仍然保留一些個人控制、設置個人目標、不再容易地受到別人的價值觀或世界觀所影響。這樣,只要生命有意義,就有盼望。盼望的關鍵不在於生活事件,而是在於這些事件所創造或啓發的意義。
一位探討死亡與臨終經驗的權威人物 – 伊利莎白·庫伯勒–羅斯Elizabeth Kübler–Ross醫師 – 曾寫說:“看着一個人平静地死去,令我們想到一顆流星, 在漫天星星中閃出短暫的光芒,轉瞬間便永遠消失在無盡的黑夜中。” [26] 但人會問,生命果真如此嗎?世俗文化普遍不相信絕症病患者會有盼望,但如果盼望是取決於意義,而意義是透過特定的文化脈絡來構成的 ,那麽,在病者垂死之時,培育盼望還是合理的,因為在他們搜尋意義之時,會更容易尋著平安。[27]
凱瑟琳·范斯洛–布倫斯Catherine Fanslow–Brunjes等人建議,垂死病者的盼望可涉及四個不同的階段:[28] 他們盼望(1)病得痊愈; (2)治療順利; (3)壽命延長; 和(4)死得安詳。因此,他們所盼望的目標是可以改變、可以重新調整、專注或定義的。這過程之可以採取不同的形式,完全是取決於病者所期望的個別目標。至於培育盼望的的主要挑戰,是幫助垂死病者自發創造或搜尋新的意義,好使這意義就像流星一樣,在空中跌下來之前盡量發揮它的光芒。這建議應該會有助於克服垂死病者所慣常感到的無意義存在。
孤立與盼望的關連
在人的生活中,要體驗自我是需要敞開一己心靈,建立人際互信和支持。這可能涉及到與他人或與那至高無上者靈裏相通。至於人的身份,與其說是通過自我反思來決定,不如説是通過有意建立人際關係的行動來確定。約翰·麥克默里John MacMurray說得好:“我需要你來保持自我。”[29] 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在他的難忘經典論述中,説及自我不單只是個人性的,也是相關性的。他寫道:
你和我的互動純屬恩典 – 是無法通過搜尋才找到的。我–你這基本字句,也只能憑全人(身、心、社、靈四方面)來表達。 全人的專注和融合,不能單由我來完成,也不能沒有我來成全。我需要你成為我:我的存在,不能沒有你。[30]
關係固然重要,但人與人(或與神)之間仍然會有鴻溝出現,引致個人隔離。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患上絕症可能是原因之一。絕症病患者往往自築繭來避開別者(包括上帝)、孤立自己。他們也可能覺得親朋戚友們都視他們像染上瘟疫一樣,所以避開他們。[31]
隔離的第二種形式是內心隔離。這是一個區分部份自己的過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術語“隔離”是描述一種防禦機制,在強迫性神經病方面尤其明顯。這是將不愉快的聯想中斷,與一般的思維過程隔離,目的是使自己好過點。[32] 在現代心理治療中,“隔離”不僅是指正式的防禦機制,也通常意味著任何形式的破碎自我。因此,當一個人抑制自己的情感或慾望而接受“應該”作為自己的願望,或不信任自己的判斷,或埋沒了自己潛力之時,這就是內心隔離。
此外,存活隔離又是更基本的一種隔離。無論人如何密切的與別人建立關係,最後仍然會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人是單獨的來這世界,也單獨的離開這世界。[33] 在初有意識的那一刻,人便允許意識來創建一個自我形像,與世俗有所區別 。這自我有一種本能尋找那至高無上者。[34] 根據本·米喬科維奇Ben Mijuskovic,[35] 人根本上是孤獨的。我們不能不面對這事實。雖然根據麥克默里MacMurray和布伯Buber的建議,人是需要別者(包括神)來構成自我,但人永遠都無法完全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意識。
我們不時都會遇到一個絕症病患者用防禦機制來隔離自己、避免別人打擾。作爲輔關者,要克服病患者這種自我退縮,要給這病患者多些空間來表達自我和建立人際關係,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舊約神學家沃爾特·布呂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提醒我們:“當人能公開表達和處理一己的苦難和悲痛之時,盼望就會冒出頭來。”[36] 要是失喪者刻意抑制痛苦、憤怒和悲傷,反不如致力表達和處理自己的悲痛,讓盼望來釋放自己、化痛苦和失落為力量、重新創造和參與新的生活目標。
伊萊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 很有見地的提醒我們,身體上的痛苦是很難充份表達出來的。疼痛會負面地影響病患者的社交和心靈、令病患者失去個人存在感。更矛盾的是,在同一時間,疼痛會完全覆蓋病患者的存在感,加增了輔關者有效地幫助病患者的難度。“疼痛有能力抹殺自我與外在的一切關連。”[37] 斯卡里告訴我們,人的感覺和感受通常都有一個對像或方法來表達,但疼痛不是一樣。疼痛往往令人孤立,令自我寂而無聲、表達不來。
基於這説法,斯坦利·豪爾瓦斯Stanley Hauerwas說:“疼痛是群體生活的敵人,因為我們實在無法感受到彼此的疼痛。”[38] 如果嘗試用藥物來麻木這疼痛、或尋找疼痛的原因來避過疼痛,豪爾瓦斯卻認爲這只會“剝奪病者在生活上一切寶貴的體驗。”[39] 上述的張先生,不願意服食止痛藥,是因為他希望“保持思維比較上清晰,盡可能與阿姨分享寳貴的時光。”[40]
如果我們相信上帝的旨意是令我們遠離疼痛、無苦無難,我們實在是歪曲了我們對上帝和對人的理解。神學家雷·安德森Ray Anderson提醒我們,我們不應對上帝的良善和大能持著太不實際的理解,影響到我們不能接納上帝可以在這充滿邪惡的世界裏擔負任何角色。[41] 同樣地,我們也不應該太理想化無痛無難的自我,影響到我們不能接受一些人是需要在多重自我形像中找到他們的真正身份。
當面對疼痛和苦難之時,人常常有兩種可能心態。一是順從天命,接受痛苦是不可避免的現實,以爲一貫支撐著我們的上帝現在不再維護我們了。另一選擇是逃避和否認,啓動應對機制來遮掩現實。兩者都不是明智之舉。
保羅·普魯伊瑟Paul Pruyser建議,若漠視疼痛和苦難的存在或感受,便是形同逃避,未必是最適當的回應。他認為即使憑著盼望、倚靠未來的承諾是可以暫時緩解劇痛所造成的苦惱,但這只會令人與現實環境脫節。或者可以説,一個更好的選擇是承認和表達自己的隔離狀況,從而正視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42] 也許這樣做,會使病痛者領會到別人的關愛。相反地,如果太過埋首於自己的隔離,便不能接受他人的好意。反之,病痛者會有一種傾向、責怪別人作為自己隔離的藉口。在這種情况下,本來可以是建立真正關係的良機,卻變得脫節和扭曲了。
普魯伊瑟建議我們重新回到上主的懷抱,“認識那以仁慈爲主的上帝、察看到祂對人的善意是在數不清的事件上和預料不到的形式中顯現出來。” 正如歐內斯特·瓊斯Ernest Jones (精神分析學家)所説,“一個人真正想知道的是上帝打算對自己履行什麽目的 。” 普魯伊瑟的結論是,“人若要尋求主,最重要的發現是真正認識這仁慈的上帝。祂未曾應許我們在患病時用奇蹟醫治、在危難時差遣天使來拯救、或在垂死時延長壽命。但祂的慈愛是與人的慈愛很相似,是應許我們在危難時與我們同在;這並不是在將來,而是在現在,在我們痛苦萬分的那一刻。”[43] 這與進程神學家Process Theologian李·斯諾克Lee Snook所提出的觀點是一致的:“基督徒盼望的基楚和目標是上帝的信實,”而不是“在來世憑著不朽壊的身體生活在天堂裏,”因爲對基督徒來説,後者已得到確據。“基督教信仰,既不能預測未來,也不能保証未來,”但“信實的神已在耶稣基督裏確實了祂的應許:就是答應信徒無論情況如何,神的慈愛也會與他們同在。”[44]
基於愛和支持的盼望。豪爾瓦斯Hauerwas建議,當我們在群體的愛和支持下體驗痛苦,會發現一股生命的奔流輸注入體,讓我們流失的生命,通過群體的專注關愛,再一次流回到我們身上。[45] 在人際關係中,彼此的痛苦和喜樂都可以互相交流,從而藉著彼此關懷和心靈醫治的大能,在群體的生活中得到回復健康。正如聖經所說:“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哥林多前書12:26)。
我們曾討論過滿懷盼望是一個群體關係過程,而不是出於獨處或隔離狀況。與他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就更有能力來盼望。羅伯特·比弗斯Robert Beavers和佛羅倫斯·卡斯洛Florence Kaslow觀察到抱著盼望這過程並“不是存在於真空裏,而是多與他人分享個人體驗,”[46] 與別人一同盼望、也為別人盼望。這超越了個人的孤獨和自我需求。“群體是盼望的媒介。”[47]無論這群體是家庭或朋友、社會、國家或教會,懷著盼望的人會感覺到與它相連。我們理應尋找能夠分享和展望我們的盼望之群體。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說,“光靠自己是不能實現盼望的。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群體的作爲。”[48] 儘管絕症病患者有隔離自己的傾向,但他們實在盡量需要各方的鼓勵和支持來培育盼望的成長。 在面對絕望之時,他們更加迫切需要建立關係來養成盼望, 就好像起源於嬰兒期的盼望是基於信任和愛。新的友誼(或重新發現的友誼)可以開拓未來,產生滿有活力的盼望:“當友誼有個新開始,時光便開始再次移動,同時盼望就好像藏在記憶深處的旋律一樣,再次被喚醒。”[49] 反過來說,破裂的關係會引致盼望的失落,而親人的失喪所帶來的悲痛往往也會導致絕望感。因此,輔關者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堅定不移的承諾,得到病患者的信任 。
盼望能通過相互信任和關懷而被找到。在這相互關係中,彼此幫助,令對方感受到自由和尋找到自我,並且變得完全自主;[50] 但有些人際關係卻對盼望是有破壞性的,特別是有一方喜歡支配、虐待、利用、或看不起另一方的非互惠關係,單方面索求服從和順服、或索求依賴作為被愛的條件。這些條件往往使對方感到壓抑,阻礙了個人成長和盼望的發展。因此,最好就是結束這種非互惠的關係,防止絕望、促進盼望。凡沒有盼望的人往往會覺得很難信任別人,認爲別人不理解自己,並且相信如果沒有自己的存在,別人的生活會過得更好。故此,無望之人實在難與別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或群體。
關於陷在苦難的人,威廉·林奇William Lynch寫道,“也許他們的絕望不可能是真正對別人絕望…也許它是對自己絕望。”[51] 我們曾經看到,當人絕望之時,是如何自築繭與他人隔離,並且往往不願與任何人建立深切關係,甚至對什麽都顯示出毫不相干的態度,不願作什麽承諾。他們往往變得孤單、離群、寂寞、和隔離。要他們建立關係來逃出隔離,實在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要求,除非有關心他們的人或群體主動的用真正的愛心和友誼來伸出援手,否則他們將會繼續維持孤立和隔離的狀況。當病患者的家人或朋友退出關顧之時,我們要考慮到他們很可能已經開始感到無望。即使建立關係不能完全消除隔離,但至少可以撫慰病者在隔離中的痛苦。
無所依據groundlessness與盼望的關連
盼望是與個人自主權的發展(即第二個發展期 – 幼兒期 – 的意志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但無可否認,這嶄新的自由意志也可以帶來焦慮和懼怕。這是事實。不錯,自由通常會被明確的視為一個正面概念,而西方的文明史也是一直嚮往和爭取自由,但正如精神學家歐文·亞隆Irvin Yalom指出,在存活觀點來看,自由也可以帶來懼怕,因爲人不能再處身於久已習慣的安定和有條理的環境中 ,所以免不了有些失落和無所依據。
自由會給人責任來選擇與作主、創造和設計自己的世界,但約翰–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卻認爲,在某種程度上來説, “人得到自由就好如被責難一樣,”[52] 因爲如果正如羅洛·梅Rollo May所説,真實的自由是要正視命運的局限,[53] 那麽依薩特之見,有自由來突破局限、開創自我和設計自己的世界,[54] 也會意味著自由人的腳底下,並沒有什麽依據可言,只能是一個深淵、一個空洞、一個虛無,就好如被責難一樣。
不過,薩特還是認為人是可以自由選擇或創建自己的人生意義(而不是世界)。在這方面,弗蘭克爾Frankl不同意薩特的説法。他指出,賦予自我這種富於創造性的能力,似乎仍然是太過理想化,離不開薩特所反對的舊有傳統思想。弗蘭克爾比喻薩特所説及的自由,就好如騙子慣常用的技巧一樣:騙子聲稱向上拋出繩子,可讓一個男童憑著繩子向上爬;這無疑就好像薩特意圖使我們相信的説法一樣,認爲人是可以創建自己的生命意義。弗蘭克爾爭辯說, 這好如在無可依據的情況下,竭盡所能向上爬,所得到的結果無非只是虛無。[55]
自由和無可依據這兩個概念實則上牽涉到責任,但對生活狀況來説,不同人有不同的責任感。在自由驅使下,當人有不滿之時,會將責任推卸給別人(例如老闆或配偶)身上,或歸咎於環境。有些人甚至在被輔導之時,也只會全盤依靠輔導員,拒絕爲自己的康復負責任。更有些人會把自己看作是無辜的受害者,被外在事件處處逼害,但卻拒絕接受自己才是事件的啓動者。
其次,自由也牽涉到意志和行動。我們已經看到在嬰兒成長為孩子的過程中,第一種美德的出現便是盼望。這盼望激發了意志,也就是盼望之後的第二種美德。孩子在成長時會將這意志建立在基本性格中,就好像有些孩子,是比其他孩子有更堅强的意志。有了意志,就會付諸行動。不論行動是好或壞,都會把自由和責任顯示出來 。
羅洛·梅指出意願包括兩部份:(1)願望;(2)決定或選擇行動。許多人很不容易經歷或表達他們的願望。[56] 要知道願望與情感是有緊密的關係;若是情感閉塞,會影響到個人不能自發願望, 因為既不能投入感情來,就不能經歷個人的心願。一旦產生了願望之時,就要面對決定或選擇行動。不少人會很清晰的知道自己願望什麽,但卻不清楚如何來決定或選擇行動。他們往往會因爲要決定而感到恐慌,會試圖完全避免整個事情的發生、或委任他人來為自己決定如何做、或甚至無可奈何的托詞環境不由自己來決定(而實際上,自己不自覺的才是左右環境發生的人)。這應對方式不乏發生在末期病者或其家庭成員身上。有些病患者不願面對現實,甚至不願談及自己的病情;有些不想作任何選擇;更有些屈服在命運之下而認命、感到沮喪、放棄盼望。
但相反地,也有些人(數目也許不多)可以在他們身上見證另一種應對方式:不論情況如何惡劣,也不能奪去自己的最後一種自由 – 就是自己還可以選擇用什麽態度來應對、和揀選自己的路,因爲選擇總是會有的。每時每刻都會提供人機會來做出決定,決定自己是否會對外在環境屈服,是否願意被强權威脅和奪走自我、放棄自由和尊嚴,成爲環境的玩物、命運的犧牲品。
基於信念為依據的盼望。我們已經了解到盼望是可以從嬰兒和育嬰者的相互信任關係而產生。嬰兒的第一個盼望是基於對育嬰者的信任,而這人也是驗證嬰兒盼望的第一人。在保羅·普魯澤Paul Pruyser的主要貢獻之中,其中一項是他將唐納德·威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的“過渡性領域”應用在宗教信仰上。[57] 威尼科特曾經注意到嬰兒往往喜歡抓住一塊毛毯、一個柔軟玩具、一個布做的娃娃、或其他一些特殊物件貼近自己的身體、尤其是嘴唇。有時嬰兒會吮著一隻手指,而其他手指仍抓住一些特殊物件。這種行爲通常會發生在嬰兒入睡之前(也就是在醒著和睡著的過渡階段中),或者在沮喪、煩躁、焦慮或抑鬱時發生。威尼科特稱這些物件為“過渡物transitional object”(又可稱為安全毯),因爲他們代表著“嬰兒和育嬰者所體驗的一切親情之片段。” 即使育嬰者不在,嬰兒也可以從這過渡物體驗到相似的親密關係。換言之,這過渡物可以替代育嬰者,令嬰兒能從獨一無二的母嬰關係過渡到直接與外在世界接觸的體驗。[58]
這“過渡物”在保羅·普魯澤的眼中,帶有神聖的光環,與宗教的起源大有關係。此外,這“過渡物”在嬰兒的眼中,也具有獨特能力、賦予嬰兒特殊的信心。[59] 不止這樣,家庭裏的其他成員也不敢輕視嬰兒的看法,在規矩上非常尊敬這“過渡物”,以防惹起嬰兒的義憤。
普魯澤並沒有說這些“過渡物”是盼望的像徵,但他暗示兩者之間是有一定的關係。他指出,嬰兒的“過渡領域”可能還未成熟到嬰兒會開始盼望。原因有二:要麽是嬰兒的“内心可能還在夢想和幻覺中而感到願望已得滿足,”要麽是嬰兒會“只著迷於外在感知世界的一成不變之定律。”[60] 所以,如果嬰兒真個能夠進入和維持成熟的“過渡領域”,那麽他們便不會再有痴心妄想(虛幻的盼望),也不會被好像改變不來的外在環境所影響(而仍然抱有盼望)。由於盼望就是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 – 不止能夠驗證願望是否可以實現,還能夠同時相信這世界還有可變的餘地 – 所以盼望正是反映著一個成熟的過渡領域。
普魯澤指出“過渡物”可以緩和嬰兒的焦慮和恐懼。威廉·邁斯納William Meissner 進一步表明,“過渡物”可以用其他標志(如游戲或音樂)或儀式(如“過渡禮儀”)來取代,促使嬰兒用盼望來替換“過渡物”,令嬰兒不再感到孤單。[61] 這令人想到詩篇中廣受歡迎的盼望形像:“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23:4 )。詩篇所採用的形像,很多都是關於過渡的經驗:例如“行過死蔭的幽谷”(詩篇23);(耶和華)“把我從禍坑裡、從淤泥中拉上來”(詩篇40); (大衛的處境)“如同毀壞歪斜的牆、將倒的壁”(詩篇62); 如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詩篇90)。正如詩人所説,我們的生命也是一樣,從一個安全點轉到另一個安全點。在這過程中,我們經歷上帝就好像詩篇121所説:“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詩121:7-8 )。
詩篇中描述的上帝顯明是一個賦予人盼望的上帝。這並非偶然,也不令人驚訝,因爲在許多詩篇裏,人的願望有三個情緒階段(即等待時的妄想、期待時的著迷、以及渴望時的焦慮)都反映著盼望。然而,這些只會令人對詩篇所帶出的盼望信念尤其印像深刻,因為盼望不止是每首詩的主調,也是詩篇整體的主題。[62]
此外,我們也不應奇怪音樂可以有效的描繪我們的生死過渡程節,打從我們目前的生活到我們的來生。啟示錄有云:“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並且我所聽見的好像彈琴的所彈的琴聲。他們在寶座前…唱歌,彷彿是新歌…”(啟14:2-3 )。因此,音樂與盼望是有獨特的關連。我們知道這點,是因爲事實上,不少民間團體和運動,在盼望共創美好將來之時,都會依靠信仰之歌和集體歌唱儀式(例如黑人民權運動所唱的“我們將會克服We shall overcome”)來支持他們盼望的信念。相反地,絕望的人往往在沉默中受苦,或是低聲呻吟,就好像單戀不成或説不出哀痛的人一樣,難以發聲。
死亡與盼望的關連
在所有存活關切中,死亡是最明顯的一個。凡人都會死,無一能倖免。這是一個可怕的事實,並且在人的心底裏,引致極度的恐慌,因為正如巴魯·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所説,一切生物都企望“自己無限期的繼續存在。”[63] 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看,人的內心有一個很大衝突: 一方面明知死亡是不能避免,而另一方面卻同時盼望能夠持續活下去。
大多數人都渴望死亡不是終結,渴望來生比目前更加完整和完美。通常我們聯想到來生,都是渴望在死後仍然能夠有機會扭轉終極的損失。我們有這渴望,但事實是否如此,要視乎我們有否持著信心來期待。對某些人來說,期待之心非常強烈。但對其他人來說,卻是相當薄弱。這強弱度會受多種因素影響,但在某種程度上,這關係到我們有沒有信心來設想我們死後的將來。
一些末期病者不想面對死亡這現實。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張先生沒有問到他病情的嚴重性。[64] 在中國文化來說,談論死亡是大忌。並且,很多中國人都相信,如果讓病者知道他們患有晚期癌症,他們可能會變得更爲沮喪、乾脆放棄活下去。有些病者會感到無奈和絕望,不再願意執行日常生活的任務,就好像納粹集中營的囚犯一樣,實實在在的躺下來等死、接受命運的安排。但反觀那些持著盼望的病者,雖是死神敲著門,但他們卻有盼望來支撐他們來繼續活著。
約翰·濟慈John Keats是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英國詩人。在他的詩“ 明亮的星,但願我能如你一樣堅定”裏,他描述星星為永恆的守望者,看守著地球上所有的事情。[65] 他指出星星是如何“凝視海水沖洗塵世的崖岸…俯瞰下界的荒原與群山, 被遮蓋在輕輕飄落的雪罩裡… (讓星光) 枕臥在我美麗的愛人之胸膛,永遠能感到它的輕輕起伏…永遠、永遠聽著她輕柔的呼吸。”就是這樣,詩人把自己投射在明亮的星身上,渴望永遠都能超越這個世界的一切。他真真盼望自己能永遠觀看到潮起潮落和雪花飄零,更能永恆的守望著愛人一晚一晚的安靜睡眠。
當濟慈寫這首詩之時,他還是一個醫學生,剛剛知道他自己患有絕症。[66] 幾個月後,他便與世長辭,享年26歲。這首詩展現了盼望的意境:面臨生命即將結束,詩人是多麽盼望著在來生,他能被提升為永恆的看守者;“雖然如今所知(所見)有限,但那時候就會完全知道(和見到)了”(林前13:12)。通過這盼望,詩人所展望的將來會顯得更真實和實在,可以緩和他的絕望,幫助他在死亡威脅之下,一天又一天的與病魔爭戰。
基於理性的盼望。真實(不是虛假)的盼望是期望目標是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這目標能否達成要視乎很多因素:視乎我們認識自己有幾多、我們的性格、特點、動機和價值觀。因此,我們需要理性思考來權衡、和選擇適合自己的行動來達成可行的盼望目標。
此外,所選擇的盼望目標是可以通過理性思考來重定方向或重新定義。身患絕症的病者往往不敢苛求病的痊愈,但會在其他問題上持著盼望,例如:自己可以活多久、會如何痛苦、身體與精神虛弱會如何嚴重、和藥物能否控制得住疼痛。如果個人損失是不可避免或不可逆轉,那麽若要持續抱有盼望,盼望的目標需要重新整頓。這可能要著眼於其他可達成的目標,並籌備資源來實現這些目標。這些都需要理性行動。最重要的,是開始逐步朝著更遠大的目標邁進。對於身患絕症的病者,這些目標也可以是短期性的,比如盼望活到聖誕節期、或盼望整理好個人財務、又或者盼望與某一家人和解、決定不計較以前的怨恨,務求自己在有生之日活得舒爽。
在這理性思考和行動的過程中,抱著盼望的人必須有一定的自控能力,否則便會感到無奈或無望。在嬰兒發展盼望期中,實則已顯示出一種早期自控能力,以防惹怒育嬰者。這需要嬰兒對育嬰者有堅定的信任。杰拉爾德·德沃金Gerald Dworkin 認爲“要有自治,就必須建立牢固的早期信任。鑒於嬰兒自從開始有自己的意志,便强烈希望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但爲著避免這任性會得罪育嬰者,嬰兒必須有自控,堅定信任育嬰者的選擇、不讓自己任性。等到成長為孩子時,活動範圍擴展了,這自控便會成爲自治。孩子往往不再寄望於育孩者,而會將盼望伸展到整個世界,期望處世的目標能夠達成。因此,孩子自幼便學會了選擇可行的路綫,下定決心向前邁進,務求改變世界為目標。這有助於幼兒超越眼前狀況而注目於未來。這鍛煉幫助孩子確認自己的身份和承擔生活壓力的責任,並且賦予孩子生命意義和凝聚力。”[67] 隨著孩子的成長,這責任會持續一生一世。正如弗蘭克爾Frankl指出,“因爲有生命,就意味著有責任來找到生命難題的正確答案,和完成生命不斷為每個人設定的任務 。”[68] 同樣地,憑著盼望,末期病者也可以學會超越眼前狀況而注目於未來、從逆境中找到生命意義和凝聚力、和完成生命不斷為每個人設定的任務。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培育盼望來幫助末期病者承擔生活壓力和在逆境中繼續活下去是唯一合理和明智的選擇。
關乎盼望的臨床研究
兩位研究學者,伊麗莎白·賴德奧特Elizabeth Rideout和莫琳·蒙泰莫羅Maureen Montemuro,使用貝克Beck的測量絕望表Hopelessness Scale 作調查工具,發現“心臟衰竭病者雖然生理上有很多限制,但那些抱有多些盼望的病者,對他們的生活有更多的投入。”[69] 他們的身體功能未必有好轉,壽命也沒有加增,但他們會更多 “對生活投入”。這樣看來,盼望似乎能賦予人生活的熱忱,但這項研究還是很難讓我們清楚知道,究竟是“對生活投入”帶來盼望,還是盼望帶來“對生活投入”。在加拿大(1994年)的另一項調查指出,對那些正在等待心臟移植的病者而言,“盼望是唯一有助於應對焦慮的因素。”[70] 兩項調查加起來,指出盼望有助於心臟衰竭的病者維持其對生活的投入,也有助於那些等待心臟移植的病者應對他們的長久等待期。[71] 盼望是可以幫我們繼續活下去,直到生命的終結。
瓊妮·厄爾克森-多田Joni Eareckson–Tada是一個因爲交通意外而四肢癱瘓近三十年的受害者。她的寫作和講章影響了無數身受痛苦和陷於苦難的人。她覺得能夠服侍他們給予她生命意義:“我發覺能夠在痛苦中越堅持得久,人生意義就越鮮明。”[72] 就是這樣, 她和無數其他人已經證明了即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人也可以有優質的生活。對他們來說,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取決於健康良好,而是取決於個人的積極生活態度。
根據多麗絲·科沃德Doris Coward的調查, 當患有艾滋病(後天性免疫缺陷綜合症)的病者願意接觸他人、與人建立關係、和抱著盼望和可行的目標來生活之時,他們會重新拾起個人的生命意義。[73] 貝特西·法伊夫Betsy Fife又發現病患者如何解讀癌症的含義,便會如何影響到他們怎樣來應對癌症。[74] 米利亞姆·卡梅隆Miriam Cameron曾經採訪了一些艾滋病患者及其愛人。她發現到不論是患有慢性疾病或絕症,大多數的病患者只要抱著信心、盼望、人生意義和目標,都可以生活得滿有尊嚴。[75] 在卡梅隆的調查裏,其中一個結論顯示出一般來説,在幫助這些病人和他們所愛的人來應付死亡的道德和存活問題上,醫療保健人員確實缺乏足夠的教牧輔關培訓來促使他們持有憐憫心和技能來應付眼前的迫切需要。[76]
況且,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出適當的緩和療護Palliative Care,可以使病患者生活得有尊嚴、也可以有尊嚴地離去。例如,瑪麗·珍·馬西Mary Jane Massie等人發現,癌症病患者不想活下去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抑鬱、絕望、無奈(失控感)、持久疼痛、缺乏家庭和社團支持、和治療癌症所產生的副作用,但卻不是癌症本身。[77] 若能適當的控制住病者的疼痛、使用抗抑鬱藥物、加强外界支持和内在心理治療來緩解他們自殺的傾向,那麽這些病者是可以繼續生活在病患中的。
在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 和邁克爾·馬赫Michael Maher的報導裏,善終療護協調員發現那些安然經歷善終的病者往往具備如下素質:有信心保持自己的控制能力;有勇氣來討論死亡的現實含意;願意探索來世的實際影響;有興趣談論宗教或靈性問題;樂意重溫過去;富有幽默感;不逃避痛苦的真相;注意個人的日常儀表;往往被愛的擁抱環繞著;和不時參與愛心行動。[78]
斯圖爾特·艾爾索普Stewart Alsop的回憶錄正好給我們提供一個令人激勵的個案研究。當他知道他患有不能動手術的致命血癌之時(急性粒細胞性白血病),艾爾索普曾經動過自殺的念頭。那時他正在醫院病房裏等候著再下一個骨髓測試。那天晚上,他有著死亡將臨的感覺。但一晚過去,他感到有一種説不出的知覺浮現出來(可能屬自我保護範疇)。雖然他沒有信仰,但他卻認為“這裏面肯定埋藏著一個隱秘。無論我們願意接受與否,在某程度上我們每個人都實在有宗教信仰…即使我在生的時日有限,我卻非常慶幸我有一個美滿的婚姻和一個相當長而充滿樂趣的生命。” [79] 此後,艾爾索普的病情有起有伏,但他卻從中學會了欣賞人生和擁抱死亡。
在另一個案例中,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討論他從閱讀克萊爾·菲利普Claire Philip的日誌所得到的領悟。菲利普是一個臨床社工。從她知道她患有癌症後,她便開始寫日記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和掙扎。在她1991年6月15日的日誌裏,她說:“我察覺到哭泣不單是浪費我自己的潛質,也只是在患病的孤獨歲月中一種無聲的掙扎… ” 她在日記最後幾頁中表明了她對死亡的接受和對生活不懈的參與。儘管她的身體日漸虛弱,加上不時發燒,她仍然“每天都花上幾小時來做一些有創造性的事情。” 甚至當她的生命消逝之時,她在最後一頁日誌裏,仍然很鮮明地説出她對生命的熱愛:
我開始閲讀一本令我輕鬆的休閑書籍,也有些寫作。剛剛今天出版的俄亥俄州臨床報告論及道德倫理與重病的處理,再加上L.C. 今天探訪我時所論及的幾個搞笑問題,已經足夠我消磨一整天了。這些都是生活的一點一滴。但讓我們每天都持續有這些吧![80]
儘管菲利普擔負著極大的身體不適和疼痛,她卻證實了人的靈性是可以不斷成長,直到生命最後一刻。科爾認為,“她的日記表明了人可以活出似乎有矛盾的諺語:你要每天都活得好像你能做百年的善事(不忘行善),也要把每天都當作是你的最後一天來生活(不忘其急切性)。”
生物學與盼望的關連
諾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1915-1990年)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是專於正面情緒對健康的影響。他著的書 動動腦筋 – 從生物學角度看盼望 深入淺出的述及他的個人經驗。他講述兩個腫瘤科醫生的對話。一個說:“你知道嗎,羅拔?我真不明白你的藥療成果比我好。我們都是用同樣藥物、同樣劑量、同樣吃藥時間表、和遵守同樣的藥療標準。然而,我的有效率只是22%,而你的卻是74%。在擴散性肺癌來説,真是聞所未聞。你是怎麼做的呢?” 羅拔回答說,“我們兩人都是使用依托泊苷Etoposide, 順氯氨铂Platinol, 長春新鹼Oncovin 和羥基脲Hydroxyurea。你叫你的組合藥物EPOH (依著藥物名稱的首要字母次序),而我卻告訴我的病人,我給他們的是HOPE (同樣藥物首要字母的逆寫, 但剛巧有盼望的含義)。當然,我告訴他們,這組合藥物只是實驗性的,也可能有很多副作用,但我所強調的是盼望。雖然藥物對這惡性癌的效用不高,但總是會有少許百分點的病人會對這藥物有良好反應。” 卡森斯說,“疾病的診斷不宜否認,但總可以嘗試挑戰它的裁決。”[81] 卡森斯的書有一個核心章節,標題是“信念轉變為有生命之物”。在這一章中,他列出一系列科學研究來支持盼望是可以帶來醫治。卡森斯在1990年去世,但在那一年就有兩篇秉承他的共同研究之期刊文章發表出來。
在第一篇文章裏,患有惡性黑色素皮膚瘤的病者被分為兩組。第一組(控制組)接受了標準的醫療程序。第二組(實驗組)除了接受標準的醫療程序外,還加上參與一個為期六週、有結構性的心理干預團。這種干預包括健康教育、解決問題、壓力管理和團隊支持。分兩個測量點來衡量結果。 六週結束後,實驗組在比對上 “表現較高生活動力,並且更多使用主動式行為來應對他們的療程。” 再六個月後的覆查表示出,兩組之間的差異變得更為明顯。這項研究的結論是:“這些結果表明,短期心理干預可以幫助惡性黑色素皮膚瘤的病患者降低心理壓力,並且提升長期有效的應對。”[82]
第二篇文章是發表在同期的刊物上,是基於以上的研究。據報導,六個星期的心理干預組有如下免疫的變化:“隨著NK細胞的抗癌跡像,大顆粒淋巴細胞與自然殺傷細胞都有顯著的增加, 並且T細胞的百分率也比前有小幅下降。”[83] 這些免疫學數據的意義在目前還未清楚。據我所知,這研究還沒有跟進。然而,這兩項研究表明了短暫的集體心理治療(重視應對技能和團隊支持)是可以減輕心理壓力、增強有效應對、和增強某些免疫量度。· – “”
關於團體干預療法的更顯著影響,有名氣的英國醫學雜誌 柳葉刀 Lancet在1989年發表了大衛·斯皮格爾David Spiegel等人的研究報告。[84] 這是研究心理–社交治療對擴散性乳腺癌病患者生存率的影響。這研究的干預療法爲期一年,病者每週都要參與團體支持組。跟進期不只是六個月,而是十年。結果發現干預組(經過心理–社交治療的病患者)比起沒有這治療的控制組有加倍的存活期(36.6個月相對18.9個月)。更重要的是,有三個女病者在這十年期結束時還活著,而且她們都是在治療組。這些都是令人震驚的結果。何況研究人員還說,“我們本來預計這療法會提高生活質素,卻料不到會影響存活量度。” 1997年 癌症 Cancer雜誌已證實了這項研究的有效性。[85] 總體來說,這些研究表明了心理–社交治療不僅能緩解心理壓力、提高應對、和增加免疫力,並且能延長壽命。
以上的研究,包括卡森斯合著的研究,並沒有特別提及盼望所起的作用,但我們不能否認盼望是團體治療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並不是一個不合理的假設。在歐文·亞隆Irvin Yalom列出的團體治療十項治療因素中,[86] 其中第一項便是“盼望的灌輸”,而最後一項是“存活的因素”,例如生存意義和目的。在此帶入亞隆並不是無因,正是因為亞隆也曾在早期與斯皮格爾共同研究過團體治療對垂死病者的影響。[87] 在斯皮格爾等人的研究中,他試圖解釋這療法是如何達到效能:“病者專注於如何利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其他病者及其家屬,從而化悲劇為意義。”
最後,1996年的報告提出,[88]“絕望是健康不良後果的一個强有力的預測因素;是獨立性的,不受抑鬱和傳統風險因素所影響。”具體來說,男性具有高度絕望的,比起具有低絕望的,高三倍可能性在六年期間死亡。如果你的健康不好,又沒有抱著盼望,你在接下來的六年中死亡的機會會比抱有盼望的高三倍。若你是健康的,但沒有抱著盼望,死亡機會會比起抱有盼望的高六倍。從字面上看,沒有盼望,生命就會早些結束。
總括來説,文獻中有豐富的數據來證明盼望對身患絕症的病者有潛在的好處,可以應用,並且在道德倫理問題上,培育他們的盼望是合理的。我們將會在下一章討論如何在中國傳統文化下幫助這些病者培育盼望來應對他們患有的絕症。
第五章尾注
[1] In this dissertation, fostering hope means promotion of growth or development of hope. It is used here to include both the inspiration and nurturing of hope.
[2] James Greek, cited in Spirituality, Health, and Wholeness: An Introductory Guide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ed. Siroj Sorajjakool and Henry Lamberton (New York: Haworth Press, 2004), 110.
[3] Charles A. Corr, Clyde Nabe and Donna Corr, Death and Dying, Life and Living, 4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3), 140.
[4] Elizabeth Kübler-Ross, On Death and Dy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99.
[5] Corr, Nabe and Corr, Death and Dying, Life and Living, 139.
[6] Paul T. P. Wong, “The Wisdom of Positive Acceptance,” President’s Colum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ersonal Meaning (2004), http://www.meaning.ca (accessed May 14, 2008).
[7]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75.
[8] Lao-tzu, Tao Te Ching, Book 1, chap. 8, 64.
[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Daoism,”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582972/Daoism (accessed May 14, 2008).
[10] Interview #23, Appendix.
[11] Merle H. Mishel, “The Theory of Uncertainty in Illness,” Image 20, no. 4 (1988): 229.
[12] Ibid., 231.
[13] Interview #10, Appendix.
[14] Avery D. Weisman, On Dying and Denying: A Psychiatric Study of Terminality (New York: Behavioral Publications, 1972), 67-74.
[15] Richard S. Lazarus, “Positive Denial: The Case for Not Facing Reality,” interviewed by Daniel Goleman in Psychology Today 48 (November 1979): 44.
[16] Richard S. Lazarus, “Stress and Coping as Factors in Health and Illness,” i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ancer, ed. Jerome Cohen et al (New York: Raven Press, 1982), 175.
[17] Inge B. Corless, “Hospice and Hope: An Incompatible Duo?”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9 (May/June 1992): 10.
[18] Yalom,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8.
[19] James E. Loder, The Transforming Moment: Understanding Convictional Experience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1), 79-91.
[20] Andrew D. Lester,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chap. 5, 80.
[21] Loder, Transforming Moment, 167-73.
[22]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115.
[23] Debra Parker-Oliver, “Redefining Hope for the Terminally Ill,”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19, no. 2 (2002): 115.
[24] Deborah R Mitchell, “The ‘Good’ Death: Three Promises to Make at the Bedside,” Geriatrics 52, no. 8 (1997): 591-92.
[25] Parker-Oliver, “Redefining Hope for the Terminally Ill,” 115.
[26] Elizabeth Kübler-Ross, “Therapy with the Terminally Ill,” Death: Current Perspectives, ed. Edwin S. Shneidman, 2nd ed. (Palo Alto, CA: Mayfield Publishing, 1980), 201.
[27] Parker-Oliver, “Redefining Hope for the Terminally Ill,” 115.
[28] Cathleen Fanslow-Brunjes, Patricia E. Schneider, and Lee H. Kimmel, “Hope: Offering Comfort and Support for Dying Patients,” Nursing 27, no. 3 (1997): 54-57.
[29] John MacMurray, Persons in Rel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61), 150.
[30]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trans. Walter Kaufma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0-1), 62.
[31] Story of Ms. Zeng from Interview #12, Appendix. Also in Chapter 2.
[32] Sigmund Freud, “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20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9), 119-23.
[33] Yalom,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353.
[34] Ibid., 23 on transcendental self.
[35] Ben Mijuskovic, Loneliness in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Assen, Netherlands: Van
Gorcum, 1979), 99-100.
[36] Walter Brueggemann, Hope within History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7), 84.
[37] Elaine Scarry,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4.
[38] Stanley Hauerwas, Naming the Silences: God, Medicine, and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 1990), 146.
[39] Ibid.
[40] Story of Mr. Zhang from Interview #8, Appendix. Also in Chapter 3.
[41] Anderson, Spiritual Care-giving as Secular Sacrament, 58.
[42] Pruyser, Between Belief and Unbelief, 187.
[43] Ibid.
[44] Lee E. Snook, “Death and Hope – An Essay in Process Theology,” Dialog 15, no. 2 (Spring 1976): 127.
[45] Hauerwas, Naming the Silences 146.
[46] Robert Beavers and Florence Kaslow, “Anatomy of Hope,”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7, no. 2 (April 1981): 125.
[47] Carrigan, “Where Has Hope Gone?” 39.
[48] William F. Lynch, Images of Hope: Imagination as Healer of the Hopeless (Baltimore: Helicon, 1965), 19.
[49] Gabriel Marcel, “Despair and the Object of Hope,” The Sources of Hope, trans. Joan Notwotny, ed. Ross Fitzgerald (Rushcutters Bay, Australia; Elmsford, NY: Pergamon Press, 1979), 47.
[50] Lynch, Images of Hope, 136-37.
[51] Ibid., 219.
[52] Jean-Paul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trans.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56), 631.
[53] Rollo May, Freedom and Destin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93-96.
[54] Sartre, Being and Nothingness, 631.
[55] Viktor Frankl, The Unconscious G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5), 58.
[56] Rollo May, Love and Will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218.
[57] Donald W. Winnicott,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 in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229-42.
[58] Pruyser,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110-11.
[59] Pruyser, Between Belief and Unbelief, 198-213.
[60] Ibid., 114.
[61] William W. Meissner,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9.
[62] Donald Capps, Biblical Approaches to Pastoral Counseling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1), 206-8.
[63] Baruch Spinoza, cited in 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by Miguel de Unamuno, trans. J. E. Crawford Flitch (New York: Cosimo Classics, 2005), 22.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for Baruch Spinoza not provided.
[64] Mr. Zhang’s story from Interview #8, Appendix.
[65] John Keats, “Last Sonnet,”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s, ed. H. Buxton Form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486.
[66] Capps, Agents of Hope, 65, as he quoted the work of Aileen Ward in John Keats: The Making of a Poet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3), 297-300.
[67] Gerald Dwork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
[68]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85.
[69] Elizabeth Rideout and Maureen Montemuro, “Hope, Morale and Adapt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1 (1986): 429-38.
[70] Alexandra M. Hirth and Miriam J. Stewart, “Hope and Social Support as Coping Resources for Adults Waiting for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6, no. 3 (1994): 31-48.
[71] Interview #14, Appendix.
[72] Joni E. Tada, When Is It Right to Die? Suicide, Euthanasia, Suffering, Merc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85.
[73] Doris D. Coward, “Meaning and Purpose in the Lives of Persons with AIDS,” Public Health Nursing 11 (1994): 331-36.
[74] Betsy L. Fife,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in Illness,”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40 (1995): 1021-28.
[75] Miriam E. Cameron, “Technical Problems Involving Death,” AIDS Patient Care: A Journal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8 (October 1994): 269-78.
[76] Paul T. P. Wong and Catherine Stiller, “Living with Dignity and Palliative Care,” in End of Life Issu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ed. Brian de Vries (New York: Springer, 1999), 77-94.
[77] Mary Jane Massie et al.,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9 (1994): 325-340.
[78] Douglas C. Smith and Michael F. Maher, “Achieving a Healthy Death: The Dying Person’s Attitudinal Contributions,” Hospice Journal 9 (1993): 21-32.
[79] Stewart Alsop, Stay of Execution: A Sort of Memoir (New York: J. B. Lippincott, 1973), 150.
[80] Thomas R. Cole, “Gaining and Losing a Friend I Never Knew: Reading Claire Philip’s Journal and Poetr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9, no. 4 (Winter 1995): 329-34.
[81] Cousins, Head First: The Biology of Hope, 34, 79.
[82] Fawzy I. Fawzy, Norman Cousins, et al., “A Structured Psychiatric Intervention for Cancer Patients. I. Changes over Time in Methods of Coping and Affective Disturbanc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7, no. 8 (1990): 720-25.
[83] Ibid., 729-35.
[84] David Spiegel et al., “The Effect of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Lancet 2 (Oct. 14, 1989): 888-91.
[85] Manuela M. Kogon, David Spiegel et al., “Effects of Medical and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 on the Survival of Women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rcinoma,” Cancer 80, no. 2 (July 15, 1997): 225-30.
[86] Irvin D. Yal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4th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3-4.
[87] David Spiegel and Irvin D. Yalom, “A Support Group for Dying Pati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28, no. 2 (1978): 233-45.
[88] Susan A Everson-Rose, George A Kaplan, Johanna Salonen and Debbie E. Goldberg, “Hopelessness and Risk of Mortality and Incidence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Cancer,”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8, no.2 (March 1996):113-21. ·
第六章
在身患絕症的病者中培育盼望
總則
從我們對盼望四維的認識,我們可以幫助身患絕症的病者,用不同方式來培育他們對存活的盼望:一、幫助他們創建或尋找到意義來渴望活下去; 二、通過關愛和支持來建立信任,從而啓發和培育他們的盼望; 三、通過靈性的提升來助長他們盼望能力; 四、通過目標的制定和達成來强化他們的盼望。
幫助他們創建或尋找到生活意義
個人敘事personal narrative。每個人都有個別故事來傾訴。敘事的意思是故事:是人詮釋世界某方面被歷史文化和個人性格所塑造出來的一種解釋。[1] 在另一種含義上,敘事是我們基於經驗他人和自我的構建。在這些敘事中,我們創造我們自己的含義。[2] 薩特Sartre引述過,“人類始終都是講故事之人; 我們在生活上都被我們的故事和其他人的故事包圍著。通過這些故事,我們可以看到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一切; 我們的生活就好像我們嘗試敘述一個故事那樣。” [3] 給別人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是我們唯一有效的途徑來表達自我。因此,如果我們想試圖了解一個人的生活狀況和感受,我們必須聽完這個人的整個故事,包括其全時空變化和關係,這樣才能把這人的意思和盼望聯結起來。[4]
在經歷世界的過程中,我們所經歷的每一個新感覺、新刺激、和新的人際互動事件都會在我們的内心裏照著某些有意義的原則(例如有指導性的隱喻)構成一個自己的故事。[5] 故事裏的事件如何變得有意義,完全是憑著故事結構如何將事件的敘述連接與未來故事的發展。斯蒂芬·克賴茨Stephen Crites是第一個提出人類的生命是依著敘事形式活出來的。[6] 人不但只講述故事或用故事來說明自己的生活,更藉著故事(不論是講述的或潛意識壓抑的故事)來構造個人身份。 [7]
所謂“核心敘事core narrative”就是故事的主題、故事的重要構思,是由無數小故事合組而成。人若憑著這樣的構思來更新思維,或者可以扭轉逆境、使之富有意義。要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核心敘事”,幫助自己來構思如何應對環境的轉變,包括了解和評估苦難、生命和死亡。宗教信仰是 “核心敘事”其中一個例子:人往往是藉著禱告和默想來了解生命和死亡。因此,我們的經驗各有其獨特性,將會構成為故事形式,逐漸建立起我們的自我和身份;而這些從體驗演變出來的故事,將會發展為我們個人的“核心敘事”。
核心敘事不單只是個人生命的數據,也是建立起自我的決定因素。要知道我們斷不能憑著個人資料或數據來真正認識對方。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過,當別人問起“她是誰who?”之時,我們不能用“什麽what”來描述她,因爲描述她的身體特點(如高矮肥瘦)、職業或所屬機構等等都不能有效地回答這個問題。原因是:答案疏忽了她的獨特性 。[8] 如果真要描述她是誰,我們需要説及她完整的個人故事。要真正認識一個人,我們需要聆聽對方的個人故事和認識對方的“核心敘事”(即故事主題)。這核心敘事會表達出對方的價值觀、宗旨、特點和獨特經驗,好使我們能更加體驗到對方的獨特性。當然,我們的體驗也會產生我們自己的個人故事。
這叙事理論,正好與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 的發展理論一致,提供依據來支持懷舊心理療法Reminiscence Psychotherapy。[9] 在他的發展理論中,埃里克森描述人的發展會臨到最後一個階段,就是藉著重溫過去來維持自我的完整,但亦可能因維持不來而感到無望。[10] 完整的自我就是帶著信心來接受人世的滄桑。這對盼望是至關重要的。埃里克森有一句貼切短語,就是“ 你是什麽人,就視乎你過去怎樣生活。”[11] 絕症病患者很多時都藉著重溫過去的成就而自豪,所以即使面對苦難,也能找到一刻喘息的機會。懷舊也有其他收益,包括與人和解、接受善終,並且會因已盡己所能而得到滿足。[12] 關顧者的聆聽、支持和鼓勵大大促進病患者的自我表達,有助於病患者恢復個人意義、身份和存活角色。照片、紀念品、音樂等物都可以用來幫助病患者追憶兒時事件和慶典等。這等干預不宜過份,應當視乎病患者的提示,也應當尊重保密。[13]
羅拔·巴特勒Robert Butler ,通過個人生命評估evaluative reminiscence,取得了一些成功來幫助抑鬱症病患者重新整合尚未解決的衝突,例如與人和解和接受死亡問題;並且成功的灌輸予病患者成就感和自豪感。[14] 老年病學家彼得·科爾曼Peter Coleman還發現老年人在重溫過去之時,所説及的故事内容和風格都會帶給他們快感,因爲他們覺得這信息的回憶informative reminiscence 帶有教學功能,可以傳承給下一代他們多年的經驗。這信息回憶法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在老年時面臨嚴重角色失落的人。[15] 通過重申他們的身份、獨特性、自我價值和成就感,信息回憶可以幫助病者應對多種的損失和維護他們的自尊。科爾曼還報告說,“當人生的滄桑威脅著個人存活之時,回憶過去更能提供多些安慰。”[16] 詢問病者過去的生活意義,有助於讓他們表達自己的感受,從而確認目前情況下的含義。
重構新盼望。要在目前重構新的盼望和意義,有一種方式就是取材於過去的盼望目標、成就、甚至挫折,來尋找未來新的機會和可能性。框架是用來制定我們如何看目前情況; 它塑造了我們的現實。脫出框架就是改變我們的思維結構和看法,重新評估我們的生活經驗,轉化累贅為强項。比如,我不止一次聽到病者說,疾病反使他們與家人多些親近,可見他們並沒有被目前環境困在絕望中,反而脫出來重構盼望在家庭的和睦和合一上。同樣地,病者也不會在思維框架中被誤導,以爲自己患的絕症是可以治愈。他們可以將新的盼望目標建在心裏安寧、身體舒適上。隨著盼望和意義的改變,個人在應對類似情況時,也會有很不同的感受、想法、態度和行為。
這重構新盼望的說法是起源於神經系統與語言程序設計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17] 和家庭治療family therapy理論。[18] 重新調整思維的意思是重塑新的概念,改變個人、家庭或團體一貫認為的模式,目的是改造自己對生活狀況的觀念。在調整思維時,一旦對框架中任何部份生出疑點,便免不了考慮用另一種新方式來了解事情的發生,再很難回到本來持有的觀點,[19] 並會開始聯想到一個順境的將來。
重新組織思維就好如將記憶當作是一個房間,將房間的家具和裝飾重新安排會有助於改變對過去的認識。重組還可以鼓勵人對現狀發展新的認知,對未來重塑自己的想法。當關顧者發現病患者的現狀與盼望有抵觸之時,不妨試圖轉個思維框架,從負面概念轉爲正面,這會有助病患者展望一個充滿盼望的未來。
但是,如果事與願違又如何?有些事真的很難積極面對,也很難説到有什麽好;即如先前説及的李先生, 他因爲用盡積蓄而買不起止痛藥來減輕疼痛,試問還有什麽好的方法去安慰他?[20] 當我問及他為什麼他沒有自尋死路之時,他與我分享唯有他才能知道的求生慾。不錯,有些處境是如斯的惡劣,實在是很難積極的去面對,但無論如何,作爲關顧者,最重要的任務是需要仍然傳講一些積極信息給病患者聼,並且自己也要努力去相信。安德魯·萊斯特Andrew Lester建議關顧者“敦促那些面臨絕望的病患者不要氣餒。即使他們不相信環境會有什麽好轉,但告訴他們,不妨邁出第一步來臨時相信。那怕只是相信一天!與他們達成協議,或要求他們來逗你開心!如果他們認爲這是虛偽作爲而反對,同意他們的看法; 建議他們就做一天(或更長時間)‘僞君子’吧。” [21] 如果他們這樣做會在感情或行為上帶出任何積極的變化,便鼓勵他們繼續如此行,就當作他們的願望是弄假成真吧!
關顧者可以幫助病患者回憶在過去他們是如何解決問題,甚至省察他們是如何處理眼前的困難。關顧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促進病患者重組眼前所發生的事情。這會有利於盼望的增長和積極的改變。
敘述未來故事。另一種方法來培育盼望是邀請被關顧者辨認出或編造出有關未來的具體故事。固然有些事是無法説出來,但用想像力來編造一個故事是可以帶出其特性。敘事理論已證明了故事有能力影響人去構造他們的世界觀。[22] 至於如何使用未來故事,關顧者大可以邀請被關顧的想像一個充滿盼望的未來、刻意追求積極的價值觀和體驗快樂的人生。例如在開始時,你可以選擇問這些問題:[23]
如果你的生活被拍成電影,有一個圓滿的結局,告訴我這部電影的結局會是什麼樣子。
如果你幾年後給我寫信,信上充滿了關於你生活的好消息,這封信將會說什麼?
如果我明年讀報紙,報導一些奇妙的事發生在你身上,那會是什麼呢?
接下來可以請他們添上細節 – 人物、地點、場景和事物 – 直到他們敘述了一個相當明確和具體的未來故事,可以幫助他們選擇一些有創意的行為,作爲他們對未來充滿盼望的基礎。
理查德·加德納Richard Gardner是一個兒童精神科醫生。在他的電視節目“編造一個故事”中,[24] 他邀請孩子們敘述他們所編造的故事,而他也告知孩子們他自己也會參與。這相互敘事方法可以帮助人編造更有盼望的未來故事。他教孩子們編故事要有頭部、中部、和尾部。故事講完後,加德納要求他們講述故事有什麽意思。之後,他會選擇故事的某一部份來重構,用同樣的人物和情節來提供另一參照來使結局不同。關顧者也可以參考加德納的做法,引導成年的被關顧者編造關於未來的故事,並且留意故事的那一部份是可以更改,化累贅為强項、化失望為成長、化危機為機遇,從而導致一個積極的或有盼望的結局。
意像導引。意像導引是利用人的想像力和投射智力來幫助他人找到或重構他們自己的未來故事。[25] 實行之時,引導對方先閉上眼,採取一個平靜的冥想態度。到鬆弛下來時,便讓對方揀選在未來可以發生的各類情況,而另一方面,也讓對方在心底裏同時形成一幅他們自己選擇的圖畫。接下來,引領他們通過各種意像或幻想來暗示如何為未來創造新的可能性,並且與他們一起探索跟未來有關的新理念。[26] 不少人會發覺這種鍛煉實在有利於幫助自己投射在未來的努力,令到他們的未來故事反影出他們自己選擇對未來的看法。約翰·濟慈John Keats寫的詩“明亮的星,但願我能如你一樣的堅定”便是將願望投射在星星的一種意像,是濟慈日復日在絕望中與病魔和死亡對抗時所依賴的盼望。[27]
當絕症病患者成功的找到或重構新的意義之時,他們生命的混亂和脆弱便會重獲控制。當苦痛和死亡被重構為救贖和永生之時,盼望便在遙遠的水平綫上升起來。
通過關愛和支持來建立信任
帕克-奧利弗Parker–Oliver認為,保持主要的人際關係是可以提供機會來確立意義和目的。經過了解與評估意義和目的之後,病患者可能有新的目標和盼望,其一便是與人和解。[28] 艾拉·比奧克Ira Byock建議,有五個説法可以用來處理破裂的關係,避免絕望。這包括:“原諒我”,“我原諒你”,“謝謝你”,“我愛你”和“再見”。[29] 有機會來探索重建或增強相互信任的關係,是人生中不可少的意義。但相反來説,如果關係已經破裂到不能有互信,而只是單方面的追求,那麽寧可終止這關係,也勝過繼續下去,因爲所帶來的只會是絕望而非盼望。
關顧者與絕症病患者的關係是培育盼望成功與否的關鍵。盼望可以在兩者互相信任和關愛的情況下發芽,再通過滿有同感心的聆聽和反思、尊重和接受、陪伴和安慰、和堅守關顧的承諾,盼望才會成長確立。新建立或重新找到的友誼可以打開未來,產生滿有活力的盼望。同時,若有一個關注自己、可以互相分享悲與喜的朋友,盼望就會有一個好媒介。
亨利·努文Henri J. M. Nouwen 有一名句,是描述什麽才是關懷, “在我們絕望或困惑中,與我們保持沉默(無聲勝有聲)的那個朋友;在我們悲痛和哀傷時,與我們作伴的那個朋友;那個可以容忍什麽都不需知道、容忍不知我們的病能否得到醫治的朋友;那個願意與我們一同面對無奈和現實的朋友;那個朋友,就是關懷我們的朋友。” [30]
通過靈性的提升來助長盼望的能力
評估個人靈性又一次提供機會來探索一下盼望的可能性。靈性是通過虔誠的閱讀、祈禱、冥想、音樂歌曲、歷史傳統(重要性是紀念過去)和儀式(重要性是釋放精神上負擔與罪孽)來提供超然性的盼望。許多宗教信仰的信徒都抱持幸福與和平的盼望,而盼望有來世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應許。這來世可以採取不同的形式。即使沒有宗教教條、教義或信條作指標,一個垂死病人通常都會在這特殊生命過渡期進入屬靈之旅,渴求生命意義。在臨終病患者中,最常見的討論話題已被證實為屬靈問題。[31] 事實上,這討論話題不止聯係著活人與垂死之人,也聯係著垂死之人與過了世之人。在最後的日子裏,垂死之人探求和平與和睦確實會帶來許多盼望的機會。此外,絕症病患者也會發現,當他們為別人服務之時,他們的付出會帶來意義,大大的提升他們的靈性。
試想奇蹟。 另一種方式來提升靈性是通過想像力。有史以來,人類已經不斷幻想著揮動魔杖、喊出魔法、靠著運氣或奇蹟來改變自己的生活。有鑒於此,史蒂夫·德沙澤Steve de Shazer等人便用這現像來治療。他們引用所謂“奇蹟問題”來激發人對未來的意像:[32]“假設你明天早上醒來,你的一切問題都離奇消失。你會怎樣知道?你的家人或朋友又怎會知道?你的生活究竟有什麼不同?”
本·弗曼Ben Furman 和塔帕尼·阿霍拉Tapani Ahola請一些來接受輔導的人想像一下,在未來的光景,他們的一切難題都全然消失了。[33] 在輔導開始時,輔導者先問“你的生活可好?”再問“可否告訴我你現在的問題?”然後,輔導者鼓勵這些客戶談論一下這個未來假設,並邀請他們試圖解釋,他們的一切難題有什麽可能會在未來奇蹟般的消失。再問他們,“你可以想像到你的未來生活會是這樣嗎?”“你覺得你的未來生活有什麼顯著變化?”通常來説,要達成奇蹟的發生,被輔導的人可以描述出他們自己或他人的有關變化。他們的描述就隱藏著促進變化的種子。這描述可以用來引導干預療法,並且可以在修訂過後,塑造未來故事。弗曼和阿霍拉指出,想像一個奇蹟的發生可以令人擺脫未來的絕望意境。至於那些考慮自殺的人,輔導者會請他們想像一下,死後來到天堂之門,見到天使,得知他們在地上的所有難題都已得到緩解,並且知道有機會可以重囘地上。[34] 試問問他們,“既然你的難題已完全解決,你又有機會從頭開始,那麽你的生活將會是怎樣過?”有了這種意境,即使有意圖自殺的人,都可以開始構建一個目前可以行得通的未來。
通過目標的制定和達成來强化盼望
培育盼望,固然可以通過鼓勵有需要的人去設想一個新的未來,也可以通過幫助他們制定具體目標來帶他們走向那個未來。制定目標是重要,但有時也很艱鉅,因為許多人的生活都似乎凍結在過去的一成不變裏,很少或根本沒有自由來考慮改變。教牧關顧者可以用這開場白:“你認爲你的生活在一個月後(或是三、六、九個月後)會有什麽改變?要現實一點,包括你的家人、財務等等都算在内。請非常具體而簡潔的列出改變。” 實在有很好理由來鼓勵對方制定一個清晰目標去達成。理查德·韋爾斯Richard Wells說過,“專注於解決生活上單一的問題,成功的機會會比同時處理太多問題高得多。”[35] 將焦點縮小到單一目標上,可以增加積極變化的可能性。
設定目標和達成目標將會促進絕症病患者積極參與日常生活,並且在有生之日,能完成未竟之事。關顧者可以幫助達成這重要的目標。雖然病患者不適宜遠行,但總可以想些有創意的方法來將目的地帶到床前。也許垂死病者很想寫本書,但又明知不能,那麽安排視頻或錄音可以將病者的思想、人生經驗和知識錄下來,作為代替品。或者這些目標看來是小,也似乎只是短期,但他們可以培育盼望,令病患者重新參與日常生活。此外,即使少少的錄音或視頻也是給所愛的人一個寶貴的遺贈,促使後人尋找自己的生命意義。
文化的考慮
關顧者究竟應如何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進行培育盼望和設置一個臺階來促進“美好的生活”?重要的是,病患者所持有的信仰和價值觀應得到尊重,因此,要使他們内心得到滿足,關顧者要樹立對生命、死亡和自然健康的尊重,認識到生和死都是大自然的一部份,並且考慮到他們的傳統文化遺產、具體歷史和社會背景,來幫助所關心的人找到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在中國,家庭居首位。許多絕症病患者在家庭關係的互愛互助中,找到他們苦難的意義。他們經常關注醫療費用對親人的沉重經濟負擔,怪不得他們大部份的未竟之事都是以家庭的需要為中心。因此,在決定醫療策略之時,關顧者必須包括病者家人在内。在這方面,中國第一宗安樂死的記載更是不言而喻了。1986年6月23日,夏素文,59歲,女性,因肝硬化被送往陝西省漢中市醫院治療感染。即使初步治療令到病情好轉,但幾天後(6月27日)病情開始惡化,她不停地哭說,“真是太辛苦了。我不想活下去。”之後,她其中一個兒子王明成,得知他母親的病情已臨“絕望”,便在6月28日要求主治醫師蒲連升給他母親打針,好讓她無痛而終。蒲醫師最初拒絕,但經過王明成苦苦哀求幾次後,蒲醫師被說服了,在6月28日 上午9時吩咐實習護士注射100毫升的藥物給病者夏素文。之前她的兒子王明成正式簽了一封信,指出“家人要求安樂死”。在蒲醫師下班之前,他囑咐夜班醫生,如果夏素文還沒死,再給她進一步的注射。在凌晨3時,夏素文再接受第二劑藥物(75毫升氯丙嗪chlorpromazine,又稱冬眠靈wintermin) 。她在1986年 6月29日早上5時身亡。夏素文的其他孩子,鑒於他們在這決策沒有被諮詢,起訴蒲醫師和王明成殺死自己的母親。兩名被告最終被判“無罪”。這個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在 2003年2月,王明成自己患上末期胃癌,他要求醫師協助他安樂死,但被拒絕。同年8月過身。[36]
在這臨床個案調查報告中,我們也看到一個孫女,如何因爲愛心,持著樂觀和抱著盼望的態度,來培育祖父的盼望。[37] 通過她的孝心、堅定不移的忠誠和關愛、責任感、勤奮和願意單獨承擔護理責任,她成功的將盼望傳遞給她的祖父,幫助他超越苦難、内心感到安寧和滿足。在這樣一個充滿關愛的環境下,“盼望的種子就已被撒下來了。”[38] 當大家靈裏相交之時,盼望就可以得到啟發,或從一個人身上移植到另一人身上。另一比較間接的方式,有可能是通過“滲透式”過程來培育盼望。儘管如此,關顧者應留意所關顧的人有什麽是他們心裏想實現的目標,從而幫助他們實現。
在中國,談論死亡和絕症往往是禁忌,會被視為干擾人的內心平安與和諧,從而引致“死亡的恐懼”。另一個禁忌是傳壞消息給絕症病患者。即使兩者都沒有充份支持證據,[39] 中國人的普遍做法仍然是不願對患有晚期疾病的親人説出痛苦的真相,恐怕真相會剝奪了病者的盼望。因此,關顧者要注意,除非病者和家人已準備好接受嚴峻的現實,否則最明智的處理還是不要自動提供任何未經查詢的信息,但關顧者需要警惕,留意所關顧的人有無處事冷漠或開始有絕望的徵像。這些表現都可能是病者已經知道真相而放棄盼望。[40]
雖然未竟之事往往會牽涉到盼望與人重新和解,但爲著面子,即使在垂死的病人床前,雙方都可能達成不了和解。奉勸關顧病者和家人的員工牢記這點。在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集體主義文化,“面子”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世界大多數其他地區也被重視。這“面子” 最初是出現在1917年錢伯斯雜誌Chambers’s Journal裏:“一有麻煩,當地的土著平民便走爲上着,好得回去向當局報告,保存‘面子’。‘向當局報告’就是他們的‘面子’吧!” [41] “愛面子” 就是意味著做一些事來避免羞辱或尷尬, 或作出一些舉動來保著名聲不受損害。“面子”在這種情況下所指的是尊嚴、聲譽、和在別人心目中的地位。對中國人來説,“面子”是非常重要的。
筆者在訪問中所遇到的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農民或“城市貧民”。他們缺乏良好教育或全時間就業。他們的家庭觀念很重,所以他們相信祖先會保護他們、祝福他們。只要他們燒紙錢、供奉食物給祖先,祖先在九泉之下也會回報他們。因此在中國,拜祖先和偶像都是很普遍的。一些信徒視基督教的上帝為“洋鬼子”。有什麽不幸之事發生,都會歸咎於這外來“邪魔”。或者我們太容易視他們為迷信之人,但我們不妨自問,“我們有什麽資格對他們下判斷?又有什麽能確定我們所信的宗教是比他們的更真呢?”他們不都是盡力抓著些微的盼望來應對人世的滄桑吧!因此,關顧者須多認識多元文化的複雜性,用憐憫心、同感心和開放的態度來關懷、照顧有不同需要的人。
醫師的角色
除了家庭中的關顧者,醫師也有許多機會來幫助絕症病患者培育盼望。德博拉·米切爾Deborah Mitchell提議醫師對臨終病者和其家屬做出三項承諾。[42] 首先,保證病患者不會被抛棄。向他們承諾他們不必獨自一人離世。這保證給與圍繞病者的人意義,也給病者持續與他人維持關係意義。第二個醫師的承諾是不會用特別手段來延長絕症病患者的壽命。這確認了人類互動和人情味的重要性,從而取代了維持生命的機器與技術。内裏的含義是表示重視質多過量。第三個醫師的承諾是保證他們不會被忘記,為他們所過的生活提供了意義,並允許他們在餘下的時候裏塑造這些囘憶來繼續保持有目的之生活。
其實,關懷團隊裏任何團員都可以做出這些承諾。米切爾提議醫師來做,是因為醫師可能會“具有更多的可信度、合法性和有效性。”[43] 讓病者相信他們的自我意識仍在成長中而還未消失,畢竟會令病人反思自己是誰,和考慮到他人會如何記念自己。這三個承諾開始了新的過程來幫助垂死病者找到新的意義和新的盼望。
善終關懷服務Hospice Program的角色
雖然據我所知,中國大陸還沒有任何有組織性的善終關懷服務,但我仍需介紹一下這服務的重要作用。有了善終關懷服務,醫師可以轉介一些絕症病患者 到這服務。從生病到垂死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期,從後者被標定為“善終關懷病人hospice patient ”後, 便開始由這服務來處理以後戲劇性的過渡。[44] 在這程序中,善終關懷提供病者道具、設置管理、和護理群體來促進角色的轉換。雖然不是只有“善終關懷病人”可以在盼望上重新定義,但“這身份標記無疑帶來新的期望,和創立一個參照群體來協助病者在盼望上重新定義。”善終關懷安排病者的周圍都是認同和重視病者的新身份之人,保護病者避過那些只看到情況是無意義與無望的人。善終關懷所扮演的角色是讓病者家人有機會來參與關顧,給與他們新的盼望。[45] 至於其他緩和醫療從業者所面臨的挑戰也是一樣,並且提供一個參照群體來支持病者,幫助他們在這過渡期產生意義。有了這些支持,病者便可以開始重新定義他們的盼望。
這善終關懷服務是非常重要,不僅是對病患者而言,還對其家人和衛生保健人員也是如此重要。從病者最初進入程序之時,垂死的狀況與從前的經驗形成了直接的對比,但病者卻能夠重設新的意義和盼望。這就要歸功於善終關懷服務了。服務人員雖然同情病患者的狀況,但卻不會視此為不幸,反視之為構造盼望的好契機。病者以前信賴高科技、不斷出入醫務所、盼望得到醫治,但在現時卻會轉爲盼望身體得舒適、家人有和好、和個人有選擇參與決策。除了盼望焦點轉移, 病者和家人所扮演的角色也有顯著的改變:以前懼怕公開談論死亡,但在接受了死亡是不可避免之後,自會覺得坦然、舒暢一點。有一點關顧者須留意。雖然病者轉移了盼望焦點,並不等於病者不希望病得到痊愈。因此,仍然需要鼓勵病者帶著盼望來祈禱痊愈的奇蹟會發生。奇蹟是可以發生的。祈禱和願望並沒有錯。然而,好應促進病者在生活上繼續創建新的意義, 而不是依靠痊愈的奇蹟來生活。
教牧輔關者的角色
最後一點,但並非是不重要,是有關教牧輔關者的重要角色。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唐納德·卡普斯Donald Capps在他的書 盼望之中介者Agents of Hope: A Pastoral Psychology裏有一個極好的説明。[46] 首先,他引用了約翰·班揚John Bunyan的經典著作天路歷程 中的一段短篇敘述:
在整個旅程中,陪伴著英雄克裡斯蒂安Christian(寓意基督徒)的朋友名字是“盼望Hopeful”。當克裡斯蒂安進入約旦河,到達應許之地時,也即是到達旅途的最後階段時,他感到自己正在下沉。他對著朋友盼望大聲呼叫:“我正下沉深水中啦!浪已過了頭,水浸過我啦!” 盼望回答說:“我的兄弟,不要沮喪;我已感覺到河底了!河底很好呀!” 但是克裡斯蒂安仍然呼喊著盼望,因爲他確信自己會死在河中,永遠也進不了城門。當他沉得越來越深時,盼望只能讓他的頭浮在水面上。當盼望安慰他說:“兄弟,我看到城門了,還看到有人正站在那裏歡迎我們呢!”克裡斯蒂安卻回答說,他們等待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盼望。但盼望堅持地告訴克裡斯蒂安,他的困難和苦惱並不是上帝拋棄他的跡像。盼望鼓勵克裡斯蒂安Christian不要氣餒;即使在這困境,耶穌基督Jesus Christ也會使他完好無損。聽到這話,克裡斯蒂安大聲喊說他可以再見到他的主!可以聽見主對他說:“我將與你一同渡過江河,不讓水淹沒你。” 就在那時,克裡斯蒂安的脚踏到地了;水變淺了,而危機也結束了。兩個人到達彼岸,遇見兩個滿身發光的使者, 是被派來事奉那些即將被歡迎進入拯救之家的人。[47]
然後卡普斯繼續說:
沒有盼望,克裡斯蒂安肯定會淹死。沒有盼望的鼓勵,他會屈服在絕望中。如此説來,盼望正是一個牧者的形像,是那個能擔保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人﹔令那些正在沉溺的人感覺到他們的腳能夠踏實地面﹔令那些面臨生命崩潰的人知道,基督甚至會不懈的努力使他們完整無損。盼望不能使克裡斯蒂安(寓意基督徒)完整—因爲只有基督才能做到這點—而是幫助正沉溺的人把頭浮在水面上,使他能看見基督,聽到基督的應許。教牧輔關者固有的本份就是作為盼望的中介者。[48]
我同意卡普斯的説法。作為教牧輔關者,我們是盼望的中介人: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應該如此行,而是因為我們想如此行﹔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需要,而是因為別人的需要﹔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議程,而是因為他人的願望。如果盼望是認知到可以在未來達成所渴望的目標 ,[49] 那麼在充滿關愛的氣氛中,培育盼望是可以鼓舞病入膏肓的病者。當大家靈裏相交之時,盼望可以從一個滿有盼望的人(關顧者)轉移到病者身上,正如盼望是在親子相互信任中發展出來一樣。這樣人人都會受益。
作為教牧輔關者,我們是神的大使。神不止與我們同在,還在我們前面呼喚、邀請、甚至挑戰我們進入未來。正如於爾根·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所說:“上帝是與我們同行和呼召我們向前走的那一位。甚至可以說,上帝是在下一個灣角處等著我們…即使我們走入死胡同,上帝也不斷為我們打開令人驚訝的新通道。”[50] 安德鲁·萊斯特Andrew Lester也說,“永生的上帝不會從後面向我們招手,把我們困在歷史中,而是藉著應許和盼望把我們拉向未來。”[51] 在我們脆弱的當下,必須超越眼前的必需品或過去的責任,意識到我們是有自由—即使是有限—來實現我們應該是什麼樣的人,從而展望未來。我們承擔著塑造未來的責任。作為教牧輔關者,我們有機會讓我們的末期病者進入更深一層的盼望。也許最好的方式來表達這一點是讓他們看到我們是以互動方式來關顧他們。與他們分享的盼望很有可能給他們帶來自己的盼望。就讓他們從我們的眼中看到盼望吧。
有盼望就有生命 [52]
在第二章開頭所敘述的李先生故事,表明了中國末期病人面臨苦難時的困境:是生存還是死亡。他們的故事真令人心碎。我對他們的問題懷疑是否有答案。我相信答案就在他們自己的內心,在條件成熟之時會被發現或創構。我相信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環境中,可能會發現不同的意義。
在我的文獻調查中,我對維克托·弗蘭克爾Viktor Frankl所提出的“力求尋找意義”印象甚深,這實在有助於那些無奈又無力來改變自己境況的人,幫助他們繼續活下去。儘管他所寫的是關於納粹集中營囚犯,但他的建議在病入膏肓中的病者身上也很有道理。根據他的觀點,我建議即使在最黑暗的境況下,盼望可以給絕症病患者提供一個積極的態度來繼續生活。盼望會讓人在未來投射出積極的意義,合乎現在的環境。我個人認為,當絕症病患者真的考慮自殺時,盼望可以阻止他們採取這類行動。
回顧文獻所寫的,可以認識到盼望不僅是寄托在意義上,也可以寄托在關愛和支持、信念和信任、和目標設定與實現。盼望的四維度 — 經驗、關係、靈性和理性 — 似乎都特別適合處理絕症病患者中常見的四項存活關切:生活無意義meaninglessness、無支持(群體)isolation、無依據(如信仰或信念)groundlessness和無奈 powerless to fend off death 。盼望也被稱為人類生命發展周期中的第一大美德(或大强項)。如果真是力上加力的話,盼望也可說是人類所有其他力量的基礎。
作為美景的展望,盼望也會根據不同的社會文化而戴上不同顏色的眼鏡。中西方對意義和盼望的不同觀點揭露出我們中國傳統裏一些隱藏著的議程、假設和預設,但同時也充實了彼此的傳統。這種思想交流和有機會用不同的方法來培育盼望很可能有助於絕症病患者應對其苦難。
當我說“有盼望,就有生命”之時,我指的是生命整體(靈、身、心、社):有靈命的形體和自我與別人的關係。有証據顯示盼望可以給病入膏肓的臨終病患者提供積極的生活態度,使他們能夠繼續從事生活、提高生活質量、減輕心理上的痛苦、和更有效地應對苦難。作爲一項新領域,“盼望生物學”進一步表明,在抱有盼望的情況下,某些免疫學措施可以得到改進,甚至壽命也可以延長。但是筆者應當謹慎地指出,本文所提及的建議仍然是一個未經驗証的假設,還需更多的研究來証實其有效性。
除此之外,人類故事將會留在我們心中。盼望的故事就是有關危險和承諾、悲劇和美好、折磨和善良的故事。讓我們考慮一下那個垂死的祖父是在一個什麽樣的境況。[53] 他接受了自己的生命即將結束的事實。世界似乎是如斯殘酷,前途又是如斯黯淡。疼痛變得難以忍受。錢就快用完了。除了他的孫女,他斷定家裡已沒有其他人會關心他。他自問:“與病魔爭戰,明知會輸,還打什麽仗?究竟我的生命還有什麽意義和目的?”
然而,當他陷入低谷,在痛苦中掙扎之時,他的眼睛打開了新的可能性。對呀,他生活中畢竟有美善的祝福:是他孫女的愛和忠誠,對他的關顧毫不動搖,使他在痛苦中找到意義。經過這次折磨,祖父和孫女的關係比以前更加親密,並且雙方都盼望對方能夠滿足自己的需要。祖父需要被愛和關顧,而孫女需要被祖父接納,對她沒有性別偏見。
當祖父考慮自殺之時,他提醒自己不要拋棄自己的家庭,玷污了家族的姓氏。他對來世的信念使他放棄了自殺的念頭,因爲他懼怕要解釋自殺的原由。相反地,他選擇了一個積極的立場:他展望未來,並採取相應的行動,開始尋找失散多年的兄弟。與其說是為了和解,倒不如說是為了滿足他的好奇心,盼望看看他的家族血統和姓氏能否留傳下去。他渴望活著來看到孫兒懷孕和嬰孩誕生。血統留傳和家族遺產是他最關心的事情,也帶給他生存的理由和意義。
這是一個美麗的故事。結局很好。祖父終於摒除了對孫女的偏見,衷心感謝孫女的孝順和忠誠。他們找到了彼此。心靈的傷治愈了。和解的盼望也實現了。她得到接受。他也得到滿足,就此便平靜的死去。
這故事不是就此結束。三年後,她因先天性視網膜疾病而失明。她想自殺。“ 不可,”她告訴自己,“自殺只會給全家帶來恥辱。”那是她祖父去世前說的話。甚至當她的視覺轉暗,就好像黑夜一般,她還是看到一線盼望和一個感恩機會。她在耶穌基督Jesus Christ裏找到安寧。“儘管我失明了,我還是慶幸自己能夠過上相當好的生活,並且作為一個針灸師,我贏得尊重…我不再羨慕那些身體健康的人,因爲一個健康的人未必有一顆健康的心。”顯然,心靈的事情比身體的痛苦對她更為重要。
在這個故事中,孫女也是盼望的中介人。她幫助她的祖父構建新的生活意義,並從遙不可及的盼望(病得到痊愈)重新定義為可以實現的盼望目標。她幫助他欣賞生活、減輕他對死亡的恐懼。她和醫師合作,承諾為他建立舒適的環境 ,用關愛和支持圍繞著他,幫助他盤點關係,與他分享自己的信仰,並為他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培育他的盼望。作為一名家庭裏的關顧者,她在身、心、社、靈四方面培育她祖父的盼望:通過堅定不移的承諾(保持祖父的身體舒適);愛心的辛勞;支持鼓勵與和解;及靈裏得醫治,她都認真的、勤奮的和負責的來幫助祖父塑造盼望。由於她自己抱有盼望,以及她激勵和培育祖父的盼望,她的祖父並沒有放棄,仍然繼續從事生活。沒有人確實知道這盼望是否延長了他的生命,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他找到了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找到了生活的理由。維克多·理查茲Victor Richards的話在這裡聽起來很真實:[54]“臨終病者所接受的關顧,不論是在量或質來說,都會有助於他的盼望增長,以及有力的幫助他對未來持著開放的態度。”作為回報,孫女的盼望也實現了。他們兩人都放棄了自殺的念頭。盼望取代了絕望和冷漠,取而代之的是信心和關愛。不錯,有盼望,就有生命。當人學會了如何在生活上抱著盼望來面對苦難和痛苦之時,“安樂死”(醫師協助病者自殺)就不是什麼大問題了。
第六章尾注
[1] Walter R. Fisher, “Narration as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1 (1984): 1-22.
[2]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4-5.
[3] This quote comes from Andrew D. Lester,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27.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for Jean-Paul Sartre not provided.
[4] Andrew D. Lester,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30.
[5] Theodore R. Sarbin, “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in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ed. Theodore R. Sarbin (New York: Praeger, 1986), 8.
[6] Stephen D. Crites, “Narrative Quality of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39 (Sept. 1971): 291.
[7] Ibid.
[8]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58), 181.
[9] Dorothy Wholihan, “The Value of Reminiscence in Hospice Care,”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9 (1992): 33.
[10] Erik H.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9), 98.
[11] E. Mansell Pattison, “The Experience of Dy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1 (1967): 32-43.
[12] Arthur W. McMahon and Paul J. Hudick, “Reminiscing: Adaptational Significance in the Aged,”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0 (1964): 292-98.
[13] Dorothy Wholihan, “The Value of Reminiscence in Hospice Care,”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md Palliative Care 9 (1992): 33-35.
[14] Robert N. Butler, “The Life Review: An Interpretation of Reminiscence in the Aged,” Psychiatry 26 (1963): 65-76.
[15] P.G. Coleman, “Measuring Reminiscence Characteristics from Conversation as Adaptive Features of Old Age,” Int. J.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5 (1974): 281-294.
[16] Ibid., 283.
[17] Richard Bandler, John Grinder,Steve Andreas and Connirae Andreas, ed. Reframing: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 (Moab, Utah: Real People Press, 1982), 5-8.
[18] For a summary, see Donald Capps, Reframing: A New Method in Pastoral Car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0), 11.
[19] Andrew Lester, “Helping Parishioners Envision the Future,” Strategies for Brief Pastoral Counseling, ed.Howard W. Stone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01), 50-52.
[20] Story of Mr. Li from Interview #6, Appendix.
[21] Andrew D. Lester, “Helping Parishioners Envision the Future,” in Strategies for Brief Pastoral Counseling, ed.Howard W. Stone, 52.
[22] Andrew D. Lester,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29.
[23] Ibid., 52 on “Helping Parishioners Envision the Future”.
[24] Richard A. Gardner, Psychotherapy with Children of Divorce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6), 58-59.
[25] Joseph E. Shorr, Gail E. Sobel et al., eds. Imagery: Its Many Dimension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Plenum, 1980), 253-66.
[26] The cared-for are invited to record whatever imagery experiences come to them, whether fleeting images or extended dramatic scenarios, whether seeming foolishness or with obvious associations, whether sleep dreams or waking imagery. Have these recorded in their journals without judgment and without censorship. This is one example taken from Ira Progoff’s book The Dynamics of Hope: Perspectives of Process in Anxiety and Creativity, Imagery and Dreams (New York: Dialogue House Library, 1985), 230.
[27] John Keats, “Sonnet.”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s, ed. H. Buxton Form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486.
[28] Deborah Parker-Oliv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Dying Role: The Hospice Drama,” Omega –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0, no. 4 (2000): 19-38.
[29] Ira Byock, “Steve’s Story,” in On Our Own Terms: Moyers on Dying Discussion Guide (New York: Thirteen/WNET, 2000), 8.
[30] Henri J. M. Nouwen, Out of Solitude: Three Meditations on the Christian Life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74), 34.
[31] Dona J. Reese and Dean R. Brown, “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 Care in Hospice: Differences between Nursing, Social Work, and Clergy,” Hospice Journal 12, no. 1 (1997): 29-41.
[32] Steve de Shazer, Putting Differences to Work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113.
[33] Ben Furman and Tapani Ahola, Solution Talk: Hosting Therapeutic Convers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91-106.
[34] Ibid., 102-103.
[35] Richard Wells, Planned Short-Term Trea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10.
[36] Yan Qin, “Schiavo’s Fate Fires Debate on Euthanasia,” China Daily (Mar.23, 2005), http://www. 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03/23/content_427546.htm (accessible May 14, 2008).
[37] Interview #7, Appendix.
[38] Paul Tillich, “The Right to Hope: A Sermon,” Christian Century 107, no 33 (Nov. 14, 1990): 1064-67.
[39] Tse, Chun-yan, Alice Chong, and Janet Sui-yee Fok, “Breaking Bad News: A Chinese Perspective,” Palliative Medicine 17 (2003): 339-43.
[40] Donald Capps, Agents of Hope: A Pastoral Psychology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95), 99. Shame is described as the third enemy of hopefulness.
[41] James Rogers, The Dictionary of Clich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5).
[42] Deborah R. Mitchell, “The “Good” Death: Three Promises to Make at the Bedside,” Geriatrics 2, no. 8 (1997): 591-92.
[43] Ibid., 592.
[44] Deborah Parker-Oliv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Dying Role: The Hospice Drama,” Omega –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0, no. 4 (2000): 19-38.
[45] Ibid.
[46] Donald Capps, Agents of Hope: A Pastoral Psychology, 3-4.
[47] John Bunyan, The Pilgrim’s Progres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57), 151-52.
[48] Donald Capps, Agents of Hope: A Pastoral Psychology, 3-4.
[49] Ibid.,4.
[50] Jürgen Moltmann, Foreword to The Origins of the Theology of Hope by M. Douglas Meek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4), x.
[51] Andrew D. Lester, “Helping Parishioners Envision the Future,” in Strategies for Brief Pastoral Counseling, ed.Howard W. Stone, 58.
[52] This phrase is, to my knowledge, first used by Robert L. Richardson, “Where There is Hope, There is Life: Toward a Biology of Hope,” Journal of Pastoral Care 54, no. 1 (Spring 2000): 75-83.
[53] Interview #7, Appendix.
[54] Victor Richards, “Death and Cancer,” Death: Current Perspectives, ed. Edwin S. Shneidman (Palo Alto, CA: Mayfield Publishing, 1980), 479.
附錄APPENDIX: 訪談資料Interview Data
| Patient Number 病者 號碼 | Patient Age 病者 年齡 | Gender性別 | Terminally ill patient 絕症病患者 | Family Member家中身份 | Spiritual Counselor屬靈輔導者 | Faith 信仰 |
| 1 | 50+ | Male男 | No否 | Husband丈夫 | None否 | |
| 2 | 50+ | Male男 | No否 | Son兒子 | Christian基督徒 | |
| 3 | 30+ | Female女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4 | 60+ | Female女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5 | 30+ | Female女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6 | 40+ | Male男 | Yes是 | None否 | ||
| 7 | 30+ | Female女 | No否 | Daughter女兒 | Christian基督徒 | |
| 8 | 70+ | Male男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9 | 50+ | Female女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10 | 60+ | Female女 | Yes是 | None否 | ||
| 11 | 70+ | Female女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12 | 30+ | Female女 | Yes是 | None否 | ||
| 13 | 90+ | Male男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14 | 18+ | Male男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15 | 70+ | Male男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16 | 40+ | Female女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17 | 30+ | Female女 | No否 | Daughter女兒 | Christian基督徒 | |
| 18 | 40+ | Female女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19 | 40+ | Female女 | Yes是 | Christian基督徒 | ||
| 20 | 20+ | Female女 | No否 | Daughter女兒 | Christian基督徒 | |
| 21 | 40+ | Male男 | No否 | Yes是 | Taoist 道家 | |
| 22 | 40+ | Female女 | No否 | Yes是 | Buddhist佛教徒 | |
| 23 | 50+ | Male男 | No否 | Yes是 | Islamic伊斯蘭教徒 |
在下面的敘述中,爲著保密,所有名稱純屬虛構:
- 周先生(50多歲)是於2007年12月4日上午9時在沙溪接受採訪,為時60分鐘。
- 他的妻子(年齡50多歲)患有晚期結腸癌,在當天凌晨早上5時去世
- 周太患有惡心、嘔吐、持續疼痛、長期臥床,以及厭食和吐血。臨終前4-5個月受苦不堪(之前,沒有告知她病情實況)
- 丈夫周先生4-5個月前自殺不遂,原因是他無法面對太太的病(他10多年前曾有過幻覺)
- 他們的一些鄰居和親戚給他們不少未徵求的建議﹔故此周先生覺得他們極為“討厭”
- 因為她的病,周太在生時變得越來越與人隔絕
- 問到周太在生時,她有什麽生命意義,周先生答道,她的三個女兒都是她的命根、是她抓著生命的全部原因
- 因為周太的病,這家人的彼此關係變得越來越親密
- 周太自己覺得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 4-5個月前,打從知道壞消息之前,周太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
- 除了家人的支持,教會也給予她很大的支持
- 從那時起,她就不再害怕死亡(對她丈夫來說也如此)
- 她已經接受了死亡,並盡了最大的努力活下去,直到看到她的孫女出生
- 在孫女出生後17小時,她便離世了
摘要:一個50多歲的丈夫,在2007年12月4日喪妻。妻子患了結腸癌,臥床不起、食欲不振、惡心、吐血,疼痛難止。在探訪周先生之前6小時,周太剛剛離世。丈夫難於接受妻子的重病,在4-5個月前曾自殺不遂。以下是周先生的一些引文:
“我的妻子一直都不知道她病情的真相,直到最後幾個月。之前,我們爲著不讓她知道,實在極其難忍。”
“有不少舊相識給與我們很多不請自來的提議,更增加了我們的負擔。為什麼他們不能離我們遠一點?”
“因爲我妻子的病,我從未感到如此無奈,尤其是不知道她的痛苦會持續多久…對我來說,看到她受苦,比我自己受苦還要難挨。”
“我和我的妻子都非常愛我們的女兒。家中有和諧和安全,值得我們夫妻感到自豪。”
“三個女兒的愛給與我們存活的意義。他們對母親的愛大大鼓舞了我妻子。”
“女兒們非常想念母親。這使她熱愛生命。她也非常想念她們。如果可能的話,只要她還活著,她就想花盡時間和他們一起。”
“我真想念她。她是我的至愛。誰會想失去?”
“我盡我所能來照顧她。”
“即使她已準備死,但仍有許多痛苦和恐懼她渴望擺脫。”
“我一直陪著她來渡過這苦難的考驗。我不想讓她感到孤單。”
“有時我默默地和她坐在一起。她是知道我會與她同行。”
“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自從她信靠了耶穌基督Jesus Christ,她有了永生的確據,也有盼望來激勵她繼續活下去。”
“教會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我不知道我的樂觀態度對她有什麽好,但在最後的日子裏,她抓著盼望,幫助她緩解她的苦難。”
“我妻子希望看到我們第一個孫女的出生,否則她就不想死。這盼望給她很大的鼓舞呀,舒緩了她的痛苦,也讓她在餘下的時間積極從事生活。”
“我的妻子在我們的孫女出生十七小時後便平靜地離去。這真個是‘好死’呀!”(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回答說:“她現在是在主懷平靜地安息了。”
“我一生只為生存奮鬥。也許我活著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找到勞碌一生、凡事盡責的意義吧!”
“我已經盡力來養家活兒,為太太和孩子們謀求更好的生活。”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只盼望減輕自己的負擔,也減輕別人的負擔!”
- 鄭先生是於2007年12月4日在廣東沙溪接受採訪,為時45分鐘
- 他的父親鄭老先生患有肺癌,視綫又差,幾乎看不到我們,所以很少參與我們的採訪
- 父親因肺癌走動起來呼吸急促﹔每兩天要注射一次麻醉劑來緩解疼痛﹔還患有厭食症(沒有食慾)
- 家中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Yu jia)照顧他
- 還有一個住在廣西的小女兒,打算在爸爸去世後接母親到廣西與她同住
- 父親容易生氣﹔曾與廣西的大兒子大吵一頓
- 家人說父親非常強硬,在六七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歷過不少艱辛
- 醫生已放棄了父親康復的機會,但父親還不知道(媽媽知道)
- 由於錢銀緊,鄭先生沒有帶父親去醫院求醫,因而感到內疚
- 自從接受了耶穌基督之後,父親感覺到有新生。教會又非常支持
- 父親三年前幾乎死於肺癌,所以父親很慶幸自己還活著
摘要:50多歲的兒子接受採訪。他的父親一直都因患有末期肺癌而很痛苦,並且擔心兒子支付不來醫療費用。孩子之間偶有不和。以下是兒子鄭先生的一些引文:
“醫生告訴我,父親的癌症已經是末期了。我媽媽和我決定不告訴他,是因為我們想保持他的盼望。告訴他又有什麼意義?不管怎樣,他自己已做好最壞的打算,把所有未竟之事都處理妥當。”
“我因為沒有帶爸爸去醫院求助而感到內疚。醫生曾經告訴我們,他們已無能爲力了(尤其是當家裏錢銀緊張時)。”
“親戚們都不明白,責怪我爲什麽不帶爸爸去醫院求止痛藥。”
“但爸爸也理解,他是關心這些開支。”
“我讓他多說話。我只是聽,有時壓抑不住我的淚水。我想我永遠無法真正感受到他所感受的,但至少他知道我在乎。”
“他告訴我一些他引以為榮的事情,也有一些他後悔的事情。我幫他整理好這些。這顯然給與他一些安慰。”
“只要有可能,我仍然幫他持守日常生活。這有助於緩解他的不適和苦難。”
“我告訴他,活著比死亡更需要勇氣。我鼓勵他帶著尊嚴來完成這場比賽。他正是這樣做。”
“他的勇氣令我們作孩子的感到驕傲。”。
“父親三年前幾乎死於肺癌。過後,他是一個新造的人。生活對他來說更有特殊意義。”
“他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決定他是生是死。似乎他的信念重新燃起他的生活鬥志。”
“他感謝上帝賜給他生命。他意識到生命應該好好珍惜。”
“爸爸很感謝家人和教會的支持。”
“我和爸爸都知道不管環境是多麼艱苦,上帝都會好好照顧我們。我們相信凡事都會為愛主的人效力。”
“奇蹟可以發生,但沒有信仰,奇蹟永遠不會發生。”
“苦難可以變爲祝福。這苦難使我們的家庭再一次團聚起來。我在廣西的妹妹正準備讓媽媽和她住在一起。”
“爸爸現在意識到,只要他還活著,他的生命就必須有目的而活。”
- 杜女士是在2007年 12月4日在沙溪接受採訪,爲時40分鐘。
- 38 歲單身(已離婚)婦人和她的女兒(10歲)與她的68歲重病母親住在一起
- 杜女士患有咽喉癌,接受過手術和術後放射治療。當時因爲放療,她不得不放棄懷孕
- 她的叔叔很迷信(操練風水), 指責她信奉基督教(拜“外國”神)所以才得癌症
- 她對自己的病應對合宜、樂觀接受,這是因爲她的性格堅毅,有包容(寬恕那個“庸 醫”),有堅强的勇氣和信仰,並且相信上帝會與她同行
- 儘管她自己的身體不好,她也盡力照顧她患病的母親
- 她感到內疚,因爲沒有好好照顧她死於肝癌的父親,所以這次她決定好好照顧她生病的母親
- 她爲著自己有足夠的醫療保險而感恩不已
- 她接受了痛苦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 她相信苦難一樣可以發生在基督徒與非基督徒身上。在她來説,苦難加強了她的信仰
摘要:一個30多歲的單身女性、一個10歲女孩的母親,因爲患有蔓延性的咽喉癌,需要手術和術後放射治療。家中還有一個80 多歲患有長期虛弱症的老媽要照顧。以下是一些她的引文:
“爲了放療,我不得不打掉我肚裏的第二胎。”
“雖然我哥哥和妹妹沒有為久病的媽媽做了什麼,但我覺得照顧她是我的責任。以前我的父親死於肝衰竭時,我無力幫助。現在有能力了,所以我要幫助我的媽媽。”
“我覺得媽媽有永生的盼望是很重要的。我曾與她分享聖經和上帝的應許。我一直在爲她祈禱,盼望她能信耶穌基督,找到信、望、愛。我們曾一起爲著病得痊愈、内心平安和身體舒適等等祈禱,並唱讚美詩。在絕境中,信心和盼望都一直支持著我們。”
“照顧我媽媽令我更親近上帝。”
“我學會堅忍,因為我知道上帝會照顧我們。”
“現在我心有平安。我的主、我的上帝給我力量、與我同行。”
- 杜老太,即杜女士的母親。在2007年12月4日於沙溪接受採訪,為時40分鐘。
- 68歲老太;因膽囊和膽管手術併發症導致膀胱瘺;她看起來很累
- 她覺得自己被朋友和家人(她的兒子和她的另一個女兒)丟棄
- 曾一度試圖自殺,但女兒勸阻及時,給予她大量的支持和鼓勵
- 家庭糾紛困擾著她。孩子們答應照顧她,但程度不等,只有忠實的女兒杜女士持續的照顧她,而另一個兒子和女兒根本不在乎
- 她非常感謝她的女兒杜女士
- 在她看來,女兒關顧她,實在是一個基督徒的好見證
摘要:60多歲寡婦,即第3位受訪者杜女士的母親,患有無法動手術的術後併發症,導致持續性尿失禁和舊病復發、與危及生命的感染。以下是一些她的引文:
“ 我的尿臭令我在人面前很尷尬。” “我真想死。”
“我不想再見來訪者了。”
“我的族人不能接受我女兒的(基督教)信仰。他們把我的病歸咎於她。”
“我女兒告訴我,如果我現在放棄,別人肯定會說我的病是我自己做錯事的結果。”
“我願意盡我所能活下去,也願意接受苦難是不可避免的。”
“上帝幫助我女兒活在癌症中,我也相信上帝會照顧我。”
“我知道上帝會與我同行。我不再感到被丟棄了。”
- 梁女士, 於2007年12月4日在沙溪接受採訪,為時40分鐘。
- 梁女士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家庭主婦;有兩個女兒—15歲和7歲
- 6個月前被診斷為患有咽喉癌,已有擴散;接受了35次放療;現正等待化療
- 3-4年前已接受耶穌基督
- 願意接受苦難的來臨
- 初時她否認擔心,但當談到她的大女兒需要手術之時,她卻完全崩潰了,因為她們沒有錢繼續求醫,這使她非常沮喪。
- 對她來說,她女兒的未來意味著她自己的一切
- 丈夫有出手幫忙,包括做縫紉和家務;哥哥和姐姐也幫助車出車入 ; 教會也有幫助
- 至於生命和死亡對她有什麽意義,她拒絕作答。在我看來,撫養兩個女兒對她來說是意義深長
- 她也不太想談論死亡
摘要:一個30多歲的家庭主婦、兩個女孩的母親,有了6個月的咽喉蔓延癌,經過放療後已無多餘錢來支付她15歲女兒“胸部下陷”的矯正手術費用了。 梁女士曾考慮過結束自己的生命。她在採訪中淚流滿面。(我坐在她旁邊,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只能遞衛生紙給她,讓她喘口氣才繼續接受訪問)以下是一些她的引文:
“我寧願自己死也要讓我的女兒活下去。”
“每當我想到我女兒的未來,我就感到無能為力。實在有太多未知之數 !”
“我丈夫在我生病時,挺身而出來幫助我。他做家務,甚至縫紉!”
“我的兄弟姐妹也幫助出入交通。”
“我可能盼望太高,但我盼望看到我的兩個女兒長大成人,能夠獨立生活。”
- 李先生, 於2007年12月在外海接受採訪,為時30分鐘。
- 年齡:40有多
- 2004年患結腸癌;經切除;2005年癌症復發;再次切除
- 2006年手術併發症:結腸造口脫垂
- 2007年10月(訪問前兩個月),他的劇烈咳嗽導致嚴重的下背痛,使他完全無法活動, 甚至需要人幫助他翻身
- 非常苦惱沒有錢來尋求進一步的化療或醫治他的背痛。他負擔不起醫生推薦的骨骼掃描
- 至於生命的意義?他是為了女兒和年幼的兒子而活著。兒子已被科技學院(大約相當於13年級)錄取,並且决心接受進一步的高等教育培訓
- 我們(也就是說,包括介紹我給他的聯絡人)鼓勵他堅持不懈(不要放棄),要為他的兒子樹立一個好榜樣
摘要:40多歲男性、農民,在探訪前的3-4年中 ,患有復發性結腸癌,臥床不起,還有嚴重的腰痛。這疼痛是從强烈咳嗽引起,已有8周歷史。他被送往醫院急診室,在那裡準備進行骨骼掃描,但由於他負擔不起掃描費用,醫生要他離開醫院(談到這件事時,他的聲音提不起來,不能再繼續了)。我問他妻子究竟發生什麼事呀?:妻子答:“醫院拒絕我丈夫入院。儘管我跪在主治醫生面前,懇求他同情我們。你知道他說什麼話嗎?‘對不起,沒有錢,就沒有同情心。’那是什麼樣的醫生?” (此時,丈夫恢復説話)
“為了孩子,我想活下去。我不想看到他們生活在這個冷酷無情的社會中而沒有父親。” “如果我放棄一切,殺死自己,我給孩子們樹立什麼榜樣?”
(當我向這個家庭道別時,我的心情很沉重。我聯絡了一個朋友,是一個物理治療師,看看他能否免費幫助,為這個不幸家庭做些什麼。我的朋友來了,給這個家庭一些建議。當我在2008年秋天再回來的時候,李先生已經與世長辭了)
- 羅女士, 是於2007年12月在江門接受採訪,為時60分鐘。
- 30多歲盲女,在廣東北部農村長大,連續先兩代(她的爺爺和爸爸)都是在貧窮學校做教師的
- 在初中一之後便在農場工作
- 她經常患結腸炎,身體不好
- 她母親是地主(當時共產黨的敵人);她父親在遠離家鄉的都市裏當老師
- 羅女士回憶到她16歲時的經歷:那時,她的79歲爺爺中了風18個月,身體癱瘓。在他生命的最後6-7個月裏,孫女是唯一照顧他的人
- 她的父母都無法分擔家裏的工作負荷,只有一個叔叔和一個姑姑住在附近,只幫了少少時間
- 爺爺生活得艱難,試圖爬起來,但又不能;大多數時候失禁
- 他在失禁時,需要孫女爲他換片;他認爲有損他的尊嚴,這是他最難接受的
- 他脾氣暴躁,不時責駡她不按時給他熱水
- 有一次他懇求她給他老鼠藥,因為他不想再活下去了。她沒有這樣做。他最終改變了念頭,認為自殺會給家庭帶來耻辱。這也幫助了羅女士,因爲她也曾想過自殺
- 她覺得爺爺不喜歡她,是因為她不是他所期望的孫子,但她仍然愛他
- 他在臨終前向她道謝,這使她覺得一切所做的都是值得
- 問到他的生命意義,羅女士說,他認爲做好事和誠實待人都是非常重要;同樣重要的是通過血脈來傳遞家族姓氏
- 在他最後的日子裏,他希望找到他失散多年的兄弟,看看他是否有一個兒子可以傳宗接代
- 對羅女士來說,19歲時她的視力開始惡化,逼使她停止在店裏工作,轉為替姐姐看顧孩子
- 儘管經過治療,她在20歲出頭就失明了
- 她在2000年後,從讀經得知上帝是滿有慈愛和公義的神,所以不久之後就成為基督徒,並在2001年受洗
- 有一次她差點死在車禍中;她相信一定是上帝救了她一命
摘要:30多歲女性、從業盲人按摩和穴位按壓 。憶起她16歲時是70多歲祖父的唯一關顧者。祖父因中風而癱瘓。她自己的父親已經離開村子去城裡教書;她的母親不願與她的祖父有任何關係。以下是一些她的引文:
“我爺爺非常暴躁,很難照顧,不過他是個好人。他一生為我們的家庭辛勤工作。他因為不能照顧自己而感到沮喪。”
“我非常愛爺爺。我關心他,因為他是我爺爺。當其他人都放棄他時,我照顧了他6個月。”
“在這幾個月裏,他的膀胱和大腸失控,是我為他清洗乾淨。他覺得這很丟人。”
“在他絕望時,他叫我給他老鼠藥。雖然我能夠感受到他的絕望,但我無法答應他的要求。”
“他最終改變了主意。他覺得如果他放棄自己,他會給他的祖先帶來耻辱。”
“他意識到,即使在來世,他也要為自己的世俗行為負責。”
“我很難取悅他。我希望他能對我好一點。”
“他希望有一個自己的孫子來傳宗接代。”
“他渴望與失去的哥哥聯係,看看他是否有兒子繼承姓氏。如果有,他的内疚會大大減輕。爺爺死時,並沒有實現他的盼望。”
“我爺爺去世三年後,我被診斷為先天性眼病患,會使我失明。我不得不放棄一份待遇優厚的工作,轉為我的姐姐做保姆。”
“當我完全失明時,我很想結束一切。就在那時,我爺爺的話提醒我,自殺只會帶給整個家族耻辱。我聽從了他的話。”
“儘管失明,我還是很感激自己能够過上像樣的生活。作為按摩師和穴位按摩師爲我贏得別人的尊敬,因爲我可以對人有幫助。”
“現在,我不再羡慕那些身體健康的人了,因爲一個‘健康’的人並不一定有一顆健康的心。”
8.張先生,2007年12月與他的妻子愛姨在新會會城接受了採訪,為時60分鐘。
- 張先生72歲;離過婚一次,現在再婚
- 在以前的婚姻中,生有3個男孩、 1個女孩
- 愛姨本人比張先生小好幾歲,也是個離過婚之人,和前夫生了一個兒子(現時22歲)和前夫同住
- 張先生長期吸烟,患有末期肺癌,肺部積水,心力衰歇,呼吸急促,食欲不振;夜間睡眠不佳,經常失眠
- 當問及生命意義之時,他說他相信上帝掌管著他的生命。在他第一次婚姻中,他自己的孩子把他趕出家門時,他考慮過自殺,但他對上帝的信仰令他放棄了這念頭。當愛姨急需伴侶之時,上帝賜給他一個好像她這樣的好伴侶
- 他一生珍惜個人自由和控制權。有一次他感到很沮喪,愛姨載他騎摩托車,令他再次心情轉好
- 他承認他愛她勝過愛自己的家庭,包括他的孩子。孩子和他自己的兄弟一樣,在他最需要的時候,拒絕幫助他。即使考慮幫助他之前,也要他遵行許多條件
- 張先生對上帝沒有怨恨。相反地,他感謝上帝提供足够資助來讓他能夠支付醫療費用
- 他為自己太過良善而後悔,他覺得以前願意為兒子做任何事,反而寵壞了他們
- 他擔心自己去世後,愛姨不知會如何養活自己
摘要:70歲男性患晚期肺癌,食慾減退,消瘦不少,呼吸急促。他的四個孩子和前妻把他從家裡趕出來,是因為他拒絕遵守他們的規條。他的40多歲老朋友愛姨收留了他、照顧他。他感激她的同情和關心。以下是一些他的引文:
“當我的家人在我需要的時候把我趕出家門,我感到很難過。愛姨收留了我。如果不是因爲她,我早就自殺了。她是我活著的理由。”
“她過去常開摩托車,帶我去郊遊。我又重新再感到自由了。”
“我信任她。她對我很忠誠。她沒有隱瞞我的病情。”
“儘管疼痛得很,我還盼望保持相當的機敏,盡可能多些和她一起享受美好的時光。”
“上帝總是給我最好的。我覺得最好的還在後頭—我稱之為天家。”
- 歐女士,於2007年12月在新會會城接受採訪,爲時35分鐘。
- 50多歲女性;已婚
- 有一個剛從五邑大學畢業的兒子,已在新會會城找到一份離家不遠的工作
- 歐女士在4至5年前被診斷為淋巴瘤病患者,並接受化療和放療
- 後來,她的病復發,腹部和腿部積聚很多水腫;更有頻繁的咳嗽,但疼痛比較少
- 癌症的折磨使她更接近上帝
- 5年前她接受化療時,遇到一位基督教院牧。她經常到醫院來探望她。儘管當時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很嚴重,但這位院牧並沒有戴口罩來探她。這種無私的愛使她皈依基督教信仰
- 從此以後,儘管苦難重重,她的信仰帶給她不少喜樂和感恩。再者,她丈夫黃先生和她兒子也給她很大支持,是她經歷苦難中不可缺少的人
- 她接受了死亡,並且已做好了充份的準備
- 她為他人禱告,從而得到滿足
摘要:50多歲女性,在過去一年中,遭受到晚期淋巴瘤擴散到腹部的折磨。儘管進行了積極的化療和放療,她的腹部仍然積水腫脹,令她呼吸困難。自從五年前她在醫院接受治療時體驗到一位院牧的見證後,她就成了一名基督徒。以下是她的一些引語:
“我的苦難帶領我到耶穌基督面前。”
“當院牧來探我之時,正是非典時期,醫院裏每個人都戴著口罩,但她沒有戴。她無私的愛影響我很大。”
“我的信念令我堅持下去。不管旅途是多麼艱辛,耶穌基督都會和我同在。”
“我的丈夫和兒子非常支持我。”
“我盼望看到我兒子畢業。他結果做到了。此外,我很高興他找到一份離家不遠的工作。多好啊!”
- 周女士,於2007年12月在江門接受採訪,為時45分鐘。
- 61歲,丈夫60歲;有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
- 大女兒是余女士。一年多前余女士在住院時接受了洗禮。是她帶我們去她家中看望她的母親周女士
- 周女士已咳嗽了一年有多。沒有疼痛,但呼吸急促
- 她還不知已患上晚期肺癌(轉移性和惡性細胞)。
- 做女兒的很擔心。她不明白她母親為什麼會患上肺癌。她母親不吸烟,也沒有肺癌的家族史。女兒很想知道藥物(Iressin)對她母親的影響
- 做媽媽的也為自己健康煩惱(淚流滿面)、擔心未來
- 她盼望女兒早日結婚
- 當我們到達他們所住的房子時,丈夫正在樓下打麻將
- 整個家都非常關心和支持她
- 至於生命意義,母親盼望能再回到農村的家,憶及過去在田裡幹活、收割莊稼的時光
摘要:61歲女性、農民、已婚,有一個兒子和三個女兒。母親患上轉移性肺癌,呼吸急促,咳嗽超過一年,但沒有明顯的身體疼痛。儘管她最初試圖避免談論她的疼痛,但當她談論到她的疾病和女兒的未來時,她變得淚眼涕涕。她沒有說太多,但她所說的,雖然簡單,但其真實性觸動了我的心。以下是一些她的引語:
“我唯一的盼望就是看到我的大女兒出嫁。”
“我喜歡再次回到農村,撒下種子,在豐收中歡慶。”
- 葉女士,在2007年12月新會會城接受採訪,為時30分鐘。
- 70多歲女性、農村出身
- 所患的病影響著她的脾臟、骨骼和大腸,尤其是脾臟,給她相當多的痛苦。她盼望恢復健康
- 家庭是她的第一考慮。她和女兒住在一起,但她一直盼望著她兩個兒子來訪(小兒子是基督教牧師),盼望他們來到她家,和她一起吃午飯
- 做了基督徒不久。不論生命是好是壞,她都願意接受
- 她期待著四個孫兒長大成人
摘要:70多歲祖母。由於多重疾病(脾臟漲大、慢性結腸炎、嚴重骨質疏鬆症等)健康不佳。當談到她的兒孫時,她臉上露出的甜美笑容,取代了她的痛苦表情。以下是一些她的引言:
“雖然我和女兒同住,但我期待我的兒子們能常來這裡吃午飯。我喜歡看到他們的微笑。” “家庭對我來說就是一切。我的孩子長大了,他們也有自己的孩子,但我的孩子永遠在我眼中還是孩子。”
“我只盼望能再次有健康來照顧他們。”
“不論每一天是晴是雨,我都願意接受。”
- 曾女士,在2007年12月新會會城接受採訪,為時60分鐘。
- 30多歲女性,經營自己創立的美髮店;丈夫葉先生也是30多歲;丈夫與他前妻生的兩個女兒和她們住在一起,婆婆葉老太也在家幫忙
- 她本人也是第二次結婚
- 沒有宗教信仰
- 一年前,曾女士在右臉頰上發現有一個腫瘤;雖已切除,但這又復發了
- 她很失望,但願中藥能幫助她
- 夫妻雙方都盼望,在健康決策上,能有自主權
摘要:30多歲女髮型師曾患上淋巴瘤在右臉頰上;經切除後,又再復發。她與前夫有一個女兒,現在與前夫住在一起。再婚之時,丈夫葉先生已有兩個女孩要她來照顧。夫妻雙方都感到家庭壓力很大。由於葉先生的兄弟姐妹强行決定葉老先生的健康決策,引致葉老先生慘死,故此作爲兒子的葉先生甚感愧疚。難怪兩夫妻都希望可以決定自己的健康問題。我覺得讓她發洩一下也是適當的。以下是一些她的引言:
“這生命是我的生命,完全是我的生命。我獨一有權來决定我何時生或死。”
“我還年輕。我不應該患上癌症。如果上帝真是愛,為什麼會這樣折磨我?”
“我想活得更充實。”
“生活的質素,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我注重享受人生旅程,而不大在乎到達目的地與否。”
“我對淋巴瘤再次復發感到失望。現在我正在服用中草藥,希望能有幫助。”
- 彭先生,2007年12月在新會會城接受採訪,為時45分鐘。
- 90歲獨居老人;持續咳嗽,令他消耗大量精力;並且有反覆泌尿系統感染
- 他從十多歲起就開始吸烟;可能患肺癌
- 喜歡對生活有控制
- 也喜歡見到他的孫兒成長
- 已是基督徒一段時間
摘要: 90歲男性,有持續咳嗽,但仍未確診。儘管用抗生素治療,咳嗽仍然持續,令他很多晚都睡不著,耗盡他的大部份精力。他一個人生活,一輩子都是獨斷獨行。以下是他的一些引言: “我寧願獨居。孩子們都有自己的生活。”
“我的孩子和孫子都支持我,但我不想成為他們的負擔。”
“我是基督徒已經很久了。”
“在我理解中,苦難是可以有補贖的,正如基督的死救贖我們的罪。”
“我們經過苦難,才可以同情那些受苦的人。正如哥林多後書1:4告訴我們,‘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祂就安慰我們 、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
“感謝上帝,在苦難中賦予我們盼望。世上將會有光明,將來再沒有悲傷和痛苦。”
“基督教的價值觀也是我的價值觀。我在基督裏找到豐盛和永恆生命,得到滿足。希伯來書13:5解釋得很透切:‘你們…要以自己所有的為足 。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我把我的人生目的看作為上帝給我的目的:那就是愛 — 愛上帝、愛我自己、愛我家人、愛我鄰居、愛我朋友、國家、同胞、甚至我的敵人。”
“我想更像基督。我不想做偽君子,言行不合一。我想活出我的信念 — 仁愛、謙卑、忠誠、誠實和負責任。”
“當我在我的生命中體驗到上帝的恩典和恩賜時,我在靈裏就稍有成長了。我既是上帝的僕人,也是上帝榮耀的見證人。這是我的榮幸。”
“我盼望成為一個好父親和好爺爺。我想留下給我的孩子和孫兒永恆的遺產。我一直祈求他們能在基督裡成長。”
“我厭倦了生活。我想有一個好死。”
“生有時,死也有時。種子必須死去才有新生命。”
“我相信我們只是地球上的寄居者。死亡只是一個過渡 — 就好像毛蟲和蛹終於變爲一隻美麗的小蝴蝶。死亡絕不是終點。它只是一個開始。我相信會有來世。”
“俗話有云:‘即使是一隻小小的螞蟻也渴望偷生。’ 我又怎能自殺呢?只有上帝才能决定我何時何地離開這世界。”
- 謝先生,2007年12月在新會會城接受採訪,為時40分鐘。
- 18歲、男性、獨生子
- 高中畢業;對計算科學很感興趣
- 患有先天性主動脈分叉和心臟間隔缺損,左肺無肺動脈,導致身材矮小、皮膚發紫和體質殘弱(不能打籃球)。預後非常差
- 只有心臟和肺移植才能加高他的生存機會,然而這手術將會帶著頗高的死亡率
- 在感情上,謝先生似乎注定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情
- 他願意接受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所盼望的結果
- 他盼望未來的醫學進步可以為他扭轉局面
- 他似乎對上帝有深厚的信仰;他從7歲起就一直是基督徒(從他的祖母帶他去教堂時開始)
- 問到他生命的意義,他回答說,生命是寶貴的,是上帝賜予他的禮物
- 他認爲應該珍惜生命,尤其是因為他身體不好
- 他意識到父母因爲生下了他(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會有內疚感
- 他的父母、叔叔和嬸嬸都給他很大的支持
摘要:一名18歲男性高中生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導致身材矮小,身體嚴重殘缺。他唯一的生存機會是心臟和肺移植,而在中國,這類手術有極高的死亡率。以下是一些他的引語:
“我心中有安寧。我接受了這事實:我的預期壽命將會很短。”
“但是,也許未來的醫學進步可能會提高我的生存機會。”
“我父母對我生來有這個問題感到很難過,但是誰能責怪他們呢?”
“我感激父母養育我。”
“他們給我很多愛和支持,比他們意識到的還要多。我叔叔和嬸嬸也一樣。”
“我的生命來自上帝。我珍惜它。”
- 梁先生,2007年12月23日在外海接受採訪,為時25分鐘。
- 70歲,男性;與妻子和兒子同住
- 他的兒子最近接受了戒毒治療
- 兩周前梁先生跌倒,傷了腰背,從那時起,便因嚴重疼痛而臥床不起
- 他負擔不起止痛的醫療費用
- 他聽覺不好,說話也不多
- 他說他只是日復日地生活著
- 他考慮過死,但盼望令他繼續活下去;他盼望看到兒子完全從毒癮中恢復過來,再次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
- 自從他的妻子和兒子最近接受了耶穌基督後,他也成為基督徒
- 他的妻子和教會中人給他很大的支持
- 他相信有來世
摘要:70歲的男性在幾周前跌倒在地,傷了腰背,痛到一直臥床不起,而他也沒錢去看醫生來緩解疼痛。他的妻子和兒子照顧著他。他兒子的最好朋友在教堂見到我,便邀請我去拜訪這個家庭。那時梁先生正處於絕望和自殺的邊緣。以下是他的一些引語 :
“我不想再忍受這種痛苦了。這簡直是在折磨我。”
“我曾想過自殺,但我不能這樣做,至少不是在我兒子還是在接受戒毒治療的時候。我希望他能保住一份工作,再次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一員。”
“眼下我只有咬緊牙關,日復日的活下去。”
“自從我兒子在戒毒後成為基督徒,我和我妻子就得到教會的大力支持。”
“昨天,他(指著兒子最好的朋友)和我分享福音。我發現來世的概念是一個非常令我欣慰的想法。”
“我現在相信了。”
- 孫女士,2007年12月26日在江門接受採訪,為時30分鐘。
- 年齡40多歲;丈夫10多年前離開了她;有一個女兒(23歲)
- 她接受乳腺腫塊切除後,轉為化療
- 她的生命意義?只要有一份好工作來埋頭苦幹
- 感激女兒對她好;女兒的愛對她很重要
- 她覺得她之前的偶像崇拜可能導致她的乳腺癌
- 她還沒有受洗
摘要:40多歲女性,在近期接受了乳腺癌切除,跟著轉爲化療。她是單身母親。自從丈夫10多年前離開了她,她獨自撫養女兒長大。她深深感到自己的疾病是由偶像崇拜所引起。她覺得有罪便須解决。以下是她的一些引言:
“你認為我的偶像崇拜與我的病會有什麼關連嗎?”
“我的朋友告訴我,做一個基督徒會幫助我的病。你認為可能有奇蹟嗎?”(在這一點,我認為她需要澄清,但我不想貿然作為她的輔導者。我鼓勵她繼續祈求上帝的醫治)
“我讀到聖經裏,奇蹟的發生是信心的結果。我想相信這一點。我每天都祈禱求奇蹟。也許上帝會聽到我的呼求,憐憫我吧。”
“謝謝你幫助我了解我的疾病。疾病也好像雨水一樣,會降臨在一切人的身上,並不分好人或壞人。”
“事實上,因為我的病,我女兒和我親近得多了。”
“我盡可能活得正常,直到最後的日子。”
“我很慶幸自己還能病中兼職。”
(當我離開之時,我鼓勵她找一個屬靈的家。在那裡她會感到舒適,並會讓她的信仰繼續成長)
- 洪女士,2007年12月26日在江門接受採訪,為時45分鐘。
- 30多歲女性;在家中4名女孩中排第三
- 她有一個9歲的兒子和一個小女兒
- 家庭來自潮州,這是受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影響最深的地方之一
- 因為這個原因,她和她的姐妹們已是第三代基督徒了
- 她父親在2000年的一場車禍中受重傷。洪女士和她的母親一同努力照顧她的半昏迷父親
- 他們的關愛和承擔給醫院的醫護人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我問她,從她的角度來看,什麼使她父親活著?洪女士分享了幾個理由:(1)可能是他的基督教信仰;(2)可能是他愛家庭,尤其是愛他的兩歲孫兒;(3)甚至可能是他非常珍視個人尊嚴。這可以解釋他為什麼要堅持活著,直至最後一個生命意義從他意念中消失
摘要:30多歲女性,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個9歲的兒子和一個小女兒),是她父親的主要關顧者。她的父親因車禍處於半昏迷狀態,幸虧有她來照顧父親,因爲她的姐姐不願伸出援手。有時他們兩姐妹會在父親面前爭吵,令他氣得無法説話,淚水從面頰流下來。因爲傷心,他甚至試圖拔出自己的靜脈導管。有一次,當他排泄不通之時,需要妻子和年幼的女兒用手指幫他通大便,他覺得尊嚴大損,說不想再活下去。女兒說 :
“他實在很難接受沒有尊嚴。”
“以後很長的日子,他拒絕吃東西,對我們一點反應也沒有。”
“我多次向上帝祈禱,願神把他帶回天家。”
“當我的祈禱沒有得到回應之時,我開始懷疑上帝。就在那時,我聽到一個微小聲音說:‘如果你沒有信,我又怎能幫助你?’ ”
“從那時起,每當我偏離上帝,這一幕就會一次又一次的出現眼前。”
“父親的信仰給他平安。我從來沒有聽到他抱怨。”
“愛支持他繼續生活。父親愛他的孫子。當父親在2000年去世之時,孫子剛剛超過2歲。”
“家庭是父親的驕傲和喜樂。”
- 黃女士,2007年12月在江門接受採訪,為時30分鐘。
- 46歲單身女性,在 2000年患上乳腺癌
- 2001年用手術切除,但復發,近期接受化療
- 自從她母親9年前去世,她一直在照顧她的父親
- 她的妹妹非常支持她
- 她曾想過生活對她沒有任何意義,只是一場惡鬥,充滿著感情的起伏
- 她害怕死亡。在她父親去世之前,她也想及她自己的死亡
- 藉著院牧的輔導、大自然的啓發和祈禱,她找到了安慰
摘要:一個40歲的單身女性患有復發性乳腺癌,正接受化療。以下是她的一些引語:
“我在大自然中找到安慰。我喜歡早晨在周圍的小山和樹林裏散步。”
“當我獨自一人在樹林裏時,我聽到小鳥為每一個新的黎明唱讚美歌。我的福氣遠比我所認識的更多。”
“當我情緒低落時,我的知心朋友和妹妹都經常鼓勵我。他們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仍然害怕死亡。也許這就是與我成長過程有關吧。”
“自從我母親九年前去世之後,我一直在照顧我父親。每想到我可能會死在我父親去世之前,實在令我很不安。”
“當我不想再活下去之時,祈禱支撐著我。”
- 曹女士,2007年12月在江門接受採訪,為時45分
- 曹女士,40多歲,自幼患上嚴重支氣管擴張,最近兩年開始咳出血,需要經常住院
- 10年前患上肺病
- 她的低氧導致了偶爾的記憶力減退
- 她有兩個孩子,分別是12歲和13歲,是5年級和6年級的優秀學生,但曹女士從未結過婚
- 孩子們的父親是一個已婚之人,但他 與曹女士同居時隱瞞了這個事實
- 他們曾經合作成立過一家公司。當他因賭博輸掉自己的一份,公司便轉入她的名下
- 他和曹女士的侄女同居,又生了一個孩子
- 曹女士感到非常矛盾和無力處理這種關係衝突和自己的健康問題
- 她在採訪中不時流淚,擔心她會早死,丟下未成年的孩子們
- 當她回憶起自己的母親在她3歲或4歲時去世,尤其令她痛苦
- 至於生命意義,她是一心養育兩個孩子
- 她從她的孩子和主内弟兄姐妹那裡找到了愛和支持
- 她承認自己的信仰很軟弱,並且她又沒有耐性
- 她說她不知道如何祈禱
- 她盼望至少能看到她的孩子長大到18歲或19歲
摘要:曹女士是一位40多歲的單身母親,有兩個孩子(12歲和13歲)。孩子的父親已婚,在他妻子發現他婚外情後便拋棄了曹女士和孩子。曹女士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過去兩年咳出血,還患有慢性貧血和低氧,引致記憶力減退。以下是一些她的引言:
“對於我日漸衰弱的健康,我無能為力。”
“我希望看到我的孩子們獨立,但我擔心我可能不會有很長的時間活下去。”
“我三歲的時候,我母親去世,看起來像…”(她不能繼續,她的眼睛充滿淚水)
“我兩個孩子都給了我很多愛和支持。這讓我堅持活下去。”
“我的信心仍然很弱。我不知道如何祈禱。你能幫我嗎?”
(在我離開之前我教她如何祈禱)
- 吳女士,2007年12月在外海接受採訪,為時45分鐘。
- 20多歲單身女性,來自廣東省西部
- 一年前在廣州一個車禍中傷及骨盆破裂
- 同時,她的母親因腎衰竭而離世。她母親只是51歲,要經過多次血液透析才能存活
- 大約五個月前,醫生已告知吳女士(通過她的哥哥)她的媽媽已無藥可救。這並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因爲媽媽對血液透析的反應不佳
- 媽媽出院時,還不知實情,仍然盼望透析能延長她的壽命,但女兒已知媽媽命不久矣
- 在12月19日,媽媽因尿毒高而作病,呼吸急促,腹痛難忍。她希望女兒帶她去醫院做更多的透析
- 那時,吳女士真的感到無能為力。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晚上,母女兩人心都碎了。媽媽在早上便在家中去世
- 吳女士覺得她丟棄了生病的母親,感到非常內疚
- 家庭中人(叔叔等)將一切不幸歸咎於她。指責她背離傳統的偶像崇拜,信奉外來的洋鬼(指基督教)
- 據吳女士說,媽媽對腎透析是寄予很高的盼望
- 此外,媽媽一直盼望有機會見她的小女兒最後一面。雖然盼望不能達成,但畢竟支持著媽媽活下去
- 吳女士承認她的信心仍然很弱。她不明白,如果上帝是富有同情心,為什麼讓她母親受那麼多痛苦
- 吳女士很少得到家人的關愛和支持
摘要:一個20多歲的單身女性一直是她51歲母親的主要關顧者,直至母親死於腎衰竭。以下是一些她的引言:
“我們家族中大多數人都很迷信於敬拜祖先。他們不能接受我的信仰。他們稱我的上帝為‘外國魔鬼’。他們認爲我的信仰使母親患上這病。”
“我母親很難接受親戚的這個想法,雖然她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受苦。她變得與他們非常隔離。”
“她不明白我為什麼不帶她去醫院。我仍然對此感到內疚。“(我也不太明白,但我讓她繼續説下去)
“醫院的醫生曾告訴我不要把她帶回去。他們告訴我,他們對我母親已什麼事都做不了。”
“我們認為最好不要告訴她醫生說什麼,因為那樣會毀了她。她早就會自殺了。”
“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再見到她離家出走的小女兒回家。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媽媽。她在我妹妹回家之前就去世了。”
“在她還活著的時候,我母親喜歡園藝。花園裏的新生命使她的精神振奮起來。”
- 40多歲男道士,2007年12月在新會接受採訪,為時30分鐘。
當他被問及有關痛苦、絕症以及生死抉擇的問題時,以下是他的一些摘要評論: ”
“苦難是人類對慾念不能達成的情感反應。自然災害(如海嘯、颶風、地震等)會造成苦難,因為它們破壞了我們一貫珍惜的價值(例如生命、財產、安全等)。當我們渴望著安穩的生活、愛情、名譽和財富等,一旦受到挫折,苦難就會隨之而來,包括恐懼:恐懼痛苦、早逝、被拒絕、自己地位卑微、貧窮等等。”
“我們睿智的老師老子曾經說過:“如果我們能放下自己的情感和慾望,我們就不會受苦了。”
“痛苦可以是祝福的化身,危機也可變為契機。”
“信念、盼望和愛都會幫助我們減輕痛苦。”
“我們常常缺乏膽量去處理我們的矛盾。盼望可以幫到這一點,將我們的目光放遠來視察未來的可能性。絕症病患者在疾病的蹂躪下,不應被剝奪盼望。雖然病不能治癒,但總可以盼望得到醫治。”
“關顧者的態度應該是抱有盼望。盼望是有感染力的。關顧者對末期病患者的關愛和堅定不移的承擔,將會在病人身上激發起盼望。”
“然而,如果末期病人決定不想活下去,激勵和培育盼望是難之又難。”
“與其在末期鼓勵和培育盼望,還不如培育病者對自然死亡和生活責任賦予一個健康的尊重?”
“接受即將來臨的死亡並不一定意味著人在被動和絕望,而是意味著有勇氣來積極面對死亡…(他接著說)對生活上的一切充滿感激和頌讚 。這就是我們應該遺留下來的饋贈。”
“生活的意義是因人而異,受不同的傳統文化背景、以及生活方式所影響。”
“我的人生目標是與自然同在,並跟隨道的引領持續學習和成長。我的目標是學習如何謙虛、在自我約束中成長,為需要我幫助的人服務。”
“道可以給我們帶來充滿喜樂、自由和尊嚴的生活 — 使我們享受健康的相交以及瞭解自己。” “我反對自殺,包括醫生協助自殺,但我承認這是個人决定。病患者之所以選擇這途徑,是因為他們覺得別無選擇,但實際上他們還可以有其他選擇。”
“作為兒女,我們很難同意醫生協助我們的父母自殺,即使是病人要求,因爲這意味著作爲兒女的不能盡孝道。中國是以孝道為先。醫生協助自殺不僅牽涉及病人,也涉及整個家庭和社團。”
“當我為絕症病患者作諮詢時,我試圖幫助他們瞭解死亡。死亡是自然不過的、是生活的一部份、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我們不應該以宿命論的眼光來看苦難,並甘願在它的陰影下屈服。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來改變我們的生活、減輕我們的痛苦。”
“我相信自然死亡才是‘好’死,而不是靠醫生協助自殺。在我的諮詢過程中,我的目標是預備對方帶著尊嚴,平安的來面對死亡。”
- 一位40歲的女醫生(佛教徒),2007年12月在江門接受採訪,為時30分鐘。
在她的專業中,她曾給不少絕症病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但她並沒有直接照顧任何患重病的人。當被問及有關痛苦、絕症以及生死抉擇的問題時,以下是她的一些摘要評論:
“痛苦是人類的感知,它的程度是取決於人的意識和了解。我們既然放不下身體的慾望,又缺乏智慧來如此做,故此,根據因果律,我們就會有痛苦。”
“因為我們的愚蠢行為,我們必須付出代價,要麼是今生,要麼是來世。”
“我們受苦是因為我們無法消除我們對痛苦的感知。如果我們冥想佛法,聽從如來佛祖教導的真理,我們可以更好的忍受痛苦和更少受些痛苦。”
“我幫助病人理解痛苦是生活中無可爭辯的事實。沒有品嘗過苦澀,我們又怎能欣賞到生命的甜美?”
“我告訴病人,世界是在不斷變化中,苦難也不會持續下去。苦難終會悄悄而去,正如它悄悄到來一樣。”
“禱告有助於舒緩痛苦。對我來說,祈禱並不涉及懇求如來佛祖。相反地,它幫助我淨化靈魂,打開心靈去尋找新的可能性和解決方法。”
“有時,我會請佛門大師幫助我。大師會建議我的病人放生:買一些被捉的活魚或鳥,放他們生,以便積些陰德。”
“幫助絕症病患者整理一下未了之事也是非常重要 。”
“我會探索病者的個人生命意義,因為這會因人而異。”
“盼望不能減輕痛苦,但它可以緩解苦難。”(“盼望是什麼意思?”我問)
“盼望,在我的理解中,是熱切地展望將來,期待實現自己可行的目標或願望。它並不是癡心妄想。”
“生命只不過是永恆的生死循環之一部份。我們佛教徒把生命比作轉動的巨輪,靈魂得以輪回與化身。人生就像火焰,熊熊的燃燒。到死亡之時,火焰只是熄滅一時,卻在其他地方重新被燃起來。”
“我盼望我在地上與未來的生活是值得頌讚的。”
“我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現在我是該放手了。如來佛祖的教誨啟發了我,給我極大的平靜。”
“我對家庭和國家有很强的責任感。一個幸福和諧的家庭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人生目標是實現自我、發揮潛能、幫助他人。我的夢想之一是盡可能多學習。另一個是追求一切美善,包括世界和平、公義和美好。”(“什麼是所謂好?”我問)
“好與壞、對與錯的道德倫理完全是主觀的,是因不同文化、宗教、種族等而有所不同。這全取決於一個人的智慧和自我實現,可以幫助一個在苦難中的人找到平安。”
“我認為應該放憐憫在第一位。我贊成安樂死(醫生協助病人自殺)。如果你設身處地為那些末期病人着想,他們一邊受著極度疼痛,另一邊又沒有錢去緩解痛楚,如果是你,難道你不想結束這一切嗎?為什麼還要延長這痛苦?”
“家裡的負擔還不够嗎?”
“我們的資源實在有限。爲著延長末期病者的壽命所用的資源,不是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照顧孤兒嗎?”
“如果是我,明知活不久已,我會放棄進一步的醫療過程。我會用我殘留的歲月來做我喜歡做的事。我會趁我還可以之時來環遊世界,在我離世前觀看世界更多地方。”
“安樂死的取捨,關鍵在於病人自己對痛苦的感知和瞭解。當人失去了生存的意志時,與病魔爭戰的勇氣就已經全失。人雖然活著,但也只是行屍走肉吧。”
- 一位50 多歲的伊斯蘭教徒,男性,2007年在廣州接受採訪,為時30分鐘。
他母親的生命曾經在長期的生命支持系統中維持。當被問及有關痛苦、絕症、生死抉擇的問題時, 以下是他對醫生協助病者自殺的一些摘要評論:
“看到我母親身體上和精神上的健康惡化,我感到很痛苦。”
“我盡我最大的努力安慰和支持母親。”
“我每天都感謝真主。即使情況看來不佳,但要知道可能會更差。”
“當我母親活著的時候,我看天空常藍;當她離世時,一切都變為黑暗。”
“世界有苦難,是因為世界偏離了真主的目的和引導。”
“不應害怕死亡。這只不過是歸回真主懷抱吧。”
“我從苦難中吸取教訓:苦難讓我更親近真主。”
“雖然只有一絲毫盼望,我也會抱有盼望,因我知道世上沒有什麼是絕對的。奇蹟可以發生。但沒有信仰和盼望,奇蹟就永遠不會發生。”
“我不停與醫生商量。或者,因爲醫學進步,我母親可能會有救。誰知道呢?”
“我不能確定我的積極態度對我母親有否好處,但至少她在餘下日子裏可以忍受痛苦、提升她的生活質量。”
“我盼望母親的來世總會比今世更好。”
“我相信能夠活著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我的人生目標是敬重真主,服侍同胞。”
“就我個人而言,我反對醫生協助病者自殺,尤其是涉及我母親。我要敬重她、感激她、回報她對我的愛。我實在很難讓她走。”
參考書目錄BIBLIOGRAPHY
Alsop, Stewart. Stay of Execution: A Sort of Memoir. New York: J. B. Lippincott, 1973.
Anderson,Ray S. Spiritual Caregiving as Secular Sacrament: A Practical Theology for Professional Caregivers. London: J. Kingsley Publishers, 2003.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 1958.
Bandler, Richard, John Grinder, Steve Andreas, and Connirae Andreas, eds. Reframing: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aning. Moab, UT: Real People Press, 1982.
Barer, Morris L., et al. “Aging and Health Care Utilization: New Evidence on Old Fallaci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4, no. 10 (1987): 851-62.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Vol. 2, pt. 1. Trans. G. T. Thompson. Edinburgh: T. & T. Clark, 1957.
Beavers, Robert, and Florence Kaslow. “Anatomy of Hope.”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7, no. 2 (April 1981): 119-26.
Bloom, Gerald, and Sheng-lan Tang, eds. Health Care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Blumenthal, David, and William Hsiao.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Evolving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3, no. 11 (2005): 1165-70.
Boisen, Anton 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ner World: A Study of Mental Disorder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2.
Bowman, Kerry W., and Peter A. Singer. “Chinese Seniors’ Perspectives on End-of-Life Decision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3, no. 4 (2001): 455-64.
Brueggemann, Walter. Hope within History.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7.
Buber, Martin. I and Thou. Trans. Walter Kaufman. New York: Scribner; Edinburgh: T. Clark, I970-1.
Bunyan, John. The Pilgrim’s Progres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57.
Butler, Robert N. “The Life Review: An Interpretation of Reminiscence in the Aged.” Psychiatry 26 (1963): 65-76.
Byock, Ira. “Steve’s Story.” In On Our Own Terms: Moyers on Dying Discussion Guide, ed. David Reisman. New York: Thirteen/WNET, 2000. http://www.pbs.org/wnet/onourownterms/community/pdf/discussionguide.pdf (accessed May 20, 2008).
Cameron, Miriam E. “Technical Problems Involving Death.” AIDS Patient Care: A Journal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8 (Oct. 1994): 269-78.
Camus, Albert. The Myth of Sisyphus. Trans. Justin O’Brien. London: Penguin, 2000.
Capps, Donald. Agents of Hope: A Pastoral Psycholog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________. Biblical Approaches to Pastoral Counseling.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1.
________. Reframing: A New Method in Pastoral Car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0.
Capps, Walter H. Time Invades the Cathedral: Tension in the School of Hope.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2.
Carrigan, Robert L. “Where Has Hope Gone?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pe in Pastoral Care.” Pastoral Psychology 25, no. 1 (Fall 1976): 39-53.
Charles, Robert H.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a Future Life in Israel, in Judaism, and in Christianity. London: A. & C. Black, 1899. Reprint, Whitefish, MT: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7
Chen, Jia-gui, and Yan-zhong Wang. “The Report on China’s Urban Health Care System.” In Chin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Development Report 1997-2001 [in Chinese]. Ed. Jia-gui Che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Press, 2001.
Chen, Yu-hsi. “The Way of Nature as a Healing Power.” In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Stress and Coping, ed. Paul T. P. Wong and Lilian C. J. Wong, 91-103. New York: Springer, 2006.
Cole, Thomas R. “Gaining and Losing a Friend I Never Knew: Reading Claire Philip’s Journal and Poetr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9, no. 4 (Winter 1995): 329-34.
Coleman, Peter G. “Measuring Reminiscence Characteristics from Conversation as Adaptive Features of Old 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5 (1974): 281-94.
Confucius. Liji: The Book of Rites [in Chinese]. Jinan, Shandong: Shandong Friendship Press, 2000.
Cook, Sarah, and Susie Jolly. “Unemployment, Poverty, and Gender in Urban China: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Laid-off Workers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IDS Research Report, no. 50. Brighton, England: University of Sussex,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Corless, Inge B. “Hospice and Hope: An Incompatible Duo?”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9 (May/June 1992): 10-12.
Corr, Charles A., Clyde Nabe, and Donna Corr. Death and Dying, Life and Living. 4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2003.
Cousins, Norman. Head First: The Biology of Hope. New York: E. P. Dutton, 1989.
Coward, Doris D. “Meaning and Purpose in the Lives of Persons with AIDS.” Public Health Nursing 11 (1994): 331-36.
Crites, Stephen D. “Narrative Quality of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39 (Sept. 1971): 291-311.
DeGraff, Geoffrey (a.k.a. Thanissaro Bhikkhu). “Life Isn’t Just Suffering.” http://www.thaiexotictreasures.com/suffering.html (accessed May 20, 2008).
Deng, Ming-Dao. Scholar Warr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o in Everyday Life. San Francisco: Harper SanFrancisco, 1990.
De Shazer, Steve. Putting Difference to Work.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Dhammavihari, Bhikku. “Euthanasia: A Study in Relation to Original Theravaden Thinking.” Y2000 Global Conference on Buddhism, Singapore June 3-4, 2000. http://www.metta.lk/english/euthanasia.htm (accessed May 20, 2008).
Donald, Anna. “What is Quality of Life?” In What is… ? Series. http://www.whatisseries.co.uk (accessed May 20, 2008).
Dunlop, John. “A Physician’s Advice to Spiritual Counselors of the Dying.” Trinity Journal 14, no. 2 (Fall 1993): 201-14.
Dworkin, Geral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Edlund, Matthew, and Laurence Tancredi. “Quality of Life: An Ideological Critique.” Perspectives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28, no. 4 (Summer 1985): 591-607.
Elwell, Walter A., ed.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84.
Erikson,Erik H. “Human Strength and the Cycle of Generations.” Insight and Responsibility: Lectures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Psychoanalytical Insight.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________.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59.
________.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1968.
“Euthanasia: The Buddhist View.” BBC Religion and Ethics Forum. Feb. 24, 2004. http://www.bbc.co.uk/religion/religions/buddhism/buddhistethics/euthanasiasuicide.shtml (accessed May 20, 2008).
Fanslow-Brunjes, Cathleen, Patricia E. Schneider, and Lee H. Kimmel. “Hope: Offering Comfort and Support for Dying Patients.” Nursing 27, no. 3 (1997): 54-57.
Farran, Carol J., Kaye A. Herth, and Judith M. Popovich. Hope and Hopelessness: Critical Clinical Concep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5.
Fawzy, Fawzy I., Norman Cousins, et al. “A Structured Psychiatric Intervention for Cancer Patients. I. Changes over Time in Methods of Coping and Affective Disturbanc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47, no. 8 (1990): 720-25.
Fife, Betsy L.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in Illness.”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1995): 1021-28.
Fisher, Walter R. “Narration as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1 (1984): 1-22.
Frankl, Viktor Emi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Rev. and enl. ed. Trans. Ilse Lasch.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________. The Unconscious G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5.
Freud, Sigmund.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umes. Eds. James Strachey et al. (London: Hogarth Press, c1966, 1974), 119-23.
Fromm, Erich.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Furman, Ben, and Tapani Ahola. Solution Talk: Hosting Therapeutic Convers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Gardner, Richard A. Psychotherapy with Children of Divorce.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6.
Gu, Edward. “Labor Market Insecurities in China.”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Publ., May 2003.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protection/ses/download/docs/ labor_china.pdf (accessed May 14, 2008).
Guignon, Charles B.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2nd ed., r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Hauerwas, Stanley. Naming the Silences: God, Medicine, and the Problem of Suffering.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Publ., 1990.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rnold V. Mi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
Heidegger, Mart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________.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Heschel, Abraham Joshua. The Prophet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Hesketh, Therese, and Wei-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The Healthcare Market.”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 (2004): 1616-18.
Hippocrates. “Hippocratic Oath.”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istory of Medicine Division. http://www.nlm.nih.gov/hmd/greek/greek_oath.html (accessed May 20, 2008).
Hirth, Alexandra M., and Miriam J. Stewart. “Hope and Social Support as Coping Resources for Adults Waiting for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26, no. 3 (1994): 31-48.
Hoff, Benjamin. The Tao of Pooh. New York: E. P. Dutton, 1982.
Hoffman, Ernst. “Hope.” In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Ed. Colin Brown. Vol. 2.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76.
Horn, Joshua S. Away with All Pests: An English Surgeon in People’s China: 1954-196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Hunter, Rodney J., et al., ed. Dictionary of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1990.
Kahn, Joseph. “China’s ‘Haves’ Stir the ‘Have Nots’ to Violenc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1, 2004, A1.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John Miller Dow Meiklejohn. Mineola NY: Courier Dover Publications, 2003.
Kasulis, Thomas P. Intimacy or Integrity: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Kaveny, M. Cathleen. “Cultivating Hope in Troubled Times.” Lume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Nov. 2005. http://www.nd.edu/~lumen/2005_11/index.shtml (accessed May 25, 2008).
Keats, John. “Last Sonnet.” In The Poetical Works of John Keats, ed. H. Buxton Forman, 48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Kekes, John. “The Meaning of Life.”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24 (2000): 17-34.
Keown, Damien. “Buddhism and Suicide: The Case of Channa.”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3 (1996): 8-31.
Kogon, Manuela M., David Spiegel, et al. “Effects of Medical and Psychotherapeutic Treatment on the Survival of Women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rcinoma.“ Cancer 80, no. 2 (15 July 1997): 225-30.
Kübler-Ross, Elisabeth. On Death and Dying.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________. “Therapy with the Terminally Ill.” In Death: Current Perspectives, ed. Edwin S. Shneidman. 2nd ed. Palo Alto, CA: Mayfield Publishing, 1980.
Lao-tzu. Tao Te Ching. Trans. Dim-cheuk Lau.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3.
Lazarus, Richard S. “Positive Denial: The Case for Not Facing Reality.” Interview by Daniel Goleman. Psychology Today 48 (Nov. 1979): 44-60.
________. “Stress and Coping as Factors in Health and Illness.” I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ancer, ed. Jerome Cohen et al. New York: Raven Press, 1982.
Lester, Andrew D. Hope i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Leung, Thomas In-sing. From Suffering to Hope [in Chinese]. CD-ROM. Vancouver, BC: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Productions Association, 2004.
Li, Chun-ling. “The Class Structure of China’s Urban Society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3, no. 1 (2002): 91-99.
Li, De-quan. “The Right Direction in Providing Health Care for the People” [in Chinese],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First 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 Beijing, Aug. 7-19, 1950. People’s Daily Oct. 23, 1950, Editorial.http://read.woshao.com/400327 (accessed May 25, 2009).
Li, Lan-qing. “The Reforms of the Basic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and the Health and Medicine System for Urban Staff and Workers” [in Chinese], delivered at National Conference in Shanghai, China, July 24-26, 2000.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3124/node3125/node3127/userobject6ai269.html (accessed May 24, 2009).
Li, Pei-lin. “Problems and Trend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http://china.com.cn/chinese/zhuanti/2004shxs/483054.htm (accessed May 14, 2008).
Lim, Meng-kin., Hui Yang, Tuo-hong Zhang, Wen Feng and Zi-jun Zhou. “Public Perceptions of Private Health Care in Socialist China.” Health Affairs 23 (2004): 222-34.
Liu, Gordon G., et al. “Equity in Health Care Access : Assessing the Urban Health Insurance Reform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5, no. 10 (Nov. 2002): 1779-94.
Liu, Yuan-li, Ke-qin Rao, and William C. Hsiao. “China’s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 Facing the Challenges.”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82 (2004): 532-38.
________.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19 (2004): 159-65.
________. “Medical Spending and Rural Impoverish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21 (2003): 216-22.
Liu, Zhong-xiang. “A Study of the Problem Related to Medical Assistance for Urban Poor.” Table 2. Sociology Department,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2003..
Lo, Ping-cheung. “Confucian Values of Life and Death and Euthanasia.” Annual of the Society of Christian Ethics, 19 (1999): 313-33.
Loder, James E. The Transforming Moment: Understanding Convictional Experience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1.
Lynch, William F. Images of Hope: Imagination as Healer of the Hopeless. Baltimore: Helicon, 1965.
Macmurray, John. Persons in Relation. London: Faber & Faber, 1961.
Macquarrie, John. Christian Hope.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8.
________ In Search of Humanity. New York: Crossroad, 1983.
________“Pilgrimage in Theology.” Epworth Review 7, no. 1 (Jan. 1980): 47-52.
Marcel, Gabriel. “Despair and the Object of Hope.” In The Sources of Hope, ed. Ross Fitzgerald, 44-66. Trans. Jean Nowotny. Rushcutters Bay, Australia; Elmsford, NY: Pergamon Press, 1979.
________. Homo Viator: Introduction to a Metaphysic of Hope.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78.
Marshall, Ellen Ott. Though the Fig Tree Does Not Blossom: Toward a Responsible Theology of Christian Hop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6.
Massie, Mary Jane, et al.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Journal of Pain and Symptom Management 9 (1994): 325-40.
May, Rollo. Freedom and Destin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________. Love and Will.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McMahon, Arthur W., and Paul J. Hudick. “Reminiscing: Adaptational Significance in the Aged.”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0 (1964): 292-98.
Meissner, William W.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Mencius. Mencius, trans. D.C. Lau.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Metz, Johannes B.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oward a Practical Fundamental Theology. Trans. David Smith.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80.
Mijuskovic, Ben. Loneliness in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Assen, Netherlands: Van Gorcum, 1979.
Minear, Paul S. Christian Hope and the Second Coming.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4.
Mishel, Merle H. “The Theory of Uncertainty in Illness.” Image 20, no. 4 (1988): 225-32.
Mitchell, Deborah R. “The ‘Good’ Death: Three Promises to Make at the Bedside.” Geriatrics 52, no. 8 (1997): 591-92.
Moltmann, Jürgen. In the End, the Beginning: The Life of Hope. Trans. Margaret Kohl.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04.
________.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Trans. James W. Le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Moyers, Bill D., Betty S. Flowers, and David Grubin. Healing and the Mind. New York: Doubleday, 1993.
Nelson, William B. Jr. “Hope.” In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ed. Walter A. Elwell, 355-57.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96.
Nichols, Aidan. The Art of God Incarnate : Theology and Image in Christian Tradition.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80.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Birth of Tragedy.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6.
________. The Birth of Tragedy and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Francis Golffing. New York: Doubleday, 1956.
________.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________.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7.
________. Thus Spake Zarathustra. Trans. Thomas Common. New York: Heritage Press, 1967.
________. “Twilight of the Idols.” In The Portable Nietzsche, trans. and ed. Walter Kaufmann, 463-564. New York: Penguin, 1976.
________. The Will to Power. Trans.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Ed.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8.
Nouwen, Henri J.M. Out of Solitude:Three Meditations on the Christian Life.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74.
Ogden, Schubert. “The Meaning of Christian Hope.”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30 (Winter-Summer 1975): 153-64.
Ou, Ai-hua, and Yan Zhu. “Analysis of Condition of Elderly People and Their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in Guiyang City.” Chinese Primary Health Care 3 (2000): 47-48.
Pannenberg, Wolfhart. Anthropology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5.
________. Theolog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Ed. Richard J. Neuhaus. Philadelphia:Westminster Press, 1969.
Parker-Oliver, Deborah. “Redefining Hope for the Terminally Ill.”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19, no. 2 (2002): 115-20.
________.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Dying Role: The Hospice Drama.” 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0, no. 4 (2000): 19-38.
Pattison, E. Mansell. “The Experience of Dy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1 (1967): 32-4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ureau of Statistic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98, 2001.
________. Gansu Province Department of Health.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System in Gansu Province.” Gansu, 2000.
________. Ministry of Health. Annual Report, 2001. Beijing, 2001.
________. Ministry of Health,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he
Circular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Style Rural Cooperative Health Care System. Beijing, Jan. 10, 2003.
________.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An Investigative and Analytical Report on the Reform of th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Zhenjiang, Changshu, and Shanghai” [in Chinese]. Beijing: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Institute Publ., Nov. 11, 2001.
________. “New Rural Medical Care System to Insure Farmers’ Health,” March 30, 2006. http://www.china-embassy.org/eng/xw/t243199.htm (accessed May 14, 2008).
________.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Report on Reform of Health Care System for Staff and Workers [in Chinese]. Beijing: Gaige, 1996.
Plato. The Republic. Introd. Charles M. Bakewell.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1928.
________. Plato’s Phaedrus. Trans. Reginald M. Hackfort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Progoff, Ira. The Dynamics of Hope: Perspectives of Process in Anxiety and Creativity, Imagery and Dreams. New York: Dialogue House Library, 1985.
Pruyser, Paul W. “Phenomenology and Dynamics of Hoping.”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 (1964): 86-96.
________. Between Belief and Unbelief.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________. The Play of the Imagination: Toward a Psychoanalysis of Cultur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83.
________“Maintaining Hope in Adversity.” Pastoral Psychology 35 (1986): 120-31.
Qin, Yan. “Schiavo’s Fate Fires Debate on Euthanasia.” China Daily, Mar. 23, 2005,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03/23/content_427546.htm (accessible May 14, 2008).
Ratner, Carl, and Lu-mei Hui.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3, no. 1 (2003): 67-94.
Reese, Dona J., and Dean R. Brown. “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 Care in Hospice: Differences between Nursing, Social Work, and Clergy.” Hospice Journal 12, no.1 (1997): 29-41.
Remen, Rachel Naomi. A quote from Healing and The Mind by Bill D. Moyers, Betty S. Flowers, and David Grubin (New York: Doubleday, 1993), 357. Publication information for Rachel Remen not provided.
Richards, Victor. “Death and Cancer.” In Death: Current Perspectives, ed. Edwin S. Shneidman, 322-30. Palo Alto, CA: Mayfield Publishing, 1980.
Richardson, Robert L. “Where There is Hope, There is Life: Toward a Biology of Hope.” Journal of Pastoral Care 54, no. 1 (Spring 2000): 75-83.
Rideout, Elizabeth, and Maureen Montemuro. “Hope, Morale and Adapt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11 (1986): 429-38.
Rogers, James. The Dictionary of Cliche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5.
Salmond, S. D. F. Christian Doctrine of Immortality. 3rd ed. Edinburgh: T. & T. Clark, 1897.
Sarbin, Theodore R. “The 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sychology.” In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ed. Theodore R. Sarbin, 3-21. New York: Praeger, 1986.
Sartre, Jean-Paul. 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i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 Trans. Hazel E. Barnes.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56.
Scarry, Elaine.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chopenhauer, Arthu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Trans. E. F. J. Payne. Vol. 2. Indian Hills, CO: Falcon’s Wing Press, 1958.
________. Parerga and Paralipomena: Short Philosophical Essays. Trans. E.F.J. Payne.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4.
Scott, W. Clifford M. “Depression, Confusion, and Multival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1 (1960): 497-503.
Shorr, Joseph E., Gail E. Sobel, et al., eds. Imagery: Its Many Dimension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Plenum, 1980.
Smith, David L.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Theology. Wheaton, IL: Victor Books, 1992.
Smith, Douglas C., and Michael F. Maher. “Achieving a Healthy Death: The Dying Person’s Attitudinal Contributions.” Hospice Journal 9 (1993): 21-32.
Smith, Stephen M. “Hope, Theology of.” In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ed. Walter A. Elwell, 577-79. 2n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2001.
Snook, Lee E. “Death and Hope – An Essay in Process Theology.” Dialog 15, no. 2 (Spring 1976): 123-30.
Snyder, Charles 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________, and Shane J. Lopez, eds.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olomon, William David. “Double Effect.” In The Encyclopedia of Ethics, 2nd ed., eds. Lawrence C. Becker and Charlotte B. Becker, 418-20. Florence, KY: Routledge Press, 2001.
Song, Xiao-wu, and Hao Liu. “The Reform of the Health Insurance Syst Accompanying Measures.” In Report on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ese], ed. Xiao-wu Song.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1.
Sorajjakool, Siroj, and Henry Lamberton, eds. Spirituality, Health, and Wholeness: An Introductory Guide for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2004.
Spiegel, David, and Irvin D. Yalom. “A Support Group for Dying Pati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28, no. 2 (1978): 233-45.
________, et al. “The Effect of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he Lancet 2 (14 Oct. 1989): 888-91.
Stone, Howard W., ed. Strategies for Brief Pastoral Counseling.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01.
Tada, Joni E. When Is It Right to Die? Suicide, Euthanasia, Suffering, Merc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2.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Vol. 2. Trans. Wilfrid Lescher. London: Thomas Baker, 1906.
Tillich, Paul. “The Right to Hope: A Sermon.” Christian Century 107, no 33 (Nov. 14, 1990): 1064-67.
Triandis, Harry C.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94.
Tse, Chun-yan, Alice Chong, and Janet Sui-yee Fok. “Breaking Bad News: A Chinese Perspective.” Palliative Medicine 17 (2003): 339-43.
Tu, Wei-ming. 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Unamuno, Miguel de. 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Trans. J. E. Crawford Flitch. New York: Cosimo Classics, 2005.
Waley, Arthur, trans. The Analectsof Confucius. New York: Everyman’s Library, 2001.
Wang, Dong-jin.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Sufficiently Understanding the Reform of th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for Urban Staff and Workers” [in Chinese]. China Labor 158 (Jan 1999): 4-7.
________e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ese]. Beijing: Falu Press, 2001.
Wang, Mei-Ling, Shuo Zhang, and Xiao-Wan Wang. WTO,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Weisman, Avery D. On Dying and Denying: A Psychiatric Study of Terminality. New York: Behavioral Publications, 1972.
Wells, Richard A. Planned Short-Term Treat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Wernow, Jerome R. “Saying the Unsaid: Voicing Quality-of-Life Criteria in an Evangelical Sanctity-of-Life Principle.”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391, no. 1 (March 1996): 103-22.
Wholihan, Dorothy. “The Value of Reminiscence in Hospice Care.” 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9 (1992): 33-35.
Williams, Alan. “’Need’ – an Economic Exegesis.” In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ed. Anthony J. Culyer, 259-72. Vol. 1.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Pub., 1991.
Winnicott, Donald W. “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 In Collected Papers: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8.
Wong, Chack-kie, Vai Io Lo, and Kwong-leung Tang. China’s Urban Health Care Reform: From State Protection to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6.
Wong, David B. “Pluralistic Relativism.” In Moral Concepts, eds. Peter A. French, Theodore E. Uehling, Jr., and Howard K. Wettstein, 378-99.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6.
________. “Comparative Philosophy – Chinese and Western.” Rev. 2005.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comparphil-chiwes (accessed May 20, 2008).
Wong, Paul T. P. “Chinese Positive Psychology.” In Encyclopedia of Positive Psychology, ed. Shane Lopez, 148-56.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ub., 2009.
________. “The Wisdom of Positive Acceptance.” President’s Colum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ersonal Meaning, 2004. http://www.meaning.ca/archives/presidents_columns/pres_col_feb_2004_ positive-acceptance.htm (accessed May 20, 2008).
________ and Catherine Stiller. “Living with Dignity and Palliative Care.” In End of Life Issues: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ed. Brian de Vries, 77-94. New York: Springer, 1999.
World Bank. China: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b-National Finance: A Review of Provincial Expenditures. Report No. 22951-CH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2.
Xiong, Yue-gen. “Social Policy for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in China: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elfare for the Aged 1 (1999): 107-22.
Yalom, Irvin D.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________.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4th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Yardley, Jim. “Rural Exodus for Work Fractures Chinese Family.” New York Times, Dec. 21, 2004, A1.
________“Xin-min Village Journal: A Deadly Fever, Once Defeated, Lurks in a Chinese Lake.” New York Times, Feb. 22, 2005, A4.
Young, Julian. The Death of God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3.
Zhou, Li-ping and Rui-zi Wang. “Analysis of Health Need and Utiliza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Hangzhou City” [in Chinese]. Journal of Zhe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27, no. 2 (1998): 84-87.
Zhuan, Hui-lin. “Analysis. May 23, 2003.Urban Deprived Groups in the New Era: Stud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 Care Protection Mechanism” [in Chinese]. Market and Population Analysis. May 23, 2003.
Zimmerli, Walther.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Outline. Trans. David E. Green.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78.
END OF BOOK – HOPE YOU HAVE FOUND IT HELPFUL 希望這書對您有幫助
